【2022諾貝爾文學獎】書寫是死與生的創造──安妮.艾諾《Happe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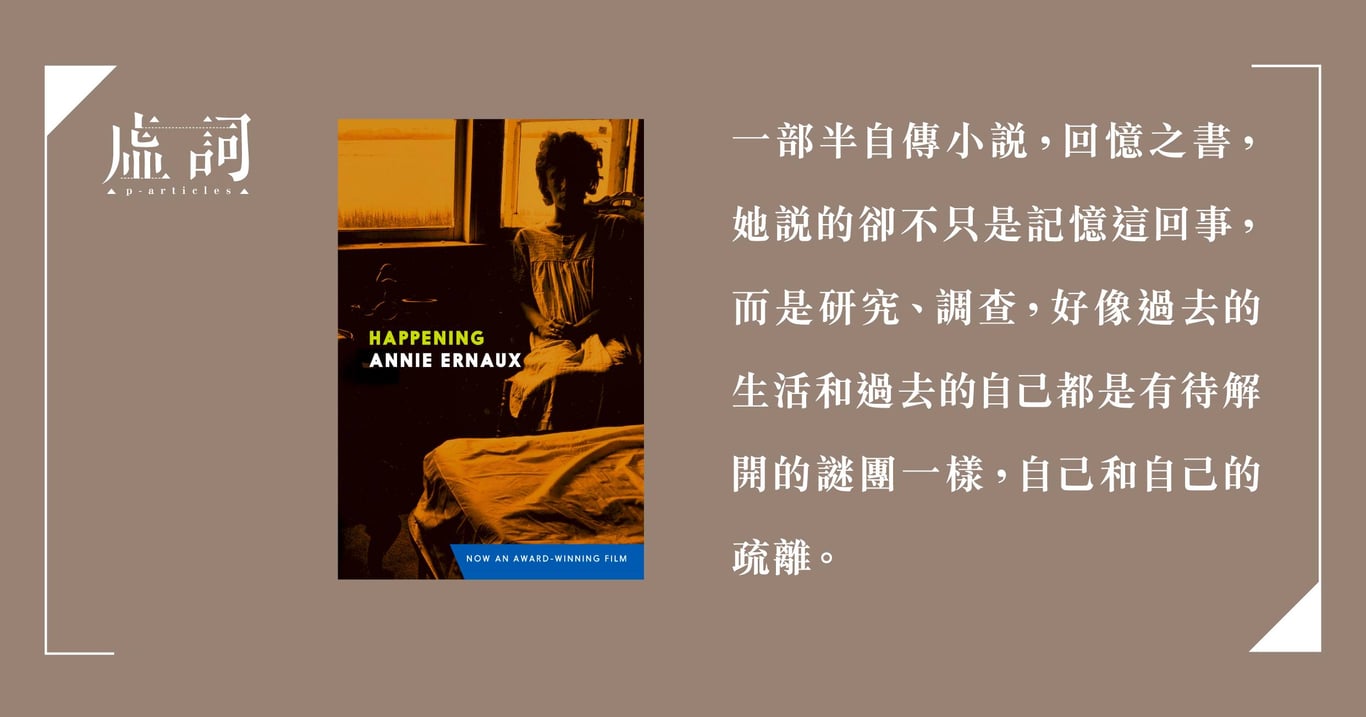
文|黃柏熹
一、
“I want to become immersed in that part of my life once again and learn what can be found there. This investigation must be seen in the context of a narrative, the only genre able to transcribe an event that was nothing but time flowing inside and outside of me.” (19)
這是安妮.艾諾(Annie Ernaux)寫在小說《Happening》(L’événement,中譯《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前言的句子。一部半自傳小說,回憶之書,她說的卻不只是記憶這回事,而是研究、調查,好像過去的生活和過去的自己都是有待解開的謎團一樣,自己和自己的疏離。當我讀到「nothing」這個字時,不知為何內裡感到分外難過,一下踏空,或是面前明明有字但妳在內裡把它唸出來的時候,妳覺著一種虛無。她所說的「時間」。所謂創傷就是,時間不是線性或可量化的姿態,而是在一個人的身體裡來回翻滾,意義在事件框架的裡外始終拿不定主意,碰上言語之際又總是說來話長,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
就像當妳以載滿情意的眼神凝視著我,我聽見風在窗戶上猛撞的聲音,但我不敢直視。或當我直視,就必須以身體為代價。重探過去必須是一趟以生命為載體的冒險,妳底賴以存在的根本,它要經得起痛和徹底翻轉的可能。
二、
我是看完那部在威尼斯電影節得獎的改編電影後,才回個頭來讀艾諾的原著小說。撇除若干情節改動,或許是出於戲劇性的考慮,電影相比小說更像一個「完整」的故事,圍繞著戲劇發展、聲影、鏡頭調度和角色的建構,提供一個在敘事結構中得以完滿結束的過程。而小說,正如艾諾所言,是以「敘述」(narrative)為目的,讓記憶和回憶的過程──包括所有遲疑和內心掙扎──都得以被赤裸呈現的書寫。赤裸的意思是,它總是分心和分裂的,這邊廂以冷靜的口吻敘述往事,那邊廂在剖析回憶之於自己的意義和其不可能性,突然停頓又重新開始。
我無意在這裡比較電影和小說的呈現手法,也不是要比較其高低。我的意思是,兩者本來就基於截然不同的目的,才會出現相異的表現形式。我會這樣形容:艾諾在小說裡的書寫是一種純粹的書寫,或一種僭越的書寫;她寫,不是為了迎合任何故事結構或外在目光,而是不得不寫,在秘密和禁忌的樊籬前,不得不去僭越,唯有形塑成字才能從中確認身體的存有,才能愛撫,或觸碰,那個被埋藏在內裡的自己。
文字,在這裡成為身體一樣的物質存有。妳必須說,才能在場。
三、
甚麼身體?一個被父權法規加以禁制,透過禁止墮胎使女人在自己內裡異化成物的身體。身處嚴格管制墮胎的法律隨時從歷史灰燼中重燃起來的現世,我幾乎是抖顫著寫下這句句子。
在被管制的身體之外,卻是艾諾筆下一個又一個在她之前或緊隨其後的,一個又一個透過不同方法嘗試終止懷孕的女人。小說裡的敘事者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時間不是線性或可量化的姿態,它回來,又再回來)。
我記得,改編電影的鏡頭常常以一種逼近的距離緊隨著主角Anne的女體,譬如母親用身體來量度她的體溫,譬如好幾次看到胸圍肩帶留下的印痕,譬如淋浴間裡,赤裸女體之間的距離和互為憑證,或房間裡的自慰和情慾探索。電影沒有離開過Anne,也沒有離開過身體,一切痛苦與快慰都源自這裡,身為女人,身體是給予也是抑壓所在。
小說也一樣寫到身體,寫到她的慾望和恐懼。艾諾在小說裡寫,“When I made love and climaxed, I felt that my body was basically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man.” (16),性慾的充盈,儼如一個沒有區別、沒有言語的伊甸樂園。但意外懷孕讓她看見作為一個女人,或女人作為眾數的命運,如果沒有終止懷孕,在工人階級背景加上年少懷孕和社會污名加諸的恐懼中,她,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女人──或許就是一個這邊廂把孩子安撫進睡,那邊廂又得為客人奉上晚餐的家庭主婦。沒錯,我們仍是必得重提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名句。她不是活在自己的性慾裡,而是在法律和恐懼中「成為」一個女人的。
四、
所以她寫。寫有時是一個倒轉的過程,把銘刻在身上的言語倒過來寫,人才能擁有自己,或至少掏出一點空間。毀壞是一種創造。
她會寫到昔日在日記中寫下的文字,如果文字以物質的形式保存著一個有待考掘的自我。她說,重讀自己的日誌,她發現過去她只會稱呼肚腹裡的東西為「it」或者「that thing」,只有一次寫到「pregnant」。她覺得沒有必要為一個不會在未來發生(而她急欲脫離的)事命名。她又寫到,在一次跟男性醫師會面的過程裡(那一次她希望他可以在終止懷孕一事上幫助自己),兩人在整段對話中完全沒有提過「墮胎」(abortion)一字,彷彿它在語言中根本沒有位置。
──如果語言不只是機械性的運作原則,而是因應使用者的意願而得以隱沒或無名。如果語言因為禁忌而在我們之間擴展成為一個黑洞。所以妳寫,所以妳說。
艾諾在書的前頁引用了超現實主義作家Michel Leiris的句子:“I wish for two things: that happening turn to writing. And that writing be happening.”。如果書寫不只是對語言的運用,而是創造語言。如果唯有透過書寫,人才能抵達自己。與其說《Happening》是有關一個在禁止墮胎年代,勇敢面對世界並得以實現自己的女性,不如說小說書寫本身就是一個「成為」的過程。書寫總是「正在發生」的,不是先有一個完整的真理在她面前等待,沒有應許之地,沒有流奶與蜜,而是一次又一次,通過回憶,通過與文字碰撞(而不至心碎),我得以成為我、擁有我、親吻我。去寫就是把整個身體交托出去,是創造,是重新講述自己。
或換句話說,去寫就是自由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把無物換成禮物的神聖時刻。「我」因為書寫而得以存在。
五、
小說《Happening》所包裹著的,其實是一種生死的倒置,或詞義轉換。
其中一個現在仍然盛行的反對墮胎理由,是把終止懷孕等同於剝奪生命。在小說裡,當艾諾寫到那個替她秘密施行墮胎手術的年長女士,把冰冷的醫療用具伸進她的兩腿間時,她形容是“is giving birth to me” (53)。被等同於殺害的手術在她筆下倒置成重生的契機。她又緊接著寫,“At that point I killed my own mother inside me”。直接挪用一個掀起爭議的詞彙,卻把一整個意思翻轉過來。
「母親」的意思未有在她筆下被確認下來,儼如將解未解的一詞多義。誰是「我的母親」?是指那個在戰前年代出生,在壓抑和羞恥的性文化中成長的,她的母親?抑或是那一個以生育為核心的,負責給予愛給予照料的母親形象?又或是一整個把她複製再造的性別矩陣,現在她得以告別過去,重塑自我?她沒有寫明,她在這裡留下一個可供解讀的密碼。她只是一再提到她覺得那位替她做手術的女士很像她的母親,在血脈之外,為女人自己創造可能性的陰性連結。
而連結就是創造的意思。
後來,她會寫到自己在大學宿舍的房間裡,跟另一名女生一起剪去臍帶,繼而大量出血被送到醫院。她會再一次挪用生與死的語言,形容她的房間,自己的房間,“I had given birth to both life and death” (69)。她這樣為自己的回憶作結,為自己的書寫作結,為自己講述自己,因為書寫她的生命得以展現,得以重生。禁忌不再是禁忌,死亡被翻轉成重生,父權律法在女性敘述的複寫/重寫下,生命或語言的主權得以被重構,改變在發生的當下發生。正如她在小說裡寫,終止懷孕使她更懂得折磨和犧牲是生育必要付出的代價,因為更懂得才能作負責任的決定,從「選擇終止」生出「接受生育」的可能,到底也是一種轉換。
一切始於書寫,終於書寫,亦繫於書寫。
一切可能的。
六、
發現自己懷孕前,她本來有一份大學論文還未完成,主題是有關女性在超現實主義寫作裡的角色。在小說結尾,她提到終止懷孕的經驗──穿過生死、時間、法律、道德和禁忌,甚至席捲身體的經驗──使她前所未有地接近這個論文主題。但她的經驗無法轉換成整全的意念或理論化的辯證,而是如夢一樣的視角,沒有形狀的概念,一種「wordless intelligence」,或未知或未被發現的言語。在禁忌和剝削的文化裡,試圖去言說那些僭越的經驗,不正正符合超現實主義那革命性的創新精神嗎?
而言說,就是構築身體本身。意思是,任何書寫,最終都是一種生命書寫,一種意志的展現和交托。唯有身處如海浪般的敘述中,自我才得以顯露(unfold)。這種自我不是自我沉溺的人格,而是通過自我考掘,展現或預視生命的可能性;正如艾諾在最後幾番提到,她彷彿是走到一個女性的前沿地帶,未來的世代將會比她走得更前。
很喜歡她寫在小說最後的句子,是為記──
“Among all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reasons that may account for my past, of one I am certain: these things happened to me so that I might recount them. Maybe the true purpose of my life is for my body, my sensations and my thoughts to become writing, in other words, something intelligible and universal, causing my existence to merge into the lives and heads of other people.” (75)
參考書目:
Ernaux, Annie, and Tanya Leslie. Happening. Fitzcarraldo Editions, 2022.虛詞・無形網站
虛詞・無形Facebook
虛詞・無形YouTube
虛詞・無形Patre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