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上對談》青年小說家生存手記:張亦絢、洪明道、鍾旻瑞雲端交鋒

張亦絢:進行線上對談的兩個主角,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年輕小說家,洪明道和鍾旻瑞。他們在出版短篇小說集之前,寫作的成績都已經備受矚目。所以我也都是先認識他們的小說,之後,才見到過他們本人。雖然他們小說裡的許多人物,會讓我想到「悶葫蘆」三個字,但小說家本人,都還蠻愛說話的。
旻瑞知識的領域相當廣泛,我想他可以參加按鈴搶答的比賽項目,包括電影與建築等。明道則是台語非常輪轉,且大家一定會注意到,他對台灣文史,甚至是地方政治,都有自己的觀察。旻瑞也在擔任編劇與導演,明道則是醫生——他的簡介裡說他在「小說和病歷中打滾」,但我想他應該也有病人?醫生作家是蠻有傳統的,文學電影雙棲也是,兩位除了聰明穎悟,也處於不算太壞的創作環境中,可以期待未來的文學長路。
➤小說裡的守備選擇
張亦絢:短篇小說集不容易介紹,因爲每個短篇都是獨立的天地,所以我先概略地說一點印象式的想法。把《等路》與《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放在一起時,我的腦海會不斷浮現兩個字,那就是「砂」與「金」。不是說一本是砂一本是金。而是說,旻瑞很擅長給出一種金黃色的氣氛,然後慢慢地,有一粒砂現出非常粗礪的質地,改變了一切。明道是相反過來,一開始會覺得是有趣或平易近人的砂,然後瞬間覺得這當中有一粒金,所以砂也要捧好,才能留住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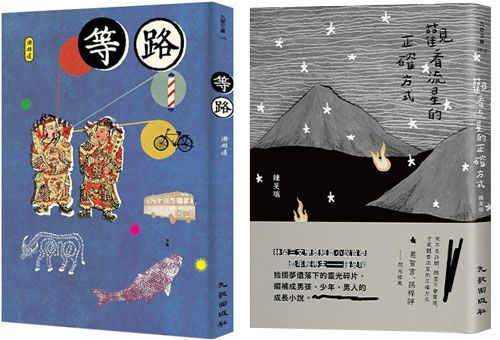
另方面,我在兩個人的創作裡,都看到一種可喜的傾向,也許對年輕創作者來說,是種不錯的參考,我會稱那個東西叫做「不逼自己」,但不是說不努力。而是說,是很善於選擇,是找到一個自己最有感情的守備範圍與方式,並不貪心。那個範圍並不天大地大,但他們就是「變本加厲」地深化與轉化它們。除了兩人的小說技巧都非常穩健,小說也有種淡泊與專注的氣質,非常耐讀與感人。
洪明道:謝謝亦絢、旻瑞一起來玩這場線上對談,線上這樣的環境,使我更容易悶住人物,悶燒一段時間後竟也把小說煮熟了。我一方面順勢利用這種時間的魔法術,一方面以此藏拙。看完引言,不得不讚嘆亦絢看小說的精準,兩三句話就可以抓出作品的質性,以及我在內心的算計。
我現在的確是醫生沒錯,也有病人。臨床工作是我和大量不同人接觸,保持對人的警醒很重要的地方。但畢竟身在其中,有所收穫也會有所消耗。
鍾旻瑞:去年在研究所上了亦絢老師半學期的課,似乎給你留下了「妙麗」般的印象,舉手時會手臂打直、貼緊耳朵,哈哈。的確我從小就是上課愛發言的學生,但我其實口才並不好,尤其只要聊到自己的創作,就很容易支支吾吾,出書時為我做專訪的幾位訪問者,應該都曾深受其擾。
老師提到的悶葫蘆角色,除了與我本身的個性相似,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的小說技巧,有許多是從孟若(Alice Ann Munro)和卡佛(Raymond Carver)身上啟蒙的。他們小說中的「悶」,各種人物的言不盡意,甚至是包藏禍心,所醞釀出的深沉令我著迷,也希望能在小說當中製造出相同的效果。
另外我猜測寫劇本的訓練也對我的小說造成了影響。初學寫劇本時,便一直被學校老師告誡不要把欲表達之事,用台詞直接說出來,應該盡量讓角色用行動來傳遞訊息,若非得用講的,更要仔細思量角色當下的處境和目的,不要讓角色成為交代、填補劇情的工具。因此刪減過於直白的情節或敘述,也成為了自我檢視時的本能反應。
張亦絢:你這樣一說,我真的很想叫你妙麗。
➤寫作的外部環境
洪明道:我剛要起步時,正好是文藝政策和生態轉變的時候,使我很快地找到可以穩定寫作的模式。這真的是幸運。如果沒有這樣的環境配合,我還是會寫,但也許就不會這麼順遂。在還沒有什麼成果、不確定能寫出什麼時,我一直問自己,如果只能寫一本書哪些是我最想寫的?寫作的過程十分驚奇好玩,在其中,我一再確認光是創作本身就可以帶給我滿足。
寫《等路》前不久,為了教育自己而大量閱讀的作品,影響了我看待小說的態度。〈泳池〉是在那段時間看的,讓我對於平淡的力量更有信心。在後來的《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裡,旻瑞展現了他創造不同氣氛、各種展延時間的能力。如果拿吃來說好了,這個廚師是大菜小吃都能做啊!

鍾旻瑞:關於創作環境,印象當中我曾經歷過的大改變——或說趨勢,除了國小、國中時的網路小說熱潮,就是這幾年大家常掛在嘴邊的影視IP,但這兩者都是看電視新聞可以得知的,不是什麼內行人的觀察。
比較大的焦慮還是回到創作本身。我的小說很貼著自己的生活在寫,因此經常有「燃料耗盡」的恐慌,當然寫作才剛開始,這目前還算是遠憂,但我真的常警告我自己,若不勤做功課,學習運用其他材料,遠憂很快就近了。
讀明道的《等路》時,特別崇拜他所能塑造角色的多樣性,不分年齡時代,都能準確掌握人物和環境的細節。許多段落的描寫,都全面照料到讀者的「五感」,可以聽見對白的口吻,聞到味道、感受到溫度。
➤《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裡的同志時空軸
洪明道:讀《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時,許多篇章有關男性之間的情感,閱讀時頓時青春回憶湧上心頭,小說成功讓我想起克服過的一些困境和困擾。
從伴侶法一直到同志婚姻公投的這幾年,各性別團體無不動了起來,動用文字、動員情感,以達最大力量的展現。但《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不求代表性、力量或說服,而展現物質、文化、人攪在一起的網絡,這類事物特別吸引我。摻雜肉體的愛、經濟的愛、孤獨的愛、投射自身的愛、單一的愛、流動的愛……的「那種東西」,在小說裡被辨識出來。
在〈第五次約會的下午〉,小說捕捉了「這種東西」既高雅又卑劣,不好也不壞的時刻。但要抵達這樣的時刻,外在也是參一腳的,諸如交友軟體的視覺性、即時性、以及拉起在社會不同階級的「我」和「他」的偶然性。小說的推進走在鋼索上,「他」一步一步中靠近,「我」半推半就,最後的落地毫不馬虎。
張亦絢:〈第五次約會的下午〉寫得很好的還有姐姐這個角色。一個非同志姐姐的人生追求,有很明顯的時空軸,所以姐姐的代表性台詞「我們快沒時間了」,是「她的戰術」。這裡對照出同志的「時空問題」,非同志的思慮是時空軸上的進度,同志的「沒有」,是「時空軸的沒有」——姐姐的寬容反而更顯得殘酷。或許同志也想寬容,但卻沒有同等資本,小說裡,傷害並不來自「惡意」,而是更根源性的處境。
找住處沒那麼難,為什麼投向沒那麼愛的同志同居?以往評這篇會說,異性戀也會無愛同住,落點在道德上。但我看最後的選擇,是主角想要保有最低限的同志時空軸,這也同理了爲什麼某些同志會做出危險的人生選擇,問題不在智慮,而是更被剝奪的基本需求層次,「我們連『快沒時間的時間』都沒有」——主角沒出這個聲,這也是非常棒的技巧,可是應該在小說裡「聽到」這事。小說不只哀傷,還言之有物。
➤創作燃料耗盡的焦慮
洪明道:〈肉球〉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肉球〉裡的課題並非男同志特有的,類似的故事很容易被寫俗,但這課題發生在男同志裡又有點不一樣。〈肉球〉遊走在感情的開放和佔有慾之間,兩個人物共處一室,各自與貓的互動裡透露洶湧的潛在訊息。即使讀爛了開放式關係的理論,摸熟了液態之愛等書,小說裡的人物也要愛著才知痛,人也常常如此。
《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時常用文字看穿「那種東西」的組成,而「那種東西」和別種最顯而易見的不同之處,偶爾會被人稱作是「男同志文化」,但小說不刻意強調不同,也沒有全部混為一談,慢慢的把「那種東西」裡被世人認為好的壞的都描出來。
小說裡寫得很成功的又一件事是「變化」。借用小說人物裡的話來說,「這幾年變化太快,原本感到不可能的事,又可以重新夢想了」。但即使如此,還是有成長的孤獨、憂鬱和恐懼,度過這些事情的人物時常忘了這些。《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讓我的新身體重新想起舊傷,也讓我不敢輕忽正在他人身上發生的痛,有擾亂線性進步觀或將成長視為扁平曲線的可能。
也想問旻瑞,在寫作第一本書時有燃料耗盡的焦慮,那寫完後會不會想在同處挖深一點?現在怎麼處理類似的擔憂?
鍾旻瑞:想再深入的心情當然是有的,但目前計劃先轉移目標,去挑戰其他方向。一方面是對更多東西產生興趣,希望探一下自己能掌握的邊界。一方面也想把已經寫過的主題,放進地下再釀一釀,看時間能如何改變我與它們的關係。這並不表示我在寫其他內容時,會完全捨棄或排斥相同的元素,大概也無法真的捨棄,那些畢竟最觸動我神經,只要經過就忍不住多看它們幾眼。
無論是影視或小說,我近來養成的品味都偏「硬」,像是歷史或職人,即便不是寫實,也是有很縝密世界觀的奇幻或科幻作品。在閱讀的時候,會忍不住一直跳到作者的立場去想像他們如何處理材料,在細節完備的同時,又不會成為百科全書,依然是一則好看的故事。這些作品對緩解焦慮滿具有效果的,它們提醒了我做功課的重要性,以及做足功課後,作品所能開展的可能性。

➤《等路》裡的感官與敘事練習
張亦絢:旻瑞怎麼讀明道的《等路》呢?有哪幾篇是你會特別想提出來跟大家談的?
鍾旻瑞:讀明道的小說,腦海中最常浮現的詞是「精準」,他從各事物中揀選出來的細節,所透露的訊息總能夠大於細節本身。比方〈路竹洪小姐〉末段洪小姐站在天橋階梯上,明道寫「飼料的玉米粉發酵過,卻能產生肉食久置的氣味。這股氣味形成了風,把洪小姐的裙擺吹起來,那是一件有皺摺的雪紡。」之前我提到的所謂「五感被照顧」,這一段落便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讀到時心中發出歡呼聲,寫得太好了。
「有皺摺的雪紡」是極簡的白描,在小說該處卻起了很強大的作用。從前面我們雖可以拼湊出洪小姐的身世,但在那一刻卻彷彿可以把這個人物的「材質」放在手中端詳,皺的、淡色的、輕盈的、顆粒的布料,是少女會有的選擇。這樣一種材質被帶有異味的風吹動,無論讀者是否有去思考延伸意義,它所製造的感官效果都非常深刻。
明道的作品中有很多句子,是可以這樣拿出來一一拆解、細讀的。對於事物特質的掌握,我感覺這真的是某種獨特的天賦,但或許明道在此前做了許多練習。我對明道出書前的創作歷程不太熟悉,是否可以請明道談談在小說創作上的「練習」,是如何掌握這些技巧、選擇語氣和風格的?又或者,《等路》也是某種有意識的練習呢?
張亦絢:嗯,雪紡是很舒服的輕磨沙粒感呢,很高興聽到雪紡的出現。如果可以,也想請問明道,書寫台語的能力是怎麼養成的?有人跟我說,你是台語家庭,但有些台語家庭不見得傳承到書寫的能力,這部份很想多了解一點。
洪明道:大學時,有空閒會強迫自己寫一些日常事物,一個單位大概一百字,儘量不用成語或已經有的說法,但現在沒時間,已經中斷這個自我訓練了哈哈!
我猜這可能和認識字詞的方法有關,高中時代被我視為同儕的寫作者,她在網誌或部落格為自己訂立了一個標準,那就是「不懂的字詞不寫」。
在字詞要有把握,又要避免已成俗的描述或說法的狀況下,除了用動詞和名詞推進小說,大概就要靠各種感官能感知道的事物。在寫《等路》時,是有意識的想控制文字層次的傳達誤差,並讓意義在其他層次生成,而找尋字詞的來源很大一部份是生活中的聲音,一些日常聊天、抐代誌。這些聲音有不同於書面文的活力,也常常是台語,轉換過程中在台語部分加點雅氣(ngá-khì)。這麼說來,在咖啡廳寫作時偷聽隔壁桌講話是我很大的樂趣。

至於語氣和風格,我沒什麼主動選擇。我很喜愛小說的距離和隱藏,我喜歡把自己縮到最小,只保留某個我曾體驗過的核心,類似於旻瑞所提到觸動神經的部分。
而學台語文從羅馬拼音、聲調這些非常基礎的東西開始,慢慢獲得書寫能力,到現在還是有很多要學的。大約是五、六年前,我週末會去長老教會上課,讀台語文聖經故事,兼作人類觀察。寫作者創作時如果想寫台語,可以上網查查台語文,能避免許多陷阱和誤遞。如果有特殊意圖或象徵再自行造字。
➤小鎮經驗與空白空間
鍾旻瑞:讀完《等路》時,我立刻注意到雖是各自獨立的短篇集,卻有首尾呼應之處,那就是火車行進的方向。首篇〈改札口〉女主角因遭遇白色恐怖,從路竹搬遷到台南,卻因調職不順,每日仍須早起前往路竹教書。最後一篇〈路竹洪小姐〉結尾,洪小姐則是懷著不確定,搭上了離開路竹的北上列車。一來一往之間,其實都是對路竹這地方,透露出想離開而無法真正離開的矛盾。
我成長過程並沒有留下這類「封閉小鎮」的經驗,因此思考這會不會是我們作品中描寫如此不同的原因。我的小說裡人與人、人與地方之間的歷史很短,甚至不太重要,根本是陌生人。明道筆下的人物,身上卻都背負著一道歷史「臍帶」,千絲萬縷地決定了角色當下的樣貌和處境,也讓他們難以真正做出改變。
我從明道的小說中隱約讀出某種憤怒的殘留。會說殘留,是因為認為那經過了時間和文學創作的轉化,已成為了充滿感情的表達,並非寫來作為武器,要挑戰或是冒犯誰的。對於明道而言,小鎮經驗的影響是什麼呢(創作和情感上都可以)?那可能是你憤怒的來源嗎?
洪明道:我一直不太懂自己成長時期的憤怒是一種怎樣的東西,持續透過創作來搞懂它。小說裡藏了不少類似的情緒。
就和創作相關的歷程來說,我被學校老師認為作文寫得不錯,文學大概就是種升學工具,就這樣而已,那時候,很少人告訴我可以去探索、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我總是會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受困在學校或台南。現在說起來有點中二,但當時會覺得時常和外在環境對撞。
在保守的台語家庭裡,長輩也很難想像後代寫作,偶爾我會聽到他們驕傲地說,咱厝內有人出冊閣著獎,寫贏真濟外省人。並不是要劃分省籍,也不認為寫作可以拿來輸贏,但比較能理解他們的限制,以及加在我身上的限制。這麼一來,不是告訴十幾歲的自己那些憤怒不必要,反而更能體會憤怒的真實感,轉化成可以言說的東西。
我自己算是從小鎮裡流出來的人,在路竹、台南、台北都待過一段時間。異地後往往感受到身心變化,過捷運閘門不那麼時尚流暢,行為模式也會不同。環境對我的影響,不下於所遭遇的人,《等路》裡的人物的確受環境牽連,還有一些性格、時間和其他人物等的牽連。種種牽連交織在一起可能就是旻瑞讀到的歷史臍帶。經旻瑞這麼一說,《等路》裡人物的狀態類似日語的「不自由」,他們可能不充裕、受限制或不能隨意行動。但這類臍帶或出路是小說打造出來的,有沒有說服力就交給讀者裁決了。
張亦絢:嗯,了解!明道這段話有很多深意啊,「寫贏真濟外省人」,這也是真的嘛,我覺得說出來很好。我也是小鎮流出來的作者,所以我非常驚豔《等路》「寫環境」的功力。封閉小鎮是一種說法,我看到比較多反而是對「異質性空間」的處理。這也是明道小說特別好看的地方,魚塭、海邊道路或「無名地」,他都能寫出「八百萬種不死亡」。我對大都會喪失的「空白地帶」,感受很強。非都會的「空白的刺激」,也是「小說之地」復育的記憶。《等路》在這個意義上,可說出類拔萃。

➤小說的身體與臍帶
張亦絢:小說家讀小說家,著眼點與一般讀者略有不同。兩人都展現了各自「讀技巧的偏執」(這是好的)。但我來稍事平衡,也說一下,兩本小說集的故事性與結構都有「不避俗又不流俗」的優點,技巧經常也是隱而不顯的,從未變成擾動閱讀的機關。在對談中,明道綜合觀察的傾向比較明顯,旻瑞對單一物件或句構激發感受性的效果情有獨鍾,這有點像「工程」與「工序」的兩種不同重心,但在完成小說上,重要性是不分軒輊的。我們看到旻瑞念茲在茲的「作功課」,明道在養成台語書寫投下的工夫,會發現兩人對工程與工序上的倚重,又彷彿位置對調。——換言之,兩人對均衡發展都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小說能寫得那麼好,皆非偶然。
能把兩個作者連通在一起,我想是「身體平權」的概念。因爲,無論性身份或是多語(在談多語時台語往往被忽略,但我覺得除了母語外,也應將其放在多語中思考。),身體可以說都是最後的拔河點。那麼,《等路》與《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都提供了非單一平權概念的複合思考,明道揭露的層面包括了多篇觸及的城鄉經濟,障礙者如〈路竹洪小姐〉、「歧視性正音矯正」如〈零星〉,以及政治受難者被隱形的身體如〈改札口〉——後者可說是經典級的文本。
而旻瑞的〈指關節〉、〈煙火〉與〈容器〉多篇,也不無黑色幽默的劍指當代對形象與外貌的失控迷戀——平權因此在兩位手中,都成爲高度外延的場域,且內容豐富。
最後,讓我重拾旻瑞的表達,並接續明道的探討,就「臍帶說」稍作延伸。生物性的臍帶在落地後,必要剪斷,但文化與精神性的臍帶呢?不同於生物性,我們可能同時併有胎兒與長者,兒童與成人於一身,所以臍帶也可能必須在斷與不斷之間。此外,我們思及臍帶,將自我定位在哪一邊呢?是吸收方或供給方?
文化的臍帶性也許不同於生物性,不是絕對單向且強制的。如果說「歷史性」經常被想像成父權、壓迫或保守的,小說除了恢復個體多元性以對抗,是否也可能作爲另一種根與源的新集散地,透過「去歷史」而「再歷史」呢?我想,這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方向。●(原文於2020-06-04於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等路
作者:洪明道
出版:九歌出版
作者簡介
洪明道
台大醫學系畢業。1991年生,原高雄縣人。現職成大醫院住院醫師,在病歷和小說中打滾。創作以小說為主,以《等路》獲2019年臺灣文學金典獎及蓓蕾獎、金鼎獎。曾獲臺南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等小說首獎。希望能當台灣小說界的美空雲雀。
於《秘密讀者》發表多篇評論,其他評論散見於《聯合文學》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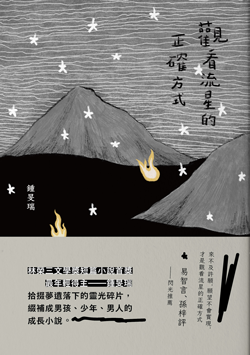
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
作者:鍾旻瑞
出版:九歌出版
作者簡介
鍾旻瑞
1993年生,台北人,政大廣電系畢業。曾獲台北文學獎、台積電學生青年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17歲時寫的小說〈醒來〉,便入選九歌100年度小說選。〈泳池〉榮獲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為歷屆最年輕得主,是文壇備受矚目的新人,目前從事編劇、導演等影視工作。

性意思史:張亦絢短篇小說集
作者:張亦絢
出版:木馬文化
作者簡介
張亦絢
1973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 /巴黎回憶錄》 (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2019起,在BIOS Monthly撰「麻煩電影一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