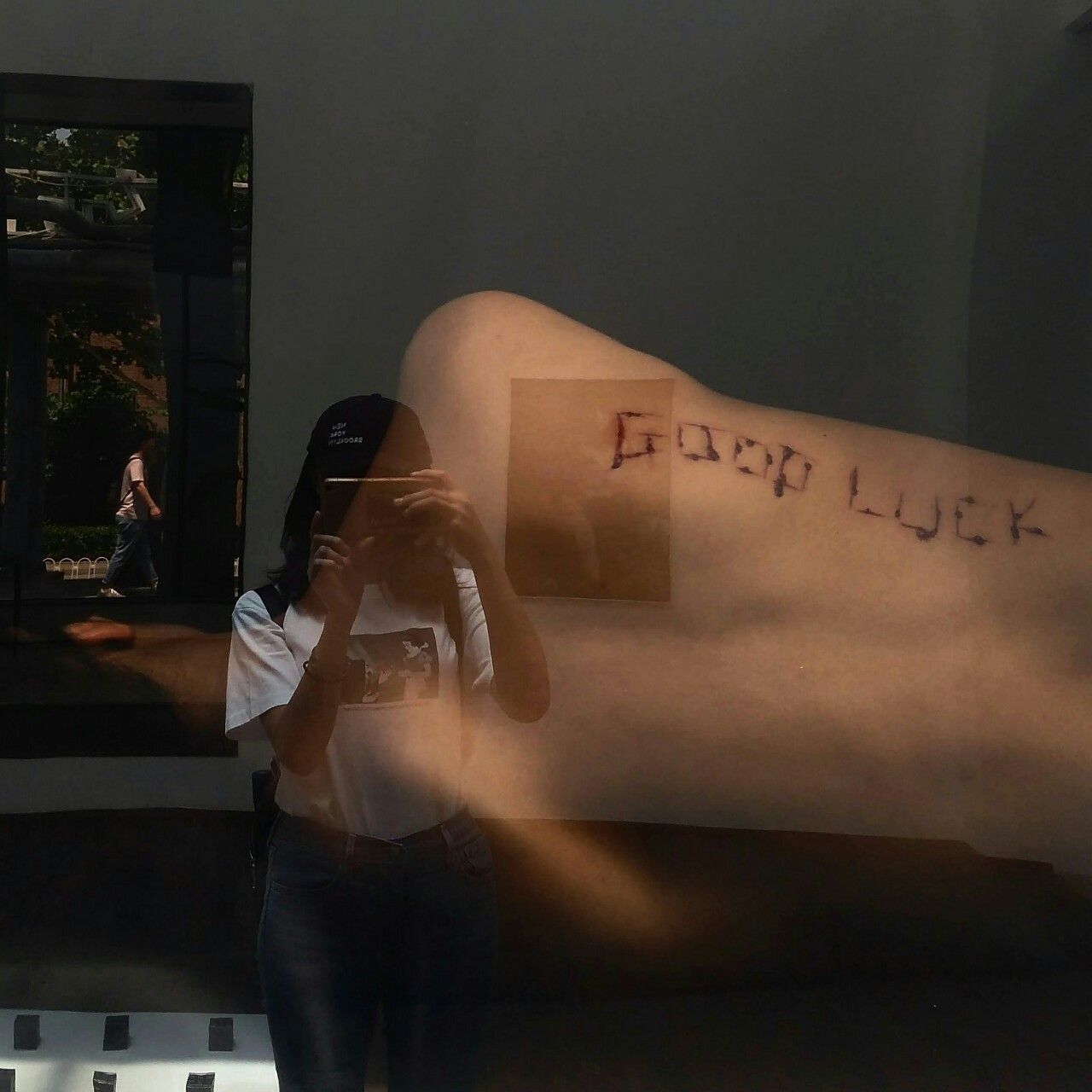【電影】聖慾(2021):你信或不信,我就在這裡
剛看完《聖慾》(Benedetta,2021),我很愛,跟我同行的朋友則不很喜歡。「太亂了,」她說,「進不去。」
好有趣,因為對我來說,反而是那接二連三朝我湧來的感官刺激,淹沒我、沖刷我,逼迫我放下理性,只能去感受。而我喜歡這部片,也只能訴諸感受。我試著跟她解釋我喜歡《聖慾》的什麼,現在我要試著以文字重現那天我想說、想描繪給她看的我的感覺,但大概很難。畢竟文字是屬於理性的。
(這不是影評,只是心情。從來不覺得自己在寫影評。我何德何能稱自己在寫影評。)

尤記得大一時上西洋文學概論,教授常常提醒我們,要面對的文本是來自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而我們要想接近那個時代,基本上不可能。讀中世紀的東西,他會叫我們想像自己的生活是全然被天主教浸透:沒有週休二日,放假的日子就是宗教節慶、生老病死都跟教會有關、對時間的理解、對苦難的想像,等等、等等。但這些東西列表出來就是這樣、就是知識,就是對中世紀我可以說出的一些生活樣態,充其量也只是知道,卻無從想像——從何想像起?我甚至不信教啊。
可是我想說的第一點,就是《聖慾》不知為何,使我有一瞬間能夠想像自己生活在那樣的時代。
我很難一一描述哪些機制讓我一時之間恍惚變得「可以」了(對,因為感受就是不理性,沒有文字插足的空間),但倒可以側寫幾個我還記得的腦中印象——最一開始,Benedetta進到修道院,褪下錦衣換上麻布,她一句「皮膚會痛」跟修女回覆的「那就是目的」,觸覺的基調有了;她所謂的「房間」是用布幕圍出來的,實際上跟眾人同處一室,只有一兩個個人櫃子使用,然後十三年間她都在這個「房間」起居,一種全然不同的人我關係有了(更加極端的是Benedetta和Bartolomea坐在隔壁一起上廁所——可以一起上廁所,不能讓對方看見裸體)⋯⋯
這些鋪陳讓我能夠「陷入」,從而讓我在電影後半段,有了相當神奇的體驗。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跟著Benedetta見證一切的修女。
這很重要。在電影前半段,Benedetta反覆看見異象,導演拍出她所見的耶穌,觀眾自然相信Benedetta是真的虔誠、真的聖人。但在後半段,Benedetta成功上位修道院長後,儘管她次次聲稱自己看到神顯靈,電影裡卻再也沒有任何顯靈的片段。我覺得自己像被拋在那個時空當中,我就是那些一無所知的修女跟村人。我得靠我自己所見,判斷Benedetta到底是聖女還是騙子。而這就是我認為《聖慾》想要探討的主題——關於信仰、關於虔誠。
- 如果是我,信或者不信?
如果是你,你信或不信?在前半段被說服了「對,她真的看得見」之後,突然眼前又擺出新證據:碎掉的玻璃片可能被她拿來自己割出聖痕(Stigmata)、她每一次的「看見」都恰好替她解圍(「怎麼可能這麼剛好!?」)、她跟Bartolomea進駐院長獨立房間後沉迷肉體之歡的放縱、甚至是把聖母像當成自慰道具歡愛⋯⋯你還相信,她是如她自稱虔誠的「耶穌的妻子」嗎?
那,當你面對你無法理解的恐怖、超越你存在的巨大厄運——死亡跟瘟疫,眼前出現了一個堅定的說你會沒事的聖女,你相信不相信她?不要問你的理智,情感上你想不想相信?
這當然是個人選擇;電影對觀眾信或不信不予置評,倒是刻畫了幾個劇中人的信與不信。
比如Benedetta的情人Bartolomea——她從頭到尾都不信。她跟Benedetta不同,當初進到修道院本不是自己想獻身於神,而是為逃離家暴又性侵的父兄,要說她有多虔誠,我是抱有疑問。她貼身照顧Benedetta期間Benedetta身上第一次出現聖痕,接受修道院長質疑時,她主動站出來替Benedetta作證——偽證。她根本沒看見,作證只是為了她愛Benedetta;她要是真信Benedetta,哪還會需要、或者是敢,在這麼嚴肅重大的事件上說謊?
後來她要Benedetta承認她就是在演戲,曝露出自己自始至終都只是把Benedetta看成女演員。Benedetta堅持她是真的聖女,Bartolomea說:Tu me dégoûtes,「你讓我覺得噁心」。直到最後,兩人戀情曝光、失去容身之地,Benedetta好不容易逃出火刑,離開小鎮,卻仍堅持回返修道院,Bartolomea都還在懇求Benedetta:「承認吧,你是假貨。你不可以回去,因為回去你必死無疑,別再說什麼耶穌會來解救你這種鬼話」。她覺得Benedetta瘋了。當然,在不信者眼裡,Benedetta是瘋了。
另一個人是修道院長Felicita。Felicita身為修道院長,第一次看見奇蹟時的反應,竟是奇蹟總帶來麻煩。她從來不相信Benedetta,只是為了政治利益假裝相信她,後來甚至親至佛羅倫斯請教廷派人來裁決Benedetta偽造聖痕(那位教廷大使自然也是不信),不過——到了最後,她突然相信了。她在佛羅倫斯與法國小城之間的往返途中罹患黑死病,臨死前Benedetta來見她,不知在她耳邊低語了些什麼,讓她成為一個真正的虔信者。她無畏的走向Benedetta被從之解放的火刑柱,擁抱火焰,為之吞噬。
她在死亡面前突然的「信」,跟小城居民們對Benedetta的擁戴,也有幾分可比之處。試想:你發現全世界都受瘟疫侵襲,幸好蒙主眷顧,你所在的地方還沒有確診(真切題的現代詞彙);這時,你那地區的聖女、「耶穌的妻子」、宗教機構的首長突然被爆出醜聞將被處刑,她卻預言:她在,則瘟疫不來;她死,則神怒降臨,眾人陪葬——你敢燒死她嗎?你敢不敢冒這個險?
這是另兩個《聖慾》讓我體驗到的、以前只能靠想像的情境:民粹、絕對恐懼。同在疫中的我們,此刻應該很能同感中世紀鄉人對黑死病來襲的不知所措;把之前的恐慌放大數千倍,去想像一個疾病還沒被除魅、科學還沒把一切都變得可觀察可分析的世界,未知的疫病是壓倒性的存在,輾過所經的一切,而你覺得自己立於它的車輪前,無從逃避。這時候除了懼怕神罰,跟著眾人上街自我鞭笞,以祈倖免,我還能有什麼預防措施?除了緊緊抓住每一縷希望的蜘蛛絲,哪還有別的地獄出口?在書上讀恐懼帶來民粹,聽起來人們好像很蠢,但只要設身處地代入那些恐懼,就會發現民粹是不得已又自然的結果。群眾暴亂,劫刑場、殺教廷大使,對將自己投身情境中的我來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這又是怎樣的信仰?是一種巴斯卡賭注(Pascal’s Wager)一樣的,工具性、功利性的信仰?
這種信仰,在本質上與聖女Benedetta的信仰,是兩回事。
- Benedetta的虔誠(我流解釋)
對,我認為Benedetta是整部電影最最虔誠、恐怕也是唯一虔誠的人。
珠玉在前,我說再多都是野人獻曝。但我還是要說,因為有些東西只有我才說得出來;這是來自矢口八虎的啟示。姑且就當作白話文版的「怎說Benedetta沒騙人!?」來看吧。
整部電影兩小時,我當然也在Benedetta到底有沒有說謊之間來回擺盪了很久。直到最後一幕她毅然回到修道院,我才確信Benedetta是真的對自己所說、所見深信不疑。如果說前一場火刑柱是教廷大使嗤笑「現在是你命跟你的『幻視』二選一,你確定你還要演下去?」,那麼這一刻,就是好不容易從死亡賭局裡逃生的Benedetta,自願再來一局。
(大使問Benedetta要不要用坦白自己是假聖人換取絞刑取代火刑,我心裡期待的是Benedetta屈服說好跟決定把戲演到底——我甚至心裡都替她想好台詞了,一句「我要擁抱火焰」,又有猶大、又有痛苦的死亡,完美的再演——二者選一,萬萬沒想到她居然走出第三條。)
Bartolomea作為Benedetta質疑者的代表,替我們講出心聲:「你我皆知你是假的,幹嘛還要自投羅網?」Benedetta的回應是:「因為我是真的。我回去,他們也傷害不了我——到時候你也好,那些質疑我的人也好,就都會相信我了。」看,這個女人,她用破碗碎片割破自己皮膚偽造出聖痕逃脫火刑,現在她要回去。回去做什麼?就算那是你的家,你還是得面對審判,到時候再偽造一次神蹟好逃脫嗎?這有什麼意義?沒有意義。所以真的就像她說的,她真的只是相信,相信會沒事、相信耶穌與她同在、相信她的聖痕(哪怕是自己製造出的也仍)是耶穌旨意⋯⋯而且是從頭到尾都相信。
她瘋了,對,她當然瘋了。在我們這些沒信仰的人眼裡,有著堅定信仰的人,哪個不瘋?信仰超越理性、凌駕以理智為條件做出的選擇,而不理智的行為,我們一律冠上瘋狂之名。而我們之所以會質疑Benedetta,其實也很自然,因為我們的理智就是無法接受這些神蹟的巧合。
「你那自己割出來的聖痕又怎麼解釋?」但Benedetta不是解釋過了嗎?她說,我無法決定上帝要以什麼工具實現他的意志。甚至就連不信Benedetta的主教跟Felicita也各自解釋過了:上帝不受人間的律法限制、Benedetta自殘當時可能精神上處於上帝帶來的「恍惚狀態」之中⋯⋯
簡單來說,如果上帝執行他的意志的方式,就是讓Benedetta進入恍惚狀態中,無意識地用碎片割出聖痕?這樣算不算神蹟?
「那又怎麼會這麼剛好,每次神蹟出現,都幫你逃出又一個危機?」——這個問題終究還是源於信仰不足。神蹟如何能用理智衡量,超越人的存在如何能以人間常識判斷?你若是信仰堅定,一開始就不會問這個問題。你(跟Benedetta本人)只會相信Benedetta確是天選之人,逢兇必得神助化吉,她的順遂中沒有人為算計,而是神之所願、是必然的結果。
《聖慾》裡沒有那種你一看就只能大呼「奇蹟!」的超自然現象,每一件發生在Benedetta身上的事,都容許你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怎麼辦,我想說的,Haseo全都說過了⋯⋯)
不過,「沒騙人」是否就等於「是真貨」?就算Benedetta完全相信自己的幻視是神蹟,有沒有可能她的幻視真的就只是,對,幻視?
延伸下去說,我們現代人還是可以提出一個假設:如果每次Benedetta遇上險境看見的幻視,都是突然蒙受巨大壓力產生的幻覺呢?如果她的幻視僅僅是精神病理學的現象,讓她在壓力下潛能爆發看見一個個逃脫困境的解方?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問,瘋狂跟信仰的界線在哪裡。到哪裡為止,我可以說這個人瘋了,到哪裡為止,我可以說這個人看見的東西是上帝顯現在他面前?我如何知道上帝顯現了什麼、上帝有沒有顯現什麼?我想今日的我們不知道,而在《聖慾》的那個世界裡,教會(權力)會告訴你答案。
(p.s. 正如Haseo說的:「能為了證明自己是上帝新娘而鑿出聖痕,這本身難道不夠奇觀嗎?若這真是貝尼蒂塔極限心靈狀態下產生的心身現象,不也讓我們見識到信仰的威力?」)
- 聖/慾
一旦我接受了Benedetta是絕對虔誠的信徒,我就得回頭面對她那明顯不合教規的性。首先,她是女同志(但我可以這樣稱呼她嗎?首先她就應該沒有女同志的身份認同),更過分的是,她還接受Bartolomea把聖母像削去下半身成為一根假陽具(也難怪Bartolomea要質疑她做戲;其他人還不清楚,她可是親眼看著Benedetta接過這根極致瀆神的情趣玩具然後享受它)。
對第二個疑問我沒有答案,偶然看到有人提到神的雌雄同體(?),或許可以由此出發。但關於她的同性性行為(對,我決定這樣稱呼),我倒是覺得有幾點解釋。
第一是她活在修道院裡!就像在女校裡一樣,整天被女孩子包圍,你當然很容易喜歡上女生呀。第二則是我比較在乎的,什麼同性不同性、貞潔或放蕩,對她來說都沒差。為什麼?因為耶穌不是說了,「在我之下沒有羞恥」。她也是這麼對Bartolomea說的,「你覺得我們很羞恥嗎?我不覺得,在耶穌之下我們不需感到羞恥」。Benedetta已經超越教義了;她不是跟隨教義,而是跟隨耶穌。
我願意相信當Benedetta跟教廷大使說,她對Bartolomea的愛是一股在小腹的「暖流」、由此她得到更多人的愛(大意應該是這樣),她說的是真的。我願意相信,她是真的這樣理解跟Bartolomea的關係:她們的愛包含了肉體的歡愉,但那不是全部,那只是更大的愛的一部分,甚至是通往更大的愛的橋樑。
我想到基督教神秘主義傳統裡神愛跟性高潮的連結。很多神秘主義的修行提到跟神融為一體的感覺,會用性高潮的詞彙說明。就算回到聖經,雅歌(Song of Songs)中也滿是令詮釋者頭痛的性愛;其中不少人會說,雅歌裡的性與愛,是一種人與神之間的愛的allegory。某種極致的痛苦與幸福共存的狀態⋯⋯或者,與神同在的精神狀態,在人世間只有性高潮可以重現/稍微相近⋯⋯

因此,在我看來,Benedetta跟Bartolomea的差別清晰可見:對Benedetta來說,這從來不只是慾望,更是神愛的一部分,她們兩個的關係也隸屬神聖秩序的保護;對Bartolomea則正正相反,Benedetta的神跟幻視從來都只是為了她們之間的人愛跟性——是為了獨立的房間好翻雲覆雨、是為了歡愉不是為了受苦。所以她的愛沒有偉大到願意為Benedetta承擔酷刑的痛苦;她承擔的只有一個人的罪,都承受不住,耶穌承擔全人類的罪,Benedetta也跟著追求在肉體受苦中理解神。Bartolomea是凡人,是那個跟你我一樣不信神、不信Benedetta的凡人,而Benedetta是Saint Benedetta。
- 最後,關於幻視⋯⋯
朋友不喜歡《聖慾》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她覺得基督顯靈那部份的影像做的很假、很廉價、很出戲。我也覺得,但我寧願相信這是導演刻意的藝術選擇。
在中世紀的藝術中,神聖圖像不可以真實;他們沒有好比例、好透視,肢體僵硬,神情呆滯,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界。要怎麼畫出一個不屬於這世界的圖像、怎樣讓人一眼就認出這不是我們這邊的存在?把他畫得不像我們這邊的存在就是了。
同樣地,如果在電影中要表現幻覺的話,要怎麼做呢?我覺得刻意把這個場面拍的跟其他場面差越多越好,或許就是《聖慾》的策略。超現實的場景、莫名其妙的耶穌、失真的色彩,至少我一眼就可以感覺到,幻視場景跟「真實」之間的斷裂。但我畢竟不是專業的,只是從我所知所感為《聖慾》辯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