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 斯皮瓦克:庶民以死发声

基础教育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在印度这样发展极不平衡、但又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国家。今天,如果你从加尔各答搭乘火车,之后转乘摩托车,就能抵达斯皮瓦克目前正在进行教育实验的场所——四所乡村小学。在那里,斯皮瓦克的身份不光是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知名学者,更是投身田野的教育实践者。
斯皮瓦克从学斋到田野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在政治暴力日益增长的当今,她怎样将希望投向“庶民”的基础教育,通过日常教育实践,与当地孩子和教育者展开对话?这背后又如何体现她对东南亚政治、公民教育的批判和希冀?
本文分为两大部分——前言与访谈。在前言中,何嫄梳理了斯皮瓦克的思想发展脉络,为我们了解斯皮瓦克生平及其作品提供了重要线索,并指出斯皮瓦克在庶民研究中的关键转向——从理论转向田野与实践。在啸风翻译的访谈正文中,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斯皮瓦克在转向了实践的同时,也在不断反哺理论,并指出自己在以往研究中犯错的原因。如其所说:“我搬到现在的学校。这里更像现代的印度贫困地区,而不是村民们仍被从前的封建地主保护着的人类学式‘部落’,我的证据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次的编辑工作于我而言,也是一次深度的学习过程。与译者和校者在翻译原则与细节上的碰撞和对话,通过前言进一步对斯皮瓦克的了解,都仿佛一场近距离的教学实践。作为结绳志教学板块的一部分,希望本文亦能教育、理论和教学上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原文作者 / 弗朗西斯·韦德(Francis Wade)
对话者 / 加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原文链接 /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culture/interview-gayatri-chakravorty-spivak/
原文发布时间 / 2021年7月6日
译者 / 何啸风
译校&前言 / 何嫄
编校 / 王菁
01. 何谓庶民
前言:斯皮瓦克及其思想脉络
本篇斯皮瓦克访谈由何啸风推荐并翻译,当“结绳志”主编之一王菁邀请我参与编辑这篇文稿时,我欣然答应,不仅是因为斯皮瓦克和庶民研究在印度历史和后殖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更是因为文中对教育理念的探索常常出现在我们曾经在上海纽约大学共享的那间九楼办公室里。
当时,我们讨论课程材料该如何兼顾西方和非西方的写作(知识的去殖民),如何在一个力求全球视野的课程中回应学生对身边事的关切(知识的在地性),又如何将我们珍视的理念贯穿到课堂设计和与学生的相处中去(知识的实践性)。这可能正是斯皮瓦克和庶民研究在经历八九十年代的鼎盛期之后,至今仍被人们提起,仍能给予我们的启发的魅力,也是这篇访谈对中文读者的价值所在。
加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女权和后殖民理论中耀眼的明星学者。她出生于1940年代印度独立前的加尔各答,以优异成绩在加尔各答大学英文系完成本科学业后,于1961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英语系博士,却因经济原因最终在比较文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研究用英文写作的爱尔兰诗人济慈。

1976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英语世界并不太出名,斯皮瓦克将这样一位不知名作者的解构主义著作《语法学》(Of Grammatology, De la grammatologie)从法语翻译成英语,也写了长长的译者前言将这一流派介绍给英语读者,从此受到学界的瞩目。
而她被更多人知晓的另一项学术贡献,是以1983年一份会议发言为原稿,并在1988年以书中的一章正式出版的43页论文《庶民可以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力持续至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访谈仍然在探讨这个话题。
英国文学理论特雷·伊格尔顿家(Terry Eagleton)曾经在《伦敦书评》一篇评论中,称她为“西方整个后殖民大厦的主要建筑师”【1】,并“率先将女权主义和后殖民研究传播到全球学界,或许她所作的长远政治贡献比她任何理论界的同事都要多”【2】。
然而,斯皮瓦克的学术写作风格并不通俗易懂,也因此常常受人诟病,连她自己都在公开发言中打趣说:“如果你读不懂,那是我的问题。”【3】但她的访谈和公开演讲则平易近人很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以此为入门方法。
关于“庶民”(subaltern)一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这个词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Antonio Gramsci)在他的《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中第一次使用,指“处在历史边缘的社会群体”【4】;另一种则认为这个词最早指英国军队中的初级士兵,后来被学界用来借指受殖民压迫的社会群体【5】。
斯皮瓦克本人在2004年于加州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则将它定义为“在社会流动性序列之外的群体”,是一种“不跟特定身份捆绑的立场”(a position without identity)【6】,因此在任何语言中也没有人可以说自己就是庶民。而这一被她称为“庶民”的立场,则是为了同时挑战殖民的、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写。
在《庶民可以说话吗?》一文中,她介绍了一位名叫芭杜瑞(Bhuvaneswari Bhaduri)的女性,她于1926年在其父位于北加尔各答的简朴公寓中上吊自杀。但特别的是,她去世的那天正来着月经,因此成为了一个迷。如果不是月经,人们会轻易根据文化惯性,猜测她是因为“不光彩”的怀孕才含羞自尽。
直到十年之后,人们才解开了这个迷:她是当地诸多致力于通过武力争取印度独立的团体一员。当时,她被委以一项刺杀任务,自觉无法完成,却又不想辜负组织的信任,两难之下,她选择了自尽。她一定是考虑到了,在妻子为死去的丈夫殉葬还普遍存在的社会里,自己的死会被解读为不法激情所致,所以特意等到了月经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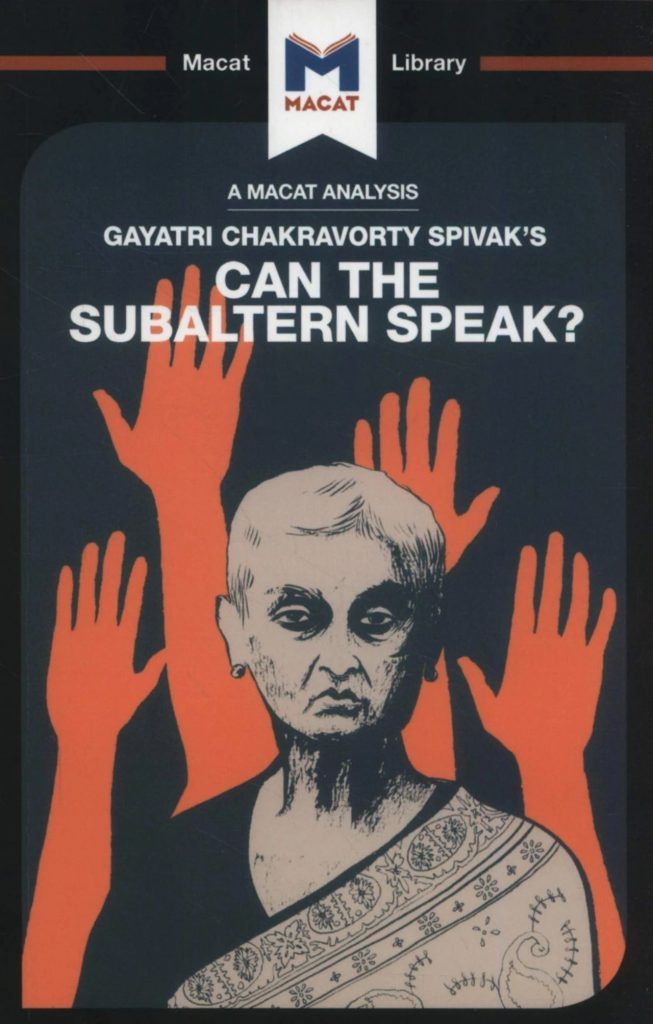
这是庶民女性对殉葬传统、对独立运动无声的抗争,但在很长时间里却未能被人解读和承认。斯皮瓦克由此把庶民,尤其是庶民女性的自主性、代表性问题带入了学界视野,并号召要重构一个庶民抗争能够被听见和看见的基础结构,而这一结构的核心是民主。
随着这一理念的发展,她的庶民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转向。如果说前一阶段,她的关注点在研究庶民群体,承认和看见他们的抗争主体性的话;后一阶段她则更多转向了田野与实践。
用斯皮瓦克自己的话说,“向庶民学习,以便能够设计出一种哲学或者教育方法,使得人们在公共事务上能够养成民主的习惯和机制。”【7】 她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以一种公民的姿态去参与、要求和改变它,而不是一味拒绝并接受被它排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访谈,正是这一转向的介绍和体现。
02. 访谈
如何塑造心灵,又不说教?
Q:您在西孟加拉邦的农村指导小学生进行“培养民主习惯的仪式”。这是什么意思?
A:我在村庄中寻求解决的智识难题是:几千年来被剥夺独立思考权利的人,如何学会一种有想象力的、实干的思维方式?
我不直接讲授民主理论,我教他们英语、孟加拉语、算术、地理——西孟加拉邦的公立学校课程。但最重要的是授课方式。我做的诸多尝试之一,就是想让学生意识到,真正聪明的人不总是回答老师的问题。
如果我们阅读法农,他知道后殖民社会的一个切实问题是领导者的存在,以及想当领导的憧憬。法农、我、葛兰西都一直在说,在普通、日常的治理结构中,比如在美国,存在着这种领导情结,它是很有害的——它完全是非民主的。下到村庄里,那种领导者几乎都是骗子的糟糕领导局面,是下面村庄政治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该如何塑造孩子稚嫩的心灵,同时又不对他们说教?我们如何教学生养成习惯,知道何时不去为胜利而斗争?我想让学生们觉得,想领导班级,每次都回答问题的做法是有点傻气的。我让他们看到,哪怕我知道答案,我也没有[总在]回答问题。所以,这是一种民主的习惯——他们随我养成习惯不想去领导,或者知道抢着领导很傻。
Q:对于这种教学风格,甚至对于您的出现,学生们总体上配合吗?毕竟,您是一个在贫穷、边缘化的社区工作的婆罗门,您“来自”哪里,他们来自哪里,有很大的差别。
A:我在村庄中通过亲历亲为的工作,想弄明白是否可能消除我这个种姓犯下的历史罪行,也就是制造了“不可接触”(untouchability)制度,以及高种姓眼中的下等人。我们[婆罗门]不接触这些人。哪怕天气再热,我们也不和他们分享水源。哪怕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也被拒绝了从宣称是我们的池塘里喝水的权利。
现在,这些限制逐渐放开了,可是,内心的感觉没有消失,种姓的偏见依然盛行。如果认真检视种姓制度,人们也应该这么去做,我们就会意识到,真正的难题是他们认为压迫是正常的,因为种姓制度是神创造的,而不是人。像“民主”这些概念,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可却不适用于这些人,他们是种姓制度的受害者,认为只有我们[高种姓]才持有“民主“这样的想法。

Q:人们经常感觉,莫迪的任期里,暴力作为政治工具被使用得更频繁了。您接触的孩子们如何看待暴力与政治的关系?
A:我总是以一件时事开启一堂课。上一堂课的时事是当地的选举,班里最大的孩子十岁,八年后就要投票。所以,我问他们对选举有什么看法。最聪明的孩子之一,九岁的拉姆·班达里·洛哈尔用英语说:“选举是游戏”。
我总是用英语开始上课。我说:“说得很好。接下来,用孟加拉语解释一下,为什么选举是游戏——选举是什么样的游戏?”我慢慢地跟他说。他用孟加拉语回答我:“是斗争”。
你看,村庄里充斥着暴力。在这个层面上,人们不懂政党政治是不可能的。不像在美国那样,这里的孩子不可能安心地当个孩子。尽管如此,这也是我们在村庄里的成功例子之一。
拉姆可以讨论一些具有更广泛内涵的事物,像我们在美国谈论的一样。某些议员和当权者竭力避免这个男孩接触到的真相:选举政治中存在的暴力是一个全球现实。这种现象不局限于村庄。我们在1月6号的暴动[川普支持者攻击了国会大厦]中看到了这一点。从这个男孩的回答中,我们不能下诊断说暴力只存在于印度村庄,还应该学到更多东西。
你成为一个公民,直面风险
Q:在2004年的文章《Righting Wrongs》中,您就布克·华盛顿与威廉·杜波依斯一个世纪前,关于庶民群体如何获得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持久争论,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您写道:“我赞同杜波依斯而非华盛顿,培养批判性智慧比获得当下的物质满足更加重要。”您能展开说说吗?
A:我在中国做了很多工作,两年前还与云南周边各省的的女性组织进行对话。她们告诉我各项省级改革都是为了创造收入。我试图在《Righting Wrongs》中指出,杜波依斯认为,比起一味强调教育是增加收入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培养人做决定的智识,使他们可以决定,到底是去创造收入,还是干点别的,比如培养一种做好事的意愿。

在这之前的一句话中,我在《Righting Wrongs》中正是批评美国:“一些美国慈善家的恩赐恰恰是罪魁祸首,让庶民产生一种普遍的剥削欲望。”保罗·弗莱雷正确地指出,假如不对被压迫者进行教育,那么,被压迫者会想成为一个个更小型的压迫者。弗莱雷没有把被压迫者浪漫化。这也正是我想说的。这也是华盛顿与杜波依斯的对立之处。
Q:《Righting Wrongs》中,在您详述了从当地管理部门处获得一口管道井的屡次失败尝试,也拒绝了“远方的国际慈善机构”可能愿意提供的相同设备后,您写道:“我们希望不需要发表短期的抵抗言论,就能让孩子们知道当局的冷酷无情。”为什么孩子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A:我那篇文章的说法是错的。我[文章中写到的那些当地村民处获得的]证据,有太多感情色彩。后来,我搬到现在的学校。这里更像现代的印度贫困地区,而不是村民们仍被从前的封建地主保护着的人类学式“部落”,我的证据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现在,我对待这一问题的新思路倾向罗莎·卢森堡式的社会民主,即利用邦政府,而不是仅仅认为邦政府冷酷无情,并告诉孩子们政府多么冷酷无情。我认为之前的想法是一个错误。当我转向现实世界,我的基本方法是:从错误中学习。所以在这点上,我所犯的深刻错误是,认为我们应该说:“没错,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卢森堡和葛兰西认为,国家既是解药,又是毒药。你要学会利用它,让它不变成毒药,即使会因此遭受惩罚。你成为一个公民,直面风险。
不过,我也教会了学生一个事实:邦政府因为我的存在,还是为他们做了些事,因为我在孟加拉邦认识人。我告诉学校的管理层,邦政府人员只应该为你们工作,因为你们是公民。我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个好人,我的父母也是好人,但是,仅仅两代人不足以消除几千年的压迫。没了我,你们也应该要自己实现。”那就是重新塑造这个邦。当然了,一次又一次,都行不通。但是,我不断地强调,而且,其中和我一起工作最久的两位学校管理层,确实试着去独立挑战邦政府。
Q:在印度或其他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仅仅是因为国家不关心贫困学生的前途,还是你觉得那是一种蓄谋:政府故意维持一种阶级区隔(class apartheid)?
A:想要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肯定是所有社会形态的现实。我很难说,哪个原因导致教育质量的鸿沟,每种情况都有自己独特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说,教育的鸿沟是为了让大部分选民缺乏批判性的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能让他们明白投票规则,明白国家不是敌人,而是选民所塑造的事物。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个秘密不想让公民知道。国家不是公民的敌人,而是公民的工具,只有这个工具干干净净才能正常运转。
国家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最好自上而下地把物质利益分给大多数选民。选民们会对自上而下的封建仁慈感恩戴德,从而选举出暴君。我告诉学校的管理层,虽然他们可以得到足球奖学金,但是,国家绝不会让他们独立思考。他们之所以不能独立思考,是因为上层阶级几千年来一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现在的统治者也依然如此。这个道理,有必要与他们讨论:如何独立思考?如何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等等。这些就是我想要教的全部内容。

Q:邦政府抛弃村庄了吗?人们很容易认为,村庄如此被忽视,邦政府是完全缺席的。
A:这些底层人民并没有被排除在邦政府的控制以外。邦政府需要他们,邦政府也利用他们。对于这些民众来说,邦政府无处不在。村庄里,为了阻止人们投票给印度人民党(BJP),草根党(反对党All India Trinamool Congress,即全印度草根国大党)为所有村民接种疫苗。加尔各答的接种政策不太好,但看到即使最穷的人也接种了疫苗,这让我惊讶。因此,邦政府无处不在。虽然穷人无法享用公民权带来的便利,但他们一直为邦政府所用。
Q:多年来,在缅甸的大规模暴力问题上,您多次表达了强硬的立场。现在,由于缅甸军方不断将反抗力量推向新的极限,全国掀起了反军方的运动。这对您有何触动?
A:缅甸的情况就是卢森堡所说的“自发性”(spontaneity)。这不是心理层面的自发性,而是沉重而漫长的无情压迫导致的社会动机。无数的暴力、剥削、压迫,持续太久了。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早已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真的不害怕死亡。这是很奇特的事。
法农以精神科医生的身份说过,虽然有基本平等时,人才成为人,但一旦置身于否定生命平等的地方,人们就会产生极端的暴力。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中,人们也会失去对死亡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底层人民只能以死亡来发声,就像布瓦吉吉[引发阿拉伯革命的突尼斯商贩]和[乔治]弗洛伊德[因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的非裔美国人——校注]那样。
可是,这种情况不会持久。大卫·罗迪格提出一个很好的理念,叫“革命时间”。他认为,在政治的紧急状态中,正如今天的缅甸,人们做出许多情急之事,甚至可能失去对死亡的恐惧。尽管“革命时间”强度很高,它没有持续的能力;一个能够带来改变的永久政治结构也无法基于这种浓缩的时间。
正如葛兰西所说,我们不能用炽热的政治激情来建立永久的政治结构。因此,虽然缅甸发生了不同凡响的事,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必然会持续下去。突尼斯没有坚持下去,埃及也没有。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得太早,但它很有力。我们的角色不仅仅是旁观者,最好可以作为一种国际声音加入它。
译者
何啸风,毕业于安徽大学,研究兴趣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
译校&前言
何嫄,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博士,伦敦大学学院教书匠。
Reference:
1. Terry Eagleton, “In the Gaudy Supermarket”, 《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21 No. 10, 13 Mary 1999,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21/n10/terry-eagleton/in-the-gaudy-supermarket.
2. 同上
3. Gayatri Spivak, “The Trajectory of Subaltern in My W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elevision, 20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ZHH4ALRFHw.
4. Joseph Buttigieg and Marcus E. Green edited, Subaltern Social Groups: A Critical Edition of Prison Notebook 25, Columbia Univesity Press, 2019.
5. Terry Eagleton, “In the Gaudy Supermarket”, 1999.
6. Gayatri Spivak, “The Trajectory of Subaltern in My Work”, 2004.
7. 同上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116. 男女不平等,有悖于伊斯兰
117. 作为左翼的萨林斯
118. 哲学人类学:饮食之道(上)
119. 底层北京:与艾华对谈
120. 为什么需要反思单配偶制
121. 哲学人类学:饮食之道(下)
122. 杀子献祭,疯了吗?
123. 哲学人类学 | 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后殖民研究与马克思学(上)
125. 斯皮瓦克:庶民以死发声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