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得远了,会忘了当时头也不回要离开的理由。
情感丰沛地流淌,像你会独自漫步的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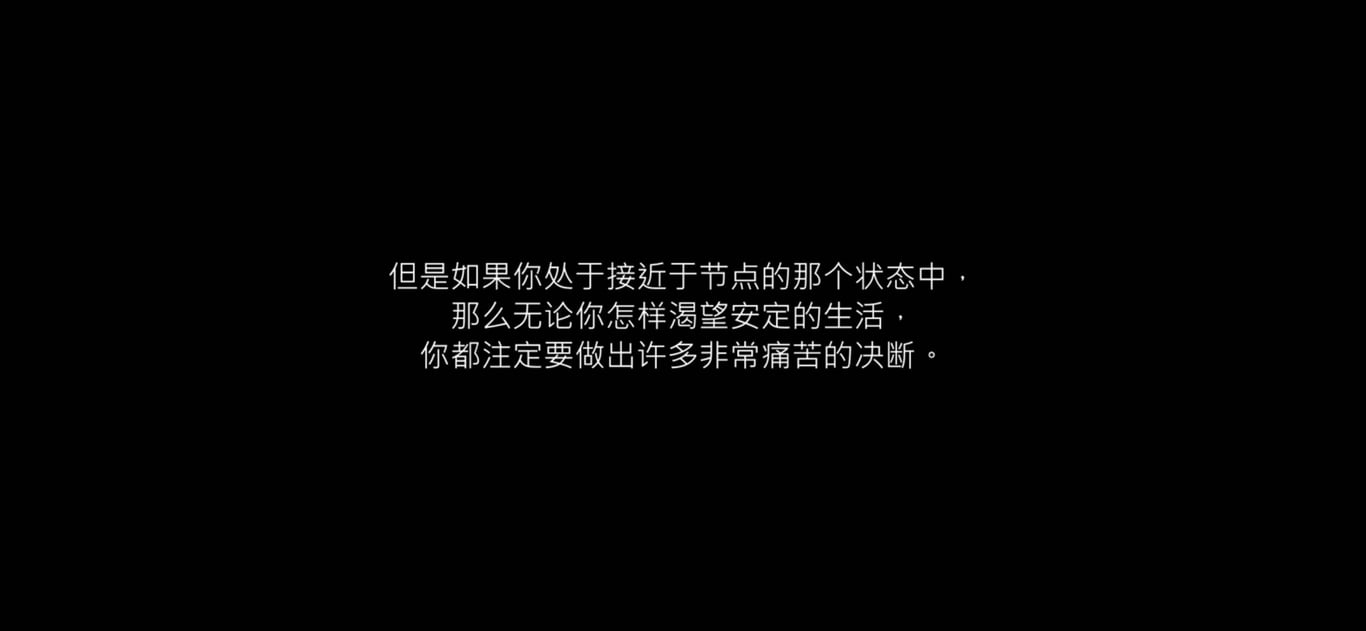
窗外有一堵斜斜的石墙,棕色的,表面粗砺,符合心意。墙下还有一块孤零零的石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尺寸恰当极具存在感的椭圆——大了是威胁,太小则微不足道——仿佛无意间掉落在此,无心插柳柳成荫,构成了一个“作品”。这作品令你想起Maya Lin。墙边的树,自是开着夏天的花,一簇簇细小的白色,风也吹不落。你见一个戴着墨镜的女子来加油,又见一个中年男子,在一部宝马后面来回来去地走,受气包的样子。你恐惧人,但如果有面玻璃隔在你们之间,你就可以研究他们一整个下午——对标本的兴趣。
另一个方向,不敢相信,停着你的车。六年前,你还只是美国的一个游客,开着从Hertz租来的日产SUV,后备箱里塞着两只硕大的行李箱,一只红色的,一只蓝色的——你和丈夫的身家性命。你总记得开着车行驶在圣塔芭芭拉时,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棕色的紧身运动衣在街道中间跑步。她轻盈地跑过一棵又一棵临风的棕榈树,似乎是有数不胜数的闲暇,在时间中任意支配游走。这一幕令你产生惊奇,记到现在。你对路边的车也惊奇,每见到一部车都忍不住想:它们有主人,它们的主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在美国有一部车,这意涵丰富地指向某种生活,某条道路,某个来处,沿途的风雨,以及抵达时终于松了口气。多年后丈夫提起你们初次抵达美国的旅行,只说:那时候你真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脱离实际,浑不知谋生为何物。
麦当劳空荡荡的,像旅途中暂时落脚充电的地方,于是你又像游客了,你吃麦辣鸡肉汉堡。毛玻璃隔板那边独坐着个西班牙裔老头,面部松弛,神色严厉,可能孤独了太久,无人陪伴。但你不是游客了,你能听见几十米开外有人在说:F**k you。游客不该主动打破这异乡语言的墙与禁忌。但你需要一面屏障,一种写字楼都用得上的,这面看得到那面那面却看不到这面的玻璃。你走得过去,可他们走不过来,烦了倦了,就关掉听觉神经,关掉那条通道。因为,这也是你很久之后才恍然大悟的:懂得一种语言,就是赤手握住刀刃。
回家的路上经过教堂,礼拜天的弥撒刚结束。左转车辆纷纷减速,耐心地等一个姑娘过马路。你探头望去,竟是个不施粉黛的中国姑娘,马尾辫,戴眼镜,怀里抱着披萨盒子,嘴角一抹微笑。她让你想起自己也曾这样在烈日下走,心中满是对崭新生活的渴望,与那种要与一切逆境搏斗的蓬勃的勇气。其实你是个多沉重的人,但走起路来总是高昂着头,目不斜视,健步如飞。因为你不再是美国的一个游客了——游客才会冲前台、旅行社、空姐,发脾气,因为游客不必对她的旅程负责,她总能找到一个责任方,将她的不快乐通通归罪于他人。
教堂在远去,以及意大利面包店,以及窗帘全部放下抵挡烈日的咖啡厅……你望着车窗外加速倒退的风景,猛然意识到你已经达成了某种愿望,某种联系,某种拓扑结构上的,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至于那是不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who cares。一个紧随其后的更大的顿悟:人在获得或失去一样东西时总是不自知的,因为潜意识还有惯性,还在抵抗,还悬置在那不可置信中。
不敢相信。像几年前中国流行的电视剧:一个只能算得上炮灰的角色也可以在夜色中昂然而立,对着某幢灯火通明的高楼发誓:总有一天,这里面会有一间办公室是我的。不敢相信,这奇异的感觉就一直追逐着你,似是一根敏感的细线牵动着,让你动不动就不声不响地流下泪来。甚至那些莫名其妙的,毫无关联的,例如Southwest的飞机在晴空下转弯,品川的海豚掀起白浪,都让你流泪。你努力思索过那泪水背后的缘由,却怎么也想不清楚。情感是那样丰沛地蜿蜒流淌,像你会独自漫步的广袤无际的草原,地平线上还有个人向你走来。那瞬间杂糅着恐惧与欣喜:他既可以一枪把你打死,又可以让你知道:天空之下,你不是唯一一个人类,可以坐下谈一谈。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