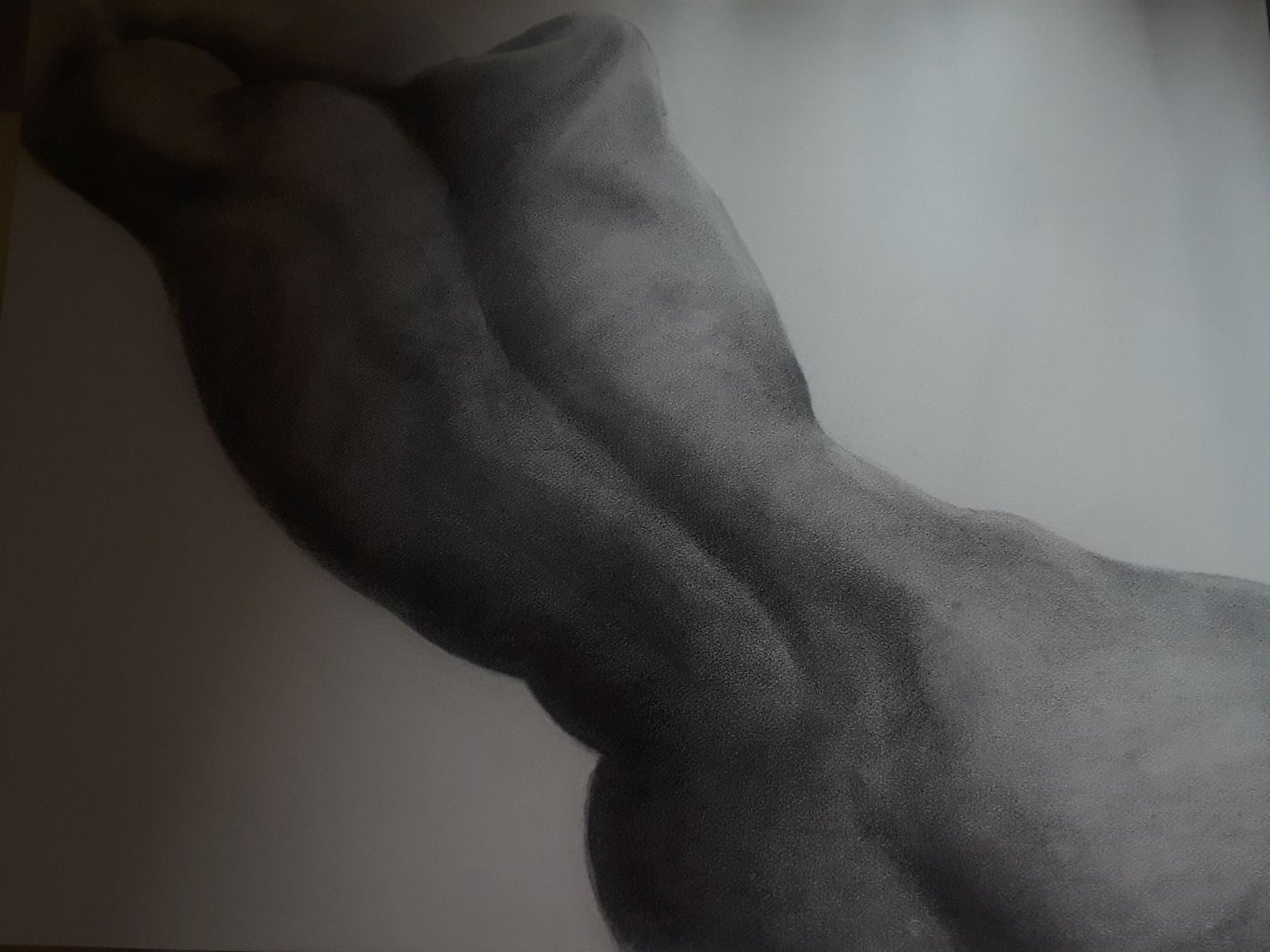

風月同天
2021的聖誕節
每年聖誕節都是在 New Jersey 的姊家過的。去年此時正值疫情高潮所以沒有聚會,今年雖然又出了個Omicorn 新變種的病毒但還是決定如期舉辦。我,姊姊,姊夫,外甥,外甥女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共八人的聚會。我們早早的都施打了第三劑加強針。
青春印記
青蔥翠綠的年歲裡,誰人不是昂首向陽,蓄勢待發,殷切地期盼未知,期盼愛情... 剛來紐約時暫住在布魯克林區的姊家。姊夫在華爾街律師樓上班,早出晚歸。姊在家帶二個可愛的稚齡孩子,可想而知她的慌亂生活,我也剛好可以幫她帶小孩。一開始是新鮮,好玩的,可是等學校開學後就有了課業的壓力。

那些花兒 《三》
步出辦公大樓時天色尚未全暗,亮晶晶的燈光從各大樓的窗格內散放出來,週五夜晚的氣氛確實不同,街上的紅男綠女步履輕快,笑語宣譁,天經地義般的歡快。我一路來到了中央公園附近,自忖著也許去趕場電影.. 『John!是你嗎?』身後傳來了高吭的男音。『天啊!

那些花兒 《二》
風急火趕的進了公司的門,前台的Cindy即刻叫住了我,壓低了聲音說『Robert剛走,之前一直瘋狂的在找你!』 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繪圖桌上一張便利貼寫道: 『撐不住了,先走了!下午幫我去見一下那古董布花掮客,選些下一季度的面料花色,還有..剛開完會,有些需要修改的圖稿,星期一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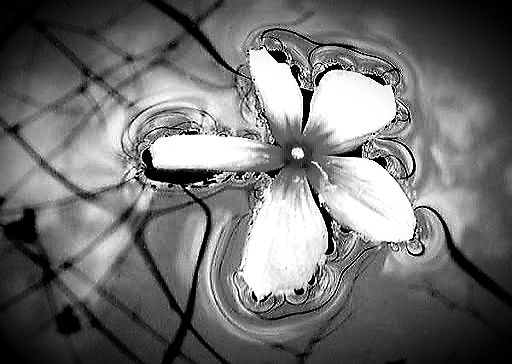
那些花兒 《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紐約 那是沒有手機與網路的時代 那也是個危機四起的年代 那日的的雲層很低,帝國大廈的頂端在雲霧裡乎隱乎現,是個悶熱的秋老虎天。中午用餐時間的交通混亂,計乘車是叫不到的,我一路過三關闖五將,殺過十幾條街,好不容易在一處人聲嘈雜的喝啡店坐定下來。

盛夏的紫薇
盛夏時節在紐約各處也有不少的紫薇花在豔陽下隨風舞動。第一次聽人說此花之名時還傻愣愣地問是還珠格格中的那紫薇嗎。自從認識了她,偶爾會在街角或公園裡不期而遇。有一次垂頭喪氣的走在一個人聲,車聲嘈雜的街口,天氣又悶又熱,猛一抬頭,那一簇簇紫紅色的紫薇花就在眼前,心情為之一振...

隱忍與放飛自我
退休之後心態上有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是眼睛裡揉不進一點沙子了。以前或許可以忍耐或輕巧帶過的人,事,現在不忍了... 一位“老朋友”, 在以往的交友過程中三不五時會被她情緒暴力,一路忍耐著過了三十多年,現在看來簡直就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我是何以接受這一切...何以吞下這些負能量的...

夜半私語
夜涼如水,睡前讀到一則佛偈:「一啄一飲 莫非前定」意指人生中的所有人事際遇皆有命定,絕非偶然。思緒回到五歲時父母離異,我們跟著父親生活,而後那位後媽的出現著實給我們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我12,13歲的時候祖母因病住院,父親那時是以沖喜之名草草且快速的續了絃。

霜白
多年以前在紐約中央公園裡偶遇大約有十多年沒見的老同事, 彼此都別來無恙,記得以前的她是光彩照人的,那次見了佛彷如同隔了層薄紗在看她,又好似她剛從霜天裡走出來,灑了層霜,華光褪減。然而氣質依舊且添了份從容。疫情期間決定不染頭髮,待染料退盡的時侯,鏡中的自己不也如同褪了色般。
黃昏的渡口 (下)
有一天我問他,我已經準備好要跳下水了,你呢?笑而不語是他的回應。我見了二位塔羅牌老師,各持正反二面的看法的。我參遍先知聖賢之書,而情是什麼,我同意一位古希臘聖賢說的 : Love is divine madness. 當時有位菲律賓朋友帶我一同去望彌撒,我並非天主教徒但欣然前往 ...

黃昏的渡口
雀噪高枝上 行人古渡頭 半途不了事 日暮轉生愁 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剛從建身房出來,走在回家的路上,總覺得背後有雙炙熱的眼睛在盯著看,一轉身,笑臉迎人的說了聲嗨,短暫的對答也交換了聯絡電話。那是個秋天的下午。第二次見面約在一家他提議的泰國小餐廳,老闆娘很熱絡,對我們有些曖昧的笑著。

張愛玲曾經的天長地久
上海靜安區常德公寓常德公寓舊貌( Eddington House )常德公寓,這幢位於上海靜安區常德路上的八層樓公寓,原建於1936年(當時還是法租界),是一幢在當時相當潮流的Art Deco風格的公寓建築,原名Eddington House.

潑了重彩的陳年往事
張愛玲出生的上海老宅現址上海康定東路85號左為張父張廷重,右為張母黃逸梵張愛玲是在上海出生的,就在這棟(黑白老照片中)十九世紀末建於蘇州河畔的花園洋房中。這看似鬼影憧憧的老洋房可不簡單,當年晚清重臣李鴻章 (張愛玲的曾祖父) 買了這棟洋房做為給女兒李菊耦的嫁妝,李菊耦嫁給了也同是晚清名臣的張佩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