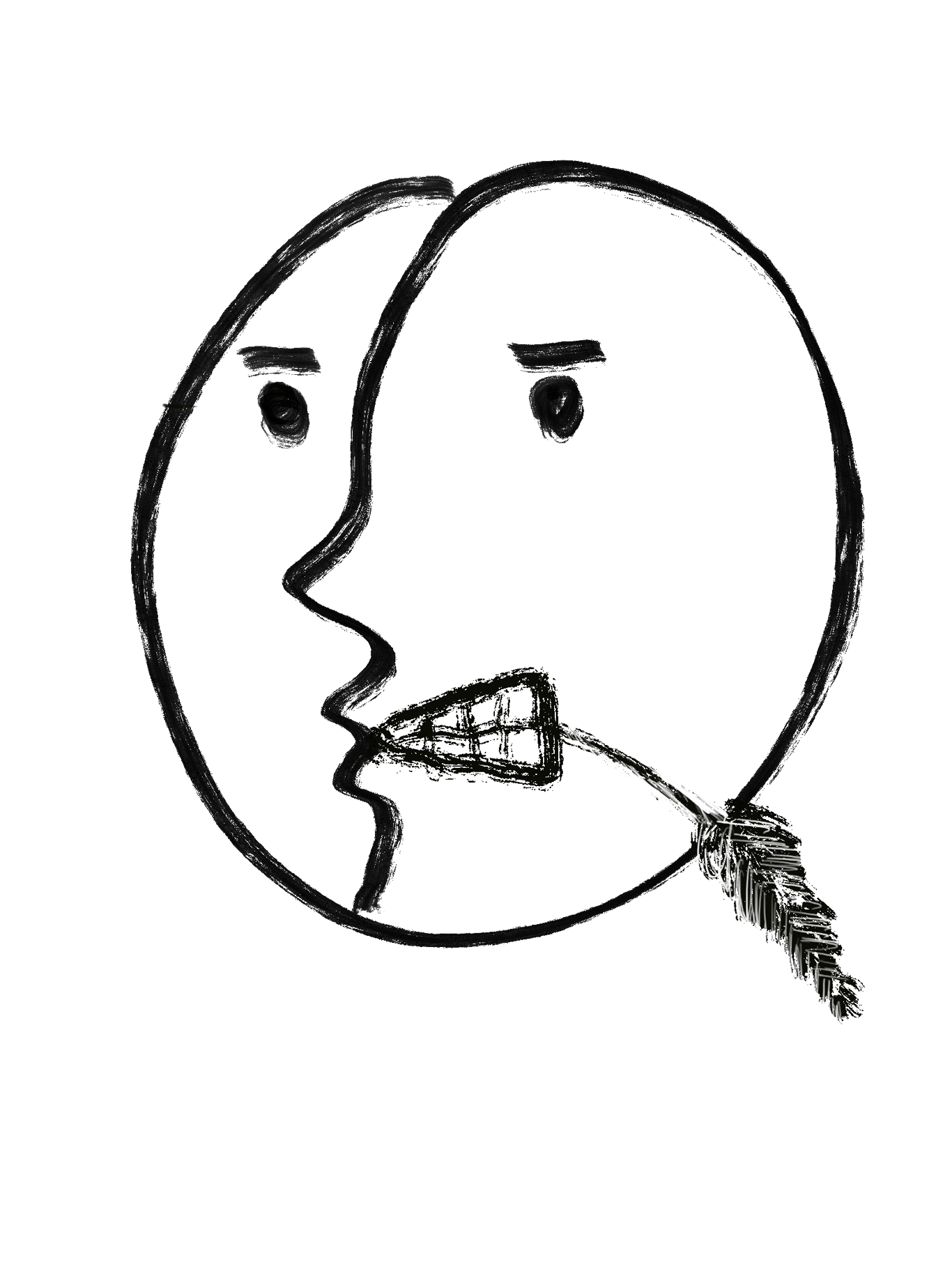
學中世紀哲學,暫時還沒死的怪咖野人。正在學習如何假裝人類。 ⋯⋯ 喔幹,學不會。
不好玩的沒用小說|阿卷
〇
我在Z大學念書時,學校裡有位叫阿卷的名人。阿卷總是戴著一副大陸時期很流行的圓框金絲眼鏡,頭髮油膩到一絲不苟。有時在校園能看到他低著頭趨步走過,有時又會看到他昂首挺胸、雙手背在身後,一副傲視萬物的樣子。他身上永遠都裹著同樣一件灰夾克,雖然有點舊,但每次打掃前,阿卷都會仔細地脫下外套、折起來放進塑膠袋,從那上面找不出半點汙漬。每年都會有將近一半新生把他認作醉心研究的老教授,畢恭畢敬跟那張嚴肅的臉打招呼,時間久了,還會偶爾有新面孔因為不打招呼就被他訓斥「沒禮貌」。
但其實他是學校清潔工。
我們文學院裡一位年輕助教,算是全校師生裡面,阿卷唯一承認的「熟識」,有天下午研討會的休息間隙,助教站在橋邊,抽著菸,把阿卷的故事當作一個人文笑話講給我聽。
一
阿卷很愛讀書,什麼書都讀,什麼書都讀到一知半解。他當年原本過來學校應徵圖書館的職缺,助教那時剛入職,也在一旁幫忙。校方這邊很有面試經驗,第一個問題就問他只有腦袋正常的人才會回答的問題,「學生歸還的書要怎樣放回原來的位置」。阿卷果然不負眾望,他用鼻孔指著那位提問的組員,從牙縫裡略顯輕蔑地擠出一句話,「從哲學上講,要想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問學生當初是從哪邊拿到這本書的……」組員很粗魯地打斷了阿卷的回答,「抱歉,您還有其他話要講嗎?如果沒有的話請幫忙告訴下一位應徵者過來這邊。」阿卷雖然外表一副書呆子樣貌,卻意外地懂得審時度勢,「你們還聘清潔嗎?只要讓我留下就行。」伴隨著略顯怯諾的聲音,原本揚起來的鼻孔稍稍收斂了一點,鏡片背後的黑眼珠也跟著沒精打采地垂到右邊的地板上去。
這誠意寥寥的情勒味,那位組員竟然覺得有些可笑,又有那麼一絲同情。「剛好這邊有位阿姨臨時請假,之後一周你先幫忙打掃下廁所,薪水的話……」廁所兩個字彷彿觸到了阿卷殘餘的一小粒英雄氣概,「我堂堂七尺男兒,你居然叫我去掃廁所!」「阿不然你以為清潔是要掃什麼?掃墓喔。所以你要不要做」組員平靜的語氣好像有嚇到阿卷,阿卷的眼睛又看回地面,羞澀地點點頭,就算應下這份工作了。「那……」阿卷開口還有一點猶豫,「請問我可以借一下掃把嗎?」組員有點吃驚,「啊不是,明天才上班啊……」「啊不是啦,」阿卷顯得有些侷促,「我是想要借回租屋一天。」「啊……喔……哦哦……」直到阿卷拿到儲藏室鑰匙並完全消失在組員的視線中時,組員的神情都還在恍惚。
第二天助教上班的時候剛好又遇見他,穿著跟現在都還一模一樣的衣服,點頭打了招呼,見到阿卷舉著的掃帚柄上有幾個字,就跟他要過來看,看到上面用毛筆工工整整寫著「周利槃特迦」。助教從此對這個人有了一點好印象,有時偶然遇見又不忙的時候,就會聊點瑣事。
二
阿卷過去當過四個月兵*,不想再回去部隊了,就算真的要打仗也會躲起來,據他自己說是因為沒辦法容忍長官踐踏他的骨氣,但誰知道呢,至少他過來的時候,並不像那種會為了一點骨氣就放棄蠅頭小利的人。
不管嘴上說的討厭武力還是內心對死亡的恐懼,兩種都可能是他喜歡看書的原因。助教也試探性地問過他為什麼不唸大學,他也只是支支吾吾說不喜歡考試那類東西束縛他自己的想法。是在很久以後,當他們的談話稍微涉及到某些基礎概念的時候,助教才發現阿卷其實是那類人:理解能力很差但又固執地相信自己的解讀才絕對正確,一直覺得別人跟他想法不一樣,只是因為別人沒達到他的深度而已。助教也曾試圖用邏輯幫阿卷分析他想法裡自我衝突的地方。阿卷沉重地哼了一聲,「那只是你的邏輯,你們的死邏輯。」那時還小心翼翼的助教也沒敢再多說什麼,擔心阿卷想要批判自己的邏輯,那樣恐怕就再也聽不到他親口講的笑話了。
雖然阿卷討厭「別人的」邏輯,但相關的書他還是會去翻,只是每次遇到入門書裡面的測試題,多多少少還是會受到些打擊就是了。
所以他所謂的「愛學習」也一樣,其實阿卷過來的第一年很喜歡旁聽教授們的課,但因為他每次長篇大論提出些無關痛癢的問題,浪費掉上課的時間,教授們就很無奈,有時候認真回答,他也聽不太懂,沒辦法做回應,又只能返回去重複他自己的問題,時間久了,教授就不准他進教室旁聽了。但阿卷的求知慾跟好奇心並不會因此而磨滅。學校裡大大小小的講座他幾乎一場都沒錯過,就算時間上有衝突也會拜託大一同學幫忙錄音,嗯,因為只有大一同學有機率尊敬他。每次散會,只要主講人是校外有些名氣的學者,阿卷就會跟身邊的大一新生大聲讚賞這位學者,表示極其贊同他的某些觀點;但如果換做是學校裡這些教授,阿卷就嚴詞「批判」。畢竟批判這種事對阿卷而言輕而易舉,只要哪一句話與自己印象裡的古代知識不符,說他違背了最「正統」的知識,這樣就很容易利用古典知識使自己顯得沉穩。至於這種反駁是否出於真心,這並不重要,他只需要收穫到沒知識新生們崇拜的眼神就好。
三
阿卷念國中的時候,有次逃課混入附近大學去聽講座,不知道主講人是誰,也不曉得要講什麼,只是學著大哥哥大姊姊們的樣子,面前擺著一個空白筆記本,右手在把玩一枝素樸的水筆,頭微低、輕輕皺著眉頭看向黑板。
阿卷直到講座結束的時候才知道,這次過來的是M市的一位中年哲學教授,但教授入場的時候,阿卷其實有點失望,上面站著的就是一個瘦瘦的普通阿伯,穿著有點舊的灰色西裝,「這樣乾癟沒氣質的阿伯怎麼可能講出什麼值得記下的格言嘛,唉。」阿卷本想逃,可惜他的位置已經被學生們圍到水洩不通,坐在中間的阿卷根本就沒辦法出去,無奈的阿卷只好閉上眼睛、集中精神,默背早上讀了八十二遍的古文名句,沒過多久就睡著了。
等到阿卷從長大變成一流學者的美夢中甦醒過來時,主持人已經在做結尾了,最後隱約只聽到一句話,可能改變他人生的一句話,「感謝大家和哲學家羅教授參與這期講座,那今天的活動到這邊就結束了,請大家退場時記得攜帶隨身物品。」「這阿伯是哲學家?」年輕的阿卷突然來了精神,眼神裡充滿了崇拜的光,一下子轉向右邊手舞足蹈:「筆記,拜託給我看你的筆記!」右邊的女生顯然被嚇到,乖乖打開筆記本,有點害羞地說,「麻……麻煩快一點,我等一下還……還要出去。」
著急的阿卷看著難以辨認的字體有點不知所措,就手忙腳亂選出幾個認識的抄下來:「破圈」、「逆境」跟「哲學家」。
散場的時候,坐在阿卷左手邊的學生A對學生B說,「嘁,你知道嗎,這個羅阿伯吼,他老師死掉以後他自己都沒寫過什麼厲害的東西餒。誰曉得他以前那些厲害的理論都是從哪來的呢。」阿卷聽到這句話,臉馬上漲得通紅,站起來對A吼到,「他很……很厲害,你根本就聽不懂啦!」但由於當時人聲嘈雜,幾乎沒人聽到這句話,越想越激動的阿卷哭著衝出了會場。
四
後來阿卷還沒唸完中學就輟學了,用那三個匆忙記下來詞,在家裡寫書。「我還滿佩服他的,」助教評論到,「我寫一篇論文還要找別人幫忙翻譯好幾篇外國論文,他寫一本書要三個詞就夠了。」助教嘴角笑容上的嘲笑明顯大過無奈。那本書助教讀過——其實只是隨便翻翻,習慣性地用平時評論教授文章的方式禮貌性地捧了幾句。雖然阿卷嘴上說助教根本沒看懂,但內心已經把他當作生死之交了。這也是後來阿卷告訴助教的。當時的助教聽到這件事,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人生的空虛。
後來的阿卷幾乎有空就去找助教講話,他聽著這些重複又空洞的語言,偶爾還夾雜著一些專業名詞,不過多數聽到的,都是阿卷對主流觀念的牢騷,只要是學校裡稍有名氣的教授,每在網路上寫一篇文章就會得到阿卷的嘲笑,不管是否讀懂,阿卷覺得,批判才是最重要的,比理解更重要。反對別人的觀念就是他活著的意義,為此他也讀了些書,大多是各學科的開山作品,比其他書讀得認真,還要把定義句都摘抄下來。助教講到這邊就開始忍不住笑起來,「我真的被他笑死,他一直以為學科的開山作就是學科的標竿,誰的觀點跟老祖宗的觀點不一樣他就去罵誰,沒人願意浪費時間反駁他,他就變成是那個唯一正確的人了。」助教抹去眼角笑出來的眼淚,接著說,「他覺得自己在破圈,在破文化圈,在破學術圈,但用過時的傳統破圈,這我還第一次聽說。他甚至有一次還拿十年前的中學作文過來給我炫耀,說他當時研究完外市哲學家的演講就看透整個行業了。但是啊,雖然在你我看來他沒什麼文化,但他在做的事就是沒人敢做,就算親眼看他們把翻譯過的外國論文署上自己姓名,也不願意講出來砸了自己的飯碗,索性自己也跟著做,融入到他們之中,等有一天熬到他們的位置上,我可能就自由了吧。或許能像阿卷一樣自由。」助教輕輕嘆了口氣,「但阿卷真的自由嗎?他也被禁錮在已經死掉的古人裡。但是他有罵出來,就像在幫我罵出來一樣,那沒文化就沒文化吧,他自不自由的,關我屁事。」
這時候橋邊的空氣裡已經明顯聞得出大麻味,助教把最後一根菸蒂扔進河裡,撇撇嘴說,「回去吧,不然就沒出息了。」
這是我跟助教相識的第九年,最後他講出最令我震驚的一句話,「我還滿同情他的。」
五
隔天我在橋頭遇見他們,助教又在呼大麻,這次顯然已經呼到有一點ㄎㄧㄤ掉,所以格外有興致地在跟阿卷講話。
「你怎麼想到要努力寫作?很花時間,又沒什麼報酬。」助教有些口齒不清。
我站在阿卷身後不遠處,阿卷也在抽菸,但聞不到大麻味,我聽到他長篇大論大談自己從破圈講座上學來的知識,還有跟著名哲學家們相識的經歷,全然忘記自己以前跟助教講過,自己在人家的講座上倒頭大睡的事情。
「你怎麼總把破圈掛在嘴邊?」助教的提問開始變得有些不識趣。
「沒破圈精神,我們要怎樣衝破這些主流意識形態的牢籠?」阿卷顯然覺得自己是在義正嚴辭地講出這句話。
「你這麼懂破圈精神,那你自己有哪裡破圈了?」助教眼神渙散,笑得有點輕蔑。
「我反對主流,還不算破圈嗎?」阿卷顯得有點生氣,就是女生因為男生打遊戲不好好聽自己講話的那種生氣。
「你就不是圈內人,算什麼破圈?我說你自己啦,生活啊什麼的,有突破你自己的地方。」助教用夾著菸的手不斷摩擦自己的臉,彷彿想要從乾淨的臉上硬生生搜出幾根漏網的鬍子來。
阿卷有些侷促,但也低著頭、認真想了好久。「我……違抗了老祖宗的人倫」,慢慢說、慢慢瞇起眼睛深吸了一口菸,一邊仔細品味尼古丁的清涼,一邊把手放回橋頭,煙終於還是隨著一聲嘆息被吐出來,阿卷轉過頭認真盯住助教幾秒鐘,又扭回頭看著河,
「我原本叫阿圈。」
沒有用的註釋
* 這邊有機會推測到,打扮老氣的阿卷年齡其實並不大(笑)。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