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戈達爾| adieu à godard

再見戈達爾
Adieu à Godard
文/林伯奇
圖/Bande à part (1964), Jean-Luc Godard, Gaumont Pictures
全文共4773字,讀完需9-15分鐘。
7年前,時年84歲的戈達爾拍攝了一部名叫《再見語言》(Adieu au langage)的電影;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卻要說出再見戈達爾——Adieu à Godard了。許久沒有提筆,今日想寫一點東西,竟是為作一篇悼文。
今天下午朋友通知我,戈達爾死了,還配了法國《解放報》的報導發來——這老頭子還是死了。相比起不久前的英國女王之死,我覺得戈達爾的去世更加令我感到驚訝、錯愕還有遺憾。曾幾何時,戈達爾被評論界廣泛譽為影壇的活化石——按照我的理解,今天的電影,基本建構於戈達爾和那一代法國新浪潮電影人所建構的電影概念之上;今日的導演從東到西,從王家衛到馬丁·斯科塞斯,無不坦言自己曾受到過戈達爾的影響;再往前追溯,那就是老師的老師,卓別林和布萊希特等人對當代電影戲劇學所做的奠基了。然而細看整個影史:帕索里尼死的最早,然後是特呂福,庫布里克於1999年去世,3年前與戈達爾同時代的“新浪潮之母”瓦爾達去世;按照19年瑞士電視台對已經八十九歲高齡的戈達爾所作的採訪,他表示自己仍然在寫作一份電影劇本並打算在瑞士拍攝,我們仍然可見一位老藝術家在此等年歲時仍懷有的可敬決心;他是電影歷史的常青樹和活化石,他是戛納電影節的象徵(儘管他曾經讓戛納電影節辦的非常尷尬),然而在2022年9月13日,我們收到了一則這樣的噩耗——一個電影界的泰斗就此隕落;對於整個藝術界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我們與大師同行的時代已然結束。曾幾何時,年少的海明威在巴黎的街頭朝喬伊斯問候“大師”,若干年後,依然在巴黎的街頭,年少的馬爾克斯向著已經成為大師的海明威問候一句“大師”。然而,我們這一代藝術青年已然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儘管戈達爾曾經在記者面前打趣稱,瓦爾達和他均已赴往生後,世上仍有雅克·侯西耶作為新浪潮運動的僅剩旗手與這個時代的藝術家相伴——我其實越想越感慨。 5年前,在瓦爾達去世之前,她與當代藝術家JR合作拍攝紀錄片《臉龐,村莊》(Visages Villages);一位是上個時代的藝術奠基人,一位是當代的新潮創作者,兩個人結伴而行,使用攝像機和照相機拍攝他們所見到的一切事物。其中他們來到了盧浮宮——正是當年戈達爾拍攝《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的取景地,年輕的JR推著輪椅上的瓦爾達參觀盧浮宮,一老一少聊起崢嶸歲月和那些電影,表達對那個時代的敬意;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瓦爾達已經於3年前去世,現在看似不倒的戈達爾也與他畢生的同志,還有特呂福,卡里娜,維亞澤姆斯基等人團聚了。
當然,說團聚其實不准確;相比起基督教所定義的“死後世界”觀念,戈達爾本人更加相信存在於其他文明中的轉世輪迴說。他對記者說他相信自己從西班牙帶回的一條小狗上輩子是國際縱隊的擔架員。一直以來,我有這樣的習慣,時不時地在微博上搜索“戈達爾”三個字,想看看這老頭子最新的情況;他是在安排新直播,還是在創作新的電影,又或者是——已然在國內浮躁的輿論中他的死訊變得不值一提,只有極少數的電影人會提起這件事?但我從沒想到,今天他真的走了,還是別人通知我我才知道的,而他的死訊比我想像中似乎更加引起關注,頗有種加繆在《局外人》中所表達的某種失落感;空蕩蕩的感覺。
讓-呂克·戈達爾於1930年在法國巴黎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出生。因為他的母親是瑞士人,所以他也同樣具有瑞士國籍;他的童年在瑞士度過。二戰結束後他回到法國,入讀索邦大學哲學系;因在巴黎期間對電影與新潮思想產生興趣,他本人與自己的資產階級父親劃清界限,後一度被關進精神病院(儘管他本人說他認為大學就是最精神病的地方)。彼時戰爭結束不久,歐洲文化界蠢蠢欲動,意大利的導演們提出了“讓電影走上街頭”的口號,如德西卡、羅西里尼等人提出了電影新現實主義的概念,以極低的成本,街頭的拍攝和粗糙感來製作電影。彼時受到大洋彼岸的好萊塢衝擊的法國影業也吸取了同樣的思維;那時的法國院線,不是好萊塢製作就是第三共和國時代的陳舊手法,而一群年輕的電影人創辦了一本叫《電影手冊》的雜誌,戈達爾便是它的撰稿人之一。這些電影人以非常犀利的語言點評,而後他們自己也製作起了電影,《電影手冊》也隨之成為了法國新浪潮運動的主舞台。
1960年,戈達爾的個人處女作《精疲力盡》上映,隨即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往後他又拍攝了許多經典作品:《隨心所欲》,《小兵》(在法第五共和國審批機制下因題材敏感未能過審上映)和《法外之徒》。在這些電影中,他表達了自己對存在主義思想等等當時歐洲思想界被人們追捧的理論的思考,同時表達個人的思想,如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和對越南戰爭的批判——往後的1968年,他更是與思想家讓-保羅·薩特頻繁同時出現。隨著國際左翼運動於1968年在全世界範圍內進入高潮,戈達爾本人的思想態度也受到影響——他坦言自己受到了社會主義者的熱情的感染,拍攝了電影《中國姑娘》(La Chinoise)。往後的1970年代,他本人加入一個叫“吉佳-維爾托夫”的電影組織,製作一些實驗性影片,在後來的20年裡一直在製作電影。進入新世紀後,他重新回到自己的個人主義風格,於2010年拍攝《電影社會主義》,在片中邀請了歐洲知名學者阿蘭·巴迪歐露面;2014年拍攝《再見語言》,這是他第一次嘗試用3D方法製作電影。 2020年,戈達爾接受瑞士洛桑藝術設計大學電影系的訪問,在網上現場直播,講述他對新冠疫情下的社會與影視業的思考;那時有人斷言“你說這老頭哪天能豎著拍電影我都信”。 2018年,戈達爾拍攝完自己人生中最後一部電影《影像之書》,進行自己的講演;隨後於此時此刻撒手人寰,頗有種當年居伊·德波的感覺。
現在,讓-呂克·戈達爾為自己的生涯畫上了句號,一個時代成為了歷史——“一個時代成為了歷史”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車軲轆話了。這個月的兩個星期來,戈爾巴喬夫,然後是英國女王,現在是戈達爾——上個時代的風雲人物紛紛離去,使我產生了一種感覺:死亡像是一塊玻璃。從某種程度上,我現在憎恨戈達爾;因為他的死,使我們與一個時代產生了隔膜,在他的生命停止之前,我們仍然可以說是身處同一時代者,仍可謂與之同行,然而他的離去卻給了我一種芥川龍之介在昭和時代初期所感受到的,與芥川龍之介之死帶給青年太宰治的錯愕感。一塊玻璃擋在我們和戈達爾之間;我們站在“當代”,而戈達爾站在“戈達爾的年代”,又或者可謂“傳奇的時代”,我們只能站在玻璃的這一邊看著他,漸漸消失,卻再也不能說我們正在與他同行;這就好像,假如1957年的馬爾克斯沒有生活在巴黎,等到1962年他再到巴黎時,卻發現海明威已經死去時的感覺。
但論戈達爾,我還是想再說說一個話題,那就是戈達爾究竟留下了怎樣的遺產。 2019到2020年,在爭議下,由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我控訴》分別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法國凱撒最佳導演獎。儘管評審委員會在如今#MeToo運動的大環境下就導演品德問題飽受指責,有一點非常明顯:當下的電影市場既厭倦了好萊塢的庸俗也厭倦了後現代主義的故作深沉,因此一部充滿古典主義色彩的電影能從技術的含義上受到好評。戈達爾所揚棄的布萊希特戲劇理論或許在當下這個時代的戲劇學、電影行業已經摸到了天花板。他最有名的門徒王家衛近些年來參與製作的作品飽受質疑,不少評論家認為如今的王家衛已經江郎才盡,只能靠90年代積攢下的名氣在當今的電影市場恰爛錢。論電影理論與電影手法,戈達爾在今日電影系學生中的地位是“必修課”,然而僅限於必修課,在未來的時代,藝術怎麼走出創新風格仍然是今日所有的藝術家都在思考的問題,從戈達爾王家衛身上照葫蘆畫瓢或許已經不再現實。
但我認為戈達爾仍然為後世留下了一份遺產;不只是為今日的藝術家,是為今日的所有人在如何面對人生,社會與世界的態度所留下的一種指引。在我看來,真正成就了許多未來藝術家的,並非戈達爾的藝術技巧或手法,而是戈達爾所留下的一種態度。
今天我看到賈樟柯導演發文紀念戈達爾;事實上,國內學院派第五代導演也全部是受到香港電影和戈達爾的影響;說來你不信,在香港除了王家衛,所謂'爛片大王'王晶也表示拍爛片只是為了恰錢,他也會為文藝片或者主題電影投資,閒下來的時候也會看戈達爾。但試想一下,國內第五代導演給人們留下的普遍印像是什麼?是一種不羈感,這種不羈感和當初戈達爾面對戴高樂當局頒發的禁令有某種共通之處。
對我來說我認為如今人們所缺乏的是一種可被稱之為“想像的空間”的東西。今天的輿論與主義的市場,遍布著形形色色的口號,吸引著人們的眼球,包攬了一批信徒。我的體會是今天的語言比以往更加豐富,然而在某種工具理性的條文下,各個派別所包裹的主張卻讓我感到抽象和形而上學。談到戈達爾,揮之不去的是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五月風暴”——當時戈達爾與巴黎大街上的學生工人們站在一起。在過去了五十多年後,去年韋斯·安德森上映了他的新作《法蘭西特派》,其中一部分由當代青少年偶像“甜茶”主演的部分便是在影射“五月風暴”。片中“甜茶”率領著一群小年輕在進行要求男生可以進女生宿舍的抗議;這也是“五月風暴”爆發的最初緣由。然而我在看國內相關的公眾號介紹這部電影時,特意要強調一下片中內容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我感到有點哭笑不得。人們常說歷史是進步發展的,然而當我們看著現在這代人無法理解過往發生過的歷史,認為過往這段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歷史竟然表現得如此荒誕不經;但我們明明就生活在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所創造出的世界裡啊!這究竟是這個時代的人大腦縮水了還是如何?我們不得而知。難道這個時代的人連嘗試想像和麵對真實的勇氣都沒有了嗎?又或者是這個時代更文明了?不;在我看來這種文明比所謂野蠻與粗魯更加粗魯;它帶有一絲高傲的意味。
這個時代的藝術家許多也不例外;然而這並不藝術。戈達爾是一個比較經典的法國知識分子,他師承了普魯斯特的“藝術曝光論”:即為藝術家存在的意義,為發現人們日常生活中會被忽略的現實;藝術家是充滿冒險性的,是充滿好奇的,像維米爾或倫勃朗那般去把會被人們忽略的畫面捕捉下來。作為攝影家的戈達爾深深理解這一點,以至於他和師承他的風格的門徒們都在去做這一件事,以至於對戈達爾來說他的任務就在於像任何一個藝術家一樣保持自己的激情,用自己的鏡頭把分分秒秒保存下來。今日的藝術家許多在我眼裡,做的是“溫室的藝術”。他們在溫室的環境裡成長,自然也要宣揚溫室的道理——但若是所謂理性已經成為常態,那麼宣揚理性的藝術意義又何在?當代許多人似乎失去了某種挑戰主義的精神——不論藝術家或者普通人,陷入在媚俗的漩渦之中,但既然如此,這個時代的人又有什麼資格去責怪這個時代的沉悶,假如前提就是已經接受了把沉悶與冷漠當作既定的規則?
所以在如今這個時代,戈達爾的價值便體現在這裡。那些實驗電影沉悶嗎?答案不言而喻。但那麼厚厚一本的《尤利西斯》,所涵蓋的冗長內容,其寓意不就在揭發人們的生活本身?我看見——今日的許多人沒有以一種誠實的態度去面對自己或者這個世界,喜歡去虛偽地“批判人性”;但就算是憤世嫉俗,只要它是真實的,那又何妨呢?五十年前的人們面對著景觀社會敢於發出自己的呼聲,敢於直面自己直面世界;今日的人們卻埋頭於所謂文明的規訓,乃至連這個時代的藝術都無法突破所謂日常與習慣的濾鏡。在我看來,戈達爾為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提供了某種信標;那就是一種來自於人內心中最樸實也最真實的目光與話語去發現——若是這個時代對人心底最渴望的東西都不予以重視,宣揚克己復禮,那麼所謂文明又有何意義?若是蔑視客觀存在,那麼敬畏又有何意義?為何吃喝拉撒?為何朝九晚五?我們為何要這樣生活? ——於我,戈達爾成為了一個個人革命的象徵,荒誕而真實,狡猾而不虛偽,去突破這個時代。
無論如何——我們,尤其是藝術家——需要真誠與激情,即便它危險。戈達爾生前對自己的狗的上輩子有過自己的猜測,我想戈達爾的下輩子,也許是巴黎某棵老樹上的貓頭鷹吧。願他保持他的激情,即便此刻,也不會安息,永不停歇;就像他的電影一樣。
於廣東廣州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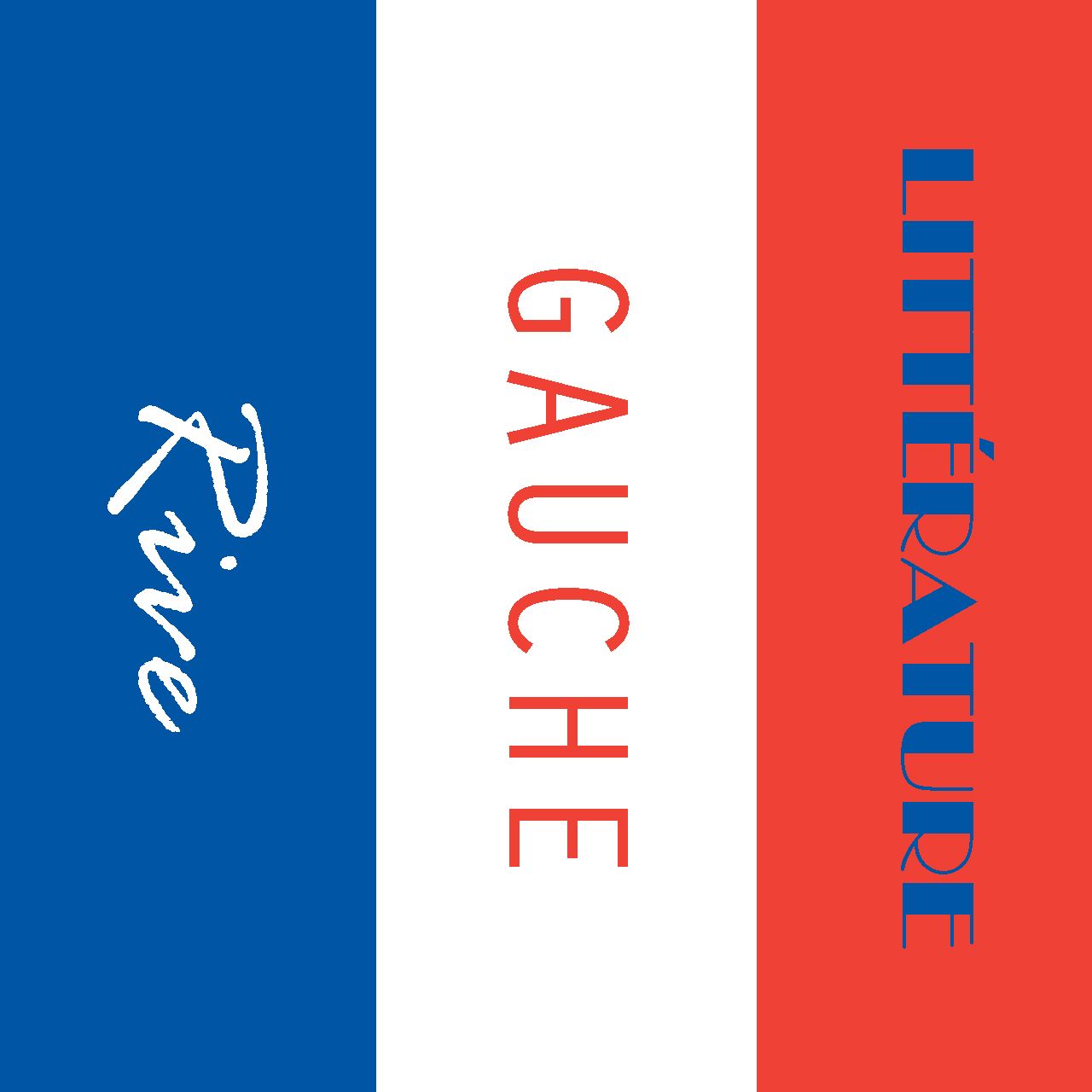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