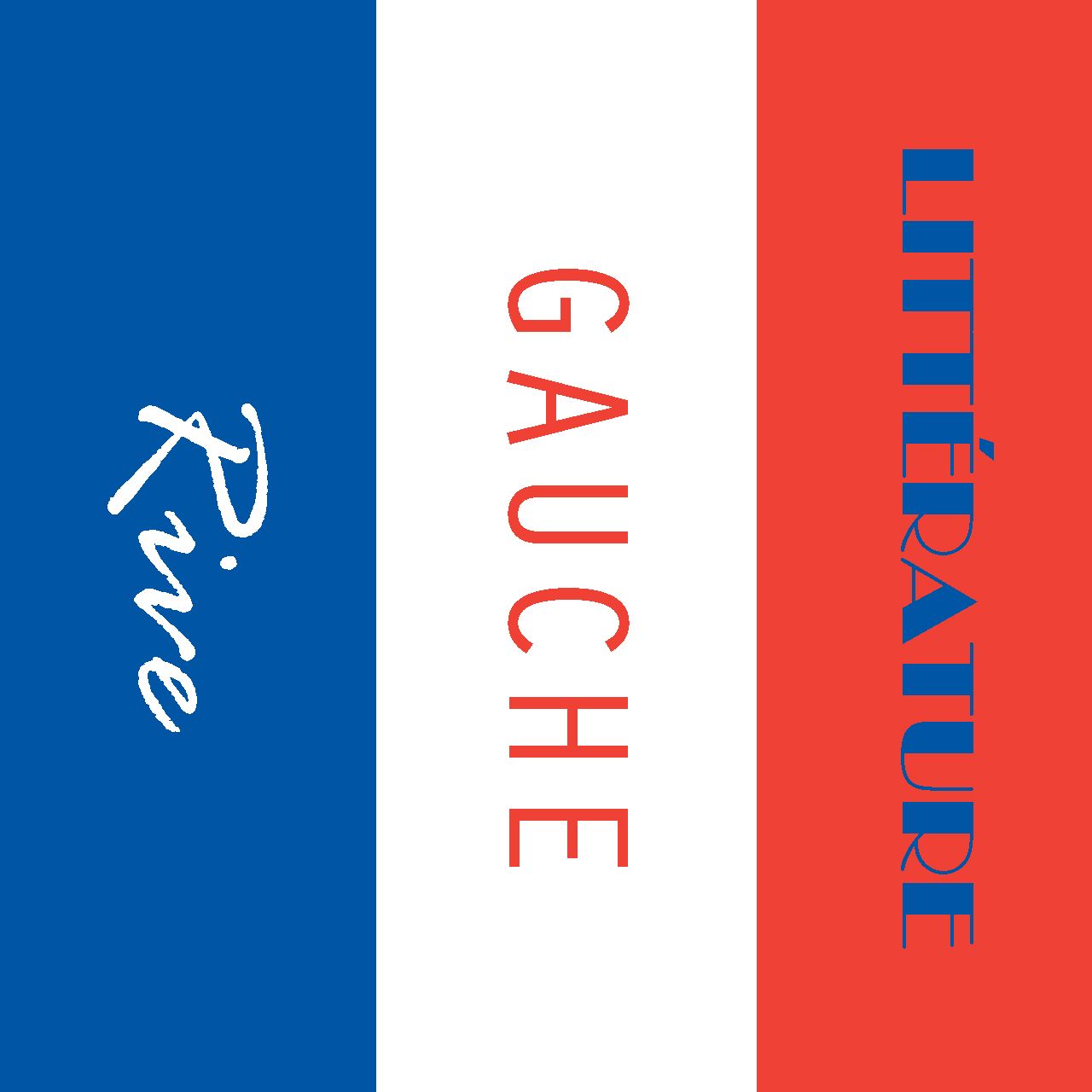再见戈达尔 | adieu à godard

再见戈达尔
Adieu à Godard
文/林伯奇
图/Bande à part (1964), Jean-Luc Godard, Gaumont Pictures
全文共4773字,读完需9-15分钟。
7年前,时年84岁的戈达尔拍摄了一部名叫《再见语言》(Adieu au langage)的电影;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要说出再见戈达尔——Adieu à Godard了。许久没有提笔,今日想写一点东西,竟是为作一篇悼文。
今天下午朋友通知我,戈达尔死了,还配了法国《解放报》的报道发来——这老头子还是死了。相比起不久前的英国女王之死,我觉得戈达尔的去世更加令我感到惊讶、错愕还有遗憾。曾几何时,戈达尔被评论界广泛誉为影坛的活化石——按照我的理解,今天的电影,基本建构于戈达尔和那一代法国新浪潮电影人所建构的电影概念之上;今日的导演从东到西,从王家卫到马丁·斯科塞斯,无不坦言自己曾受到过戈达尔的影响;再往前追溯,那就是老师的老师,卓别林和布莱希特等人对当代电影戏剧学所做的奠基了。然而细看整个影史:帕索里尼死的最早,然后是特吕福,库布里克于1999年去世,3年前与戈达尔同时代的“新浪潮之母”瓦尔达去世;按照19年瑞士电视台对已经八十九岁高龄的戈达尔所作的采访,他表示自己仍然在写作一份电影剧本并打算在瑞士拍摄,我们仍然可见一位老艺术家在此等年岁时仍怀有的可敬决心;他是电影历史的常青树和活化石,他是戛纳电影节的象征(尽管他曾经让戛纳电影节办的非常尴尬),然而在2022年9月13日,我们收到了一则这样的噩耗——一个电影界的泰斗就此陨落;对于整个艺术界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们与大师同行的时代已然结束。曾几何时,年少的海明威在巴黎的街头朝乔伊斯问候“大师”,若干年后,依然在巴黎的街头,年少的马尔克斯向着已经成为大师的海明威问候一句“大师”。然而,我们这一代艺术青年已然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尽管戈达尔曾经在记者面前打趣称,瓦尔达和他均已赴往生后,世上仍有雅克·侯西耶作为新浪潮运动的仅剩旗手与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相伴——我其实越想越感慨。5年前,在瓦尔达去世之前,她与当代艺术家JR合作拍摄纪录片《脸庞,村庄》(Visages Villages);一位是上个时代的艺术奠基人,一位是当代的新潮创作者,两个人结伴而行,使用摄像机和照相机拍摄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事物。其中他们来到了卢浮宫——正是当年戈达尔拍摄《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的取景地,年轻的JR推着轮椅上的瓦尔达参观卢浮宫,一老一少聊起峥嵘岁月和那些电影,表达对那个时代的敬意;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瓦尔达已经于3年前去世,现在看似不倒的戈达尔也与他毕生的同志,还有特吕福,卡里娜,维亚泽姆斯基等人团聚了。
当然,说团聚其实不准确;相比起基督教所定义的“死后世界”观念,戈达尔本人更加相信存在于其他文明中的转世轮回说。他对记者说他相信自己从西班牙带回的一条小狗上辈子是国际纵队的担架员。一直以来,我有这样的习惯,时不时地在微博上搜索“戈达尔”三个字,想看看这老头子最新的情况;他是在安排新直播,还是在创作新的电影,又或者是——已然在国内浮躁的舆论中他的死讯变得不值一提,只有极少数的电影人会提起这件事?但我从没想到,今天他真的走了,还是别人通知我我才知道的,而他的死讯比我想象中似乎更加引起关注,颇有种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表达的某种失落感;空荡荡的感觉。
让-吕克·戈达尔于1930年在法国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生。因为他的母亲是瑞士人,所以他也同样具有瑞士国籍;他的童年在瑞士度过。二战结束后他回到法国,入读索邦大学哲学系;因在巴黎期间对电影与新潮思想产生兴趣,他本人与自己的资产阶级父亲划清界限,后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尽管他本人说他认为大学就是最精神病的地方)。彼时战争结束不久,欧洲文化界蠢蠢欲动,意大利的导演们提出了“让电影走上街头”的口号,如德西卡、罗西里尼等人提出了电影新现实主义的概念,以极低的成本,街头的拍摄和粗糙感来制作电影。彼时受到大洋彼岸的好莱坞冲击的法国影业也吸取了同样的思维;那时的法国院线,不是好莱坞制作就是第三共和国时代的陈旧手法,而一群年轻的电影人创办了一本叫《电影手册》的杂志,戈达尔便是它的撰稿人之一。这些电影人以非常犀利的语言点评,而后他们自己也制作起了电影,《电影手册》也随之成为了法国新浪潮运动的主舞台。
1960年,戈达尔的个人处女作《精疲力尽》上映,随即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往后他又拍摄了许多经典作品:《随心所欲》,《小兵》(在法第五共和国审批机制下因题材敏感未能过审上映)和《法外之徒》。在这些电影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存在主义思想等等当时欧洲思想界被人们追捧的理论的思考,同时表达个人的思想,如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对越南战争的批判——往后的1968年,他更是与思想家让-保罗·萨特频繁同时出现。随着国际左翼运动于1968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高潮,戈达尔本人的思想态度也受到影响——他坦言自己受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热情的感染,拍摄了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往后的1970年代,他本人加入一个叫“吉佳-维尔托夫”的电影组织,制作一些实验性影片,在后来的20年里一直在制作电影。进入新世纪后,他重新回到自己的个人主义风格,于2010年拍摄《电影社会主义》,在片中邀请了欧洲知名学者阿兰·巴迪欧露面;2014年拍摄《再见语言》,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用3D方法制作电影。2020年,戈达尔接受瑞士洛桑艺术设计大学电影系的访问,在网上现场直播,讲述他对新冠疫情下的社会与影视业的思考;那时有人断言“你说这老头哪天能竖着拍电影我都信”。2018年,戈达尔拍摄完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影像之书》,进行自己的讲演;随后于此时此刻撒手人寰,颇有种当年居伊·德波的感觉。
现在,让-吕克·戈达尔为自己的生涯画上了句号,一个时代成为了历史——“一个时代成为了历史”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车轱辘话了。这个月的两个星期来,戈尔巴乔夫,然后是英国女王,现在是戈达尔——上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纷纷离去,使我产生了一种感觉:死亡像是一块玻璃。从某种程度上,我现在憎恨戈达尔;因为他的死,使我们与一个时代产生了隔膜,在他的生命停止之前,我们仍然可以说是身处同一时代者,仍可谓与之同行,然而他的离去却给了我一种芥川龙之介在昭和时代初期所感受到的,与芥川龙之介之死带给青年太宰治的错愕感。一块玻璃挡在我们和戈达尔之间;我们站在“当代”,而戈达尔站在“戈达尔的年代”,又或者可谓“传奇的时代”,我们只能站在玻璃的这一边看着他,渐渐消失,却再也不能说我们正在与他同行;这就好像,假如1957年的马尔克斯没有生活在巴黎,等到1962年他再到巴黎时,却发现海明威已经死去时的感觉。
但论戈达尔,我还是想再说说一个话题,那就是戈达尔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2019到2020年,在争议下,由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我控诉》分别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法国凯撒最佳导演奖。尽管评审委员会在如今#MeToo运动的大环境下就导演品德问题饱受指责,有一点非常明显:当下的电影市场既厌倦了好莱坞的庸俗也厌倦了后现代主义的故作深沉,因此一部充满古典主义色彩的电影能从技术的含义上受到好评。戈达尔所扬弃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或许在当下这个时代的戏剧学、电影行业已经摸到了天花板。他最有名的门徒王家卫近些年来参与制作的作品饱受质疑,不少评论家认为如今的王家卫已经江郎才尽,只能靠90年代积攒下的名气在当今的电影市场恰烂钱。论电影理论与电影手法,戈达尔在今日电影系学生中的地位是“必修课”,然而仅限于必修课,在未来的时代,艺术怎么走出创新风格仍然是今日所有的艺术家都在思考的问题,从戈达尔王家卫身上照葫芦画瓢或许已经不再现实。
但我认为戈达尔仍然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遗产;不只是为今日的艺术家,是为今日的所有人在如何面对人生,社会与世界的态度所留下的一种指引。在我看来,真正成就了许多未来艺术家的,并非戈达尔的艺术技巧或手法,而是戈达尔所留下的一种态度。
今天我看到贾樟柯导演发文纪念戈达尔;事实上,国内学院派第五代导演也全部是受到香港电影和戈达尔的影响;说来你不信,在香港除了王家卫,所谓‘烂片大王’王晶也表示拍烂片只是为了恰钱,他也会为文艺片或者主题电影投资,闲下来的时候也会看戈达尔。但试想一下,国内第五代导演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是什么?是一种不羁感,这种不羁感和当初戈达尔面对戴高乐当局颁发的禁令有某种共通之处。
对我来说我认为如今人们所缺乏的是一种可被称之为“想象的空间”的东西。今天的舆论与主义的市场,遍布着形形色色的口号,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包揽了一批信徒。我的体会是今天的语言比以往更加丰富,然而在某种工具理性的条文下,各个派别所包裹的主张却让我感到抽象和形而上学。谈到戈达尔,挥之不去的是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戈达尔与巴黎大街上的学生工人们站在一起。在过去了五十多年后,去年韦斯·安德森上映了他的新作《法兰西特派》,其中一部分由当代青少年偶像“甜茶”主演的部分便是在影射“五月风暴”。片中“甜茶”率领着一群小年轻在进行要求男生可以进女生宿舍的抗议;这也是“五月风暴”爆发的最初缘由。然而我在看国内相关的公众号介绍这部电影时,特意要强调一下片中内容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我感到有点哭笑不得。人们常说历史是进步发展的,然而当我们看着现在这代人无法理解过往发生过的历史,认为过往这段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历史竟然表现得如此荒诞不经;但我们明明就生活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所创造出的世界里啊!这究竟是这个时代的人大脑缩水了还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难道这个时代的人连尝试想象和面对真实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又或者是这个时代更文明了?不;在我看来这种文明比所谓野蛮与粗鲁更加粗鲁;它带有一丝高傲的意味。
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许多也不例外;然而这并不艺术。戈达尔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师承了普鲁斯特的“艺术曝光论”:即为艺术家存在的意义,为发现人们日常生活中会被忽略的现实;艺术家是充满冒险性的,是充满好奇的,像维米尔或伦勃朗那般去把会被人们忽略的画面捕捉下来。作为摄影家的戈达尔深深理解这一点,以至于他和师承他的风格的门徒们都在去做这一件事,以至于对戈达尔来说他的任务就在于像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保持自己的激情,用自己的镜头把分分秒秒保存下来。今日的艺术家许多在我眼里,做的是“温室的艺术”。他们在温室的环境里成长,自然也要宣扬温室的道理——但若是所谓理性已经成为常态,那么宣扬理性的艺术意义又何在?当代许多人似乎失去了某种挑战主义的精神——不论艺术家或者普通人,陷入在媚俗的漩涡之中,但既然如此,这个时代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去责怪这个时代的沉闷,假如前提就是已经接受了把沉闷与冷漠当作既定的规则?
所以在如今这个时代,戈达尔的价值便体现在这里。那些实验电影沉闷吗?答案不言而喻。但那么厚厚一本的《尤利西斯》,所涵盖的冗长内容,其寓意不就在揭发人们的生活本身?我看见——今日的许多人没有以一种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自己或者这个世界,喜欢去虚伪地“批判人性”;但就算是愤世嫉俗,只要它是真实的,那又何妨呢?五十年前的人们面对着景观社会敢于发出自己的呼声,敢于直面自己直面世界;今日的人们却埋头于所谓文明的规训,乃至连这个时代的艺术都无法突破所谓日常与习惯的滤镜。在我看来,戈达尔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提供了某种信标;那就是一种来自于人内心中最朴实也最真实的目光与话语去发现——若是这个时代对人心底最渴望的东西都不予以重视,宣扬克己复礼,那么所谓文明又有何意义?若是蔑视客观存在,那么敬畏又有何意义?为何吃喝拉撒?为何朝九晚五?我们为何要这样生活?——于我,戈达尔成为了一个个人革命的象征,荒诞而真实,狡猾而不虚伪,去突破这个时代。
无论如何——我们,尤其是艺术家——需要真诚与激情,即便它危险。戈达尔生前对自己的狗的上辈子有过自己的猜测,我想戈达尔的下辈子,也许是巴黎某棵老树上的猫头鹰吧。愿他保持他的激情,即便此刻,也不会安息,永不停歇;就像他的电影一样。
于广东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