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唐凌:社会学与艺术|围炉·HKU


唐凌,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本科、MPhil,牛津大学博士。 2019年——2020年疫情期间在牛津创办滑倒乐队,偶尔在牛津街头拿着吉他唱歌。 2021年回到香港,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创意媒体院教授酷儿影视理论,实践将社会学与艺术结合的想法。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她,也试着在音乐创作中加入女性主义和酷儿的视角。在日常生活中,Ta坚持着「用个体打动个体」的女性主义实践,同时关注身边和试着重建附近。我们一起去南丫岛(香港的一个岛屿)清理过很多次海滩,Ta也会和伴侣在生活中拿着小口袋打扫街道。在一次采访中Ta提到,作为女性主义者不可能有回头路,「女性主义是从你的身体,你的感知,你的压抑,你的情绪开始的。」
Ta或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学者,但却保有对学术最纯粹的感动与真诚。 Ta说自己也许是野草,无论是在牛津的街头唱起自己关于山火的歌,还是在滑倒乐队里用声音的印记留下学术的半影,都是日常与学术的交互。同时Ta也参与了知识的网络分享,在公众号《见树又见林》里写下学术思考,以视频播客的形式进行知识分享,尝试将学术视角带入媒体。我和Ta也是两年前在社交媒体上认识,在最困顿的高三时期我把Ta当成树洞很久,Ta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温暖。
因为日常习惯称呼Ta为牛牛,所以以下都这样称呼。

炉= 任李菲阳
唐= 唐凌(牛牛)
炉|关注牛牛的微博@Lyn-Dawn 很久,发现签名一直都是「把社会学作为艺术,反之亦然」,或许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句话和写下这句话的原因吗?
唐|你关注我的微博应该是在2019年吧,其实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重新使用微博的,因为人生中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转变。一个原因是那一年我在牛津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滑倒乐队,但其实我们乐队的朋友分散各地,一位在西安音乐学院的朋友负责作曲,我和另外一位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朋友一起填词,一人负责文学,一人负责社会学,还有一位在牛津的朋友负责歌唱的部分。我们就这样开始进行歌曲创作,也接着有了更多分享的契机。

加之那段时间我也有和好朋友王婧宜@维罗妮卡是一只小蓝山雀一起在微博上制作学术视频,创办了学术啾,参与了一些社会问题的探讨。社会学、艺术、媒体与我自身的互动也就这样进一步呈现在了日常当中。那么说到社会学与艺术的关系,我自己从本科到博士阶段一直是社会学方向,所以在音乐创作里也就会更多地加入社会学视角的思考,在填词的时候也就会带有社会学的影子。以社会学为艺术,对于我来说,是在音乐创作里和社会学进行一个双向的沟通,把自身的生命经验和艺术相交融,同时也在音乐里试着寻找更多元和丰富的表达方式。反过来,艺术作为社会学,将艺术的一部分带回社会学的视野,不仅是社会学突破自身边界、寻求与个体鲜活感知、表达对社会认知可能性的体现,也是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对我们的周围和现实世界的重新思考和交流回应。在逐渐进入这种创作模式之后,我也发现早已有很多在坚持进行类似实践的社会学学者,Ta们跳出传统意义的学者身份,进入到更广阔的创作领域,产出了很多很新颖和富有创造力的表达,他们的创作对社会、社会学和艺术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实也正如博伊斯讲的「人人都是艺术家」 ,Everything could be Art(万物皆可为艺术),艺术创作本身是很富有弹性和张力的。只是我自己在最开始进行创作的时候,还是会带有一些不确定性和不安,但在后来写了一些歌之后,我进一步找到了与艺术链接的平衡点。不过不同于Everything could be Art,Everything could be Sociology(万物皆可为社会学)也许并不完全成立,社会学往往还是会更强调偏结构性视角的部分,所以这个视角也是我自己尝试着通过音乐创作去呈现的。
炉|听到对于艺术和社会学互动的分享,也有回忆起来牛牛在牛津的展览还有近期新创作的歌。感觉每一次艺术实践也是新一次对自我的探寻,所以也想问问这些年的创作对于牛牛自身的生命来讲意味着什么?又或者这些创作带来了什么新的体验?
唐|艺术对于我自己来讲是一个窗口,也是一份解放吧。我自己开始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是在读博士的阶段,那个时候自己有了一些对于学术和学术圈整体的倦怠感。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自己在进入牛津的时候,依旧是带着「牛津是学术的最高殿堂」的期盼的,但是在真正来到这里之后,还是会不时感受到比较深的离地感和对于学术圈内部生产的些许失望,可能这也与牛津整个的新自由主义氛围有关。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当时项飈老师在我的博士资格考中也给我提出一些很关键的问题。总之,自己当时相对处在一个比较不清晰的状态。所以遇到音乐和开始进行艺术创作,对于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算是一份短暂的解放,也是一个新的摆渡期。后来蛮神奇的也在于,我们滑倒乐队去到北京科技馆演出的时候,我非常偶然地接触到了韩炳哲老师的作品,里面的一些理论给自己的博士论文带来了很多新的灵感。


虽然这些经历并不是直接和音乐艺术相关,但是这部分「遇见」和「偶然」本身也给到了自己新的感知。艺术和社会学的交融对于我自己来讲,是在不确定里重新探寻自我和生命轨迹的一个过程。没有一种体验是渺小的,恰恰是这些很小的点引出了更奇妙的所在,不同的线条、乐音、遇见交织和混合在一起,互相构成彼此关照的支点。这也是在这些年的实践里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两者结合的原因,取下两者看似坚硬的外套,内里结合的无限是很柔软和丰富的。二零年我回港大做博士后的那段时间,自己不时也会有对于发表文章数量等等的焦虑,在高浓度的压力里偶尔也会比较无措,但是我很庆幸这些年一直有音乐陪着我。而音乐和艺术一方面可以让我用非学术化的语言进行更有创造力的社会学表达,寻找到另一个支点,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感知自我和社会带来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和体验。
炉|听牛牛讲述社会学和艺术与个体生命轨迹相互牵引的部分,感觉实在很奇妙,同时我也非常受触动,拥抱这些相互交织的事物感觉也是在拥抱生命的不确定性本身。同时也很好奇对于牛牛而言,社会学学者和音乐创作者这两个身份对于自己分别意味着什么?它们又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唐|这个问题也让我想起来有一次和何式凝老师聊天,那时也是我比较迷茫的时候,我们聊到关于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学者的问题,记得当时她笑着对我说:「不然呢!难道你要做Boring Academic吗?肯定是要做Creative Academic的呀!对吧!」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一边点头,一边也很感动很受鼓舞。一方面是真的很谢谢式凝,她每次说话都是那样真诚和有力量,另外其实式凝她自己这么多年来也是真的有在把这两者努力结合,就像她自己有在拍很多电影和纪录片的同时,也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当好一个老师和学者,并且她也一直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我想这也是那段对话给我的影响持续至今的原因。艺术和社会学一样,都需要看见个体和看见人,它们是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是介入社会的行走的语言。而且不论是作为艺术创作者还是社会学学者,很重要的一点都是要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做到真诚。虽然学术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高度重复性的内部生产,并且哪怕是作为学术殿堂的牛津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想或许正如《见树又见林》里那句「社会学作为生命、承诺和实践」一样,这也是我自己作为社会学学者一直抱有的态度,也正如艺术创作要对自我真诚,这两者其实是相似和互相支撑促进的,它们都在时刻提醒着我那些最原初的感动和那些坚持写作和创作最朴素的缘由。

炉|记得牛牛在「见树又见林」的第一期播客里以摇滚乐为主讲述了对于艺术和社会学的理解,最后提到了韩炳哲老师写的那句:「最光滑的艺术就是在光滑的表面看到自己的折射」,或许可以详细讲讲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以及怎么样看待艺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的视角在这之中给艺术创作带来了什么新的可能性?
唐|其实韩炳哲写「最光滑的艺术是在光滑的表面看到自己的折射」是关于Jeff Koons的金属作品。韩柄哲主要是想借由这些作品表达对于艺术创作者的一些反思和批评。对于我自己来说,社会学的视角的确是在提醒我跳脱出那个过于「放大的自我」。这也是因为对于很多艺术创作来说,最终完成作品的那一刻还是在和观众产生连接的那一刻。就像观看艺术不是单一被动的消费艺术,而是可以变成属于艺术和观众两者共同的世界。同样社会学的反身性不仅让我把自身作为作品的材料,同时也让我可以把社会和观众,以及对于真实世界的体感和反思一起融入作品当中,这也是艺术和社会学学者这两个身份交织给到我重要启发的点。 「互动」带来「他者的加入」,「加入」延长了理论和艺术相互依存的时间和生命,也延伸了创作者的涵义。社会学和艺术一起构筑了彼此的桥梁,也一并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延展开来的社会记忆。
炉|提到艺术和社会学,布尔迪厄也写过关于知识和文学生产可能会造成的「区隔」和「符号暴力」,牛牛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有类似的顾虑?牛牛怎样看待文学艺术可能会带来的门槛?
唐|关于门槛,我觉得可能更像是马克思讲的阶级引发的区分,布尔迪厄提到的类似「区隔」可能是一个更隐形的概念,是在进入一个不熟悉场域之后内心难以言说的不安。我觉得类似的区别和区隔,不管是在艺术还是文学领域,又或者是在一些专业性的圈子里,肯定都是会有的。但也要分开来看,因为这也与讲述和介入的方式紧密相关。就像最近我唱的一首新歌,是我一位牛津的好朋友Tara写的词,整个歌词里面有很多非常晦涩的英文单词,但是其实她自己并没有要刻意去强调所谓的区隔,而是希望通过歌词创作去表现那些词句的美,因为她自己也的确是非常喜欢古典英语文学。所以好的介入方式其实是可以连接所谓的不同的,异质性并没有被强调的那么大。又比如马克思的作品,其实他的语言和表述本身也很复杂,其实是不太能直接达到团结工人的效果的。所以除开创作者自身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和参与者的整体互动,从而去完成对于整个作品的解读。这些反而可能是更抓住人的地方,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越过了所谓的显性和隐性区分的区隔。平等与包容的对话状态,是美可以成为美而非再度被分割,也是音乐「遇见有缘的耳朵」这一最纯粹的感动所在。

每次和唐凌(牛牛)对话和聊天,都会给自己留下很持久的感动和温暖。也正如Ta自己提到过的「个体打动个体」,从几年前到现在,我也一直都是那个被Ta打动着的个体。每次听到Ta新发出的歌,也会让我一次又一次想起那些和Ta对话的时刻、Ta讲过的故事和话语、还有Ta这些年做过的大大小小的尝试。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强的当下,愿Ta的音乐不停,也愿这些微小的坚持和真诚可以一直都在。

统稿| 任李菲阳
图| 来自网络
编辑| 张宇轩
matters编辑|邢奕萱
围炉(ID:weilu_fla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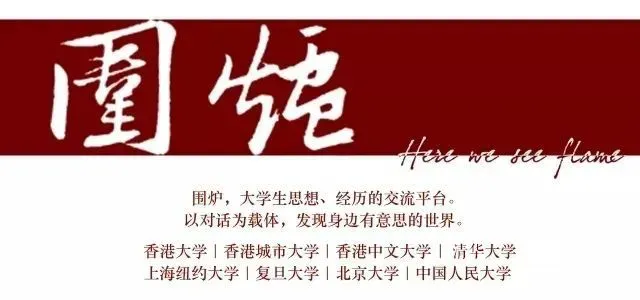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