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行业的跨性别女性:歧视、骚扰和蓄意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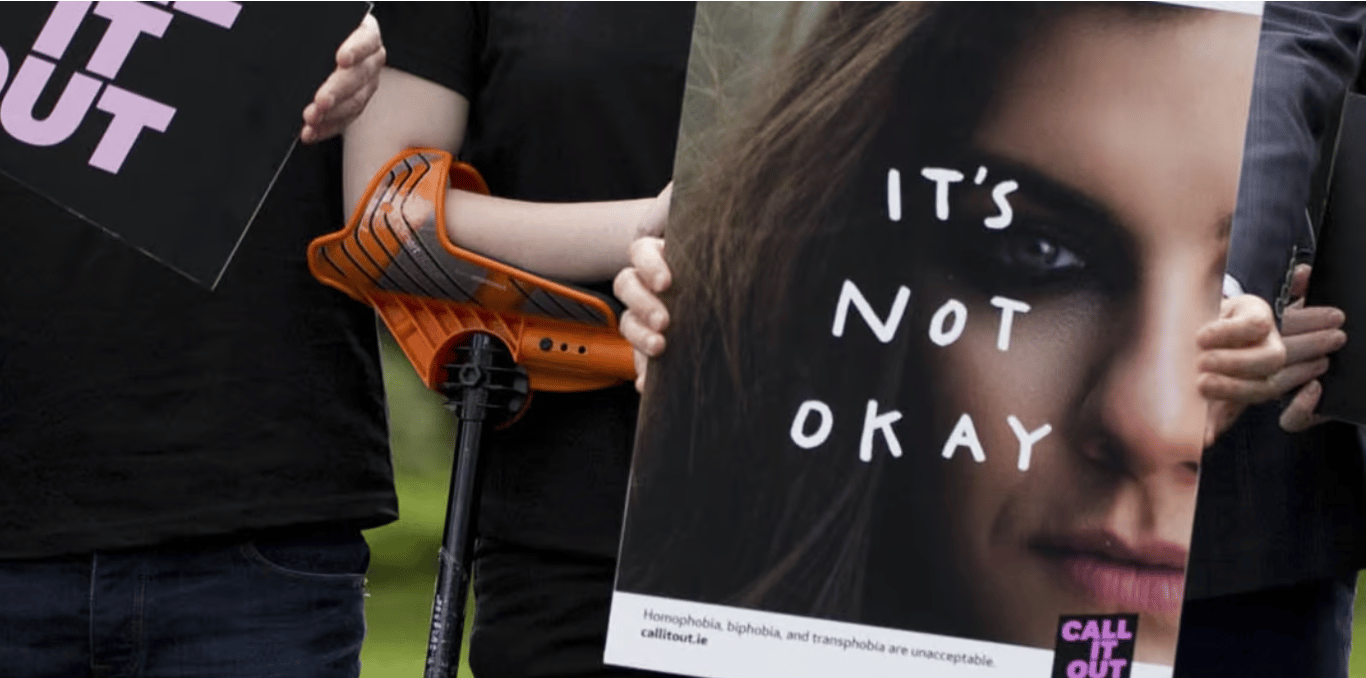
“你在这座办公楼里见过长头发的男人吗?”
我之前在《南方周末》工作,当时的主编姚以江在我递交入职材料后就跟我聊起了我的发型。姚先生今年 50 多岁,是个异性恋男性。在谈话之前,我就知道他对我的长发有些不满,因为他曾多次劝我剪掉头发。但当他开口说“你的发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过了,我们主编很不满意。你知道,外面有很多求职者在等着工作”时,我吓坏了。他的语气很柔和,但言辞却很尖锐。正是在那一刻,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期间所经历的歧视从轻微的歧视变成了赤裸裸的威胁。
那时,我刚刚结束在欧洲攻读硕士课程的四年旅程,回到中国待了两个月,当然,也是因为零新冠政策实施后回国成本太高。作为一名跨性别女性,我确实预料到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歧视,尤其是在一个没有专门法律保护边缘群体免受仇恨犯罪侵害的地方,但我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在中国会如何发生,因为我的社会转型主要是在欧洲。留长发、试穿女装、参加女权主义研讨会、出去游行等等,我想说,在欧洲生活期间,我很荣幸能与思想开放的人在一起,所以当时我得到了朋友的热烈支持。然而,当我踏上我曾经熟悉的中国土地时,事情开始失去我的控制。
对于那些可能不熟悉《南方周末》的人来说,这是一份自由派报纸,在中国受到严格控制的媒体行业中,它以大胆批评当局和为边缘群体发声而闻名。它于 1984 年在靠近香港特区的中国南方城市广州成立。它被视为 1980 年代中国媒体自由化的里程碑。它也是中国观察家观察中国政治变化的好对象。
2023 年 1 月,我来到广州,在《南方周末》担任记者。我为这个职位奋斗了三个多月,希望疫情过后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姚是我的编辑。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是在我到广州的第三天,在《南方周末》办公楼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他和朱莉在一起,朱莉是我几年前在网上认识的他的一位女下属。我们谈了一些关于这个职位的细节,以及第二天去北京出差的事情。就是在那时,他开始逼我剪掉头发,我已经留了 5 年的头发了。在那次见面时,他把我的发型形容为“艺术家发型”。这是一句不必要的评论,一个月后我才回想起这件事,当时我终于明白,除非我把头发剪成“男人味”的短发,否则他不会停止骚扰我的发型。
2 月初,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严重地震,我看穿了姚的伎俩。地震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国内外新闻机构都把镜头对准了这场灾难。南方周末也一样,但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晚了一点。在全世界都知道两国有人死亡后,他们开始组织报道,时间差不多是两天后。姚用被派往边境地区进行新闻报道的机会来引诱我,但前提是我必须剪掉头发。作为一个在广州的北方人,我还在适应这座城市,这让我感到压力很大。因此,我决定拒绝他的“善意建议”,就像我在 1 月份拒绝过几次一样。然而,他肯定有耐力。他用诱饵试了两次。第一次,他暗示条件是,头发是去土耳其的机会。但没有什么能与他的第二次尝试相比。为了打破我的壁垒,他尝试了他 30 年磨练的宣传技巧。误导。他想通过树立一个榜样来给我施加同侪压力。莫妮卡是一名顺性女性同事,据他说,她为了新闻工作牺牲了自己的头发。他的逻辑很简单:“连女人都能做到,你(作为男人)为什么做不到?”当然,他用“剪掉”代替了“修剪”,歪曲了事实。
接下来就是开头提到的姚明的终极解决方案“面包还是头发”。那是2023年3月初,理发的截止日期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谈话发生在会议室里,只有他和我,门关着。在谈话中,他让我重新介绍我的经历,然后开始“关心我家的经济困难”,突然,据他说,他的老板对我的发型不满意。我感觉自己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地狱中做出选择,一边是“正常生活”的希望破灭,职业道路被打乱,经济困难,另一边是性别认同被否定,尊严被践踏,自我凝聚力被击碎。我感到不知所措,然后出现了强烈的恐慌症、焦虑症,然后抑郁和酗酒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回来困扰我。
对于许多没有经历过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我的反应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对我来说,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折磨和折磨之后,这是我的崩溃点。恐惧是独裁者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这就是我与姚明和《南方周末》合作两个月“过度反应”的本质。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恐惧?姚明的答案又是错误的信息。事实上,如果姚明决定在你心中制造恐惧,错误的信息就会成为你的日常生活。2023年2月23日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当天在华沙发表演讲。由于波兰在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我打算写一篇文章,讲述波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波兰为什么扮演这个角色。为此,我采访了几位波兰教授,也采访了一些布鲁塞尔的教授,其中一位是波兰前外交部长。随后,姚明要求我撰写一篇对外交部长的独家采访,尽管我提醒说部长是鹰派,而且有强烈的意见。我在截止日期前一天将初稿交给了他,但随后他要求我重写整篇文章,因为姚明并不赞同部长的鹰派观点。或者说,姚明是普京入侵的狂热支持者。
当时朱莉正在休产假,因为快要生孩子了。姚明却坚持要我先把文章交给朱莉,他才肯修改。这很不寻常。他以“你的逻辑太弱”为由,让我重写了波兰那篇文章四五次,多次小修改,直到已经不是发表的合适时机。这几乎让我无法发表任何文章,因为一方面我不得不让朱莉在她怀孕期间工作,另一方面我每次都要等上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到修改。姚明的目的不难理解。这是他“面包还是头发”的伎俩,是他强势的体现。他试图操纵我,直到我完全被他控制。此外,我甚至不被允许单独与我的受访者见面,我计划好的采访也被随意取消。这对于一名资深记者来说无异于一种羞辱,对于职场中的跨性别者来说更是极大的创伤。

3月初,我开始公开反抗姚,我去找南方周末唯一的女性副总编辑席琳,抱怨他的骚扰。从那以后,我的文章没有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而我两个月的服务,一分钱也没拿到(5月份他们才付了安抚费)。更糟糕的是,姚的歧视和骚扰开始让我出现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并伴有强烈的身体症状。我无法集中精力。几个月前,我从姚的毒害中解脱出来,但阅读对我来说仍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我撤回入学文件之前和之后,我两次与他对峙。第一次是在我和席琳谈话之后。姚吹嘘南方周末的历史,声称我的发型会在高层会议上损害公司的形象。第二次是在4月19日,我穿着黑色连衣裙,戴着闪闪发光的银耳环来到南方周末的办公楼。他回避了我大约 3 个小时,然后才敢在办公室里和我说话。这次是在开放式办公室,尽管他曾建议在封闭的房间里谈话,但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这次,他承认,作为一名经理,他有责任迫使我剪头发。这里再次误导我,他试图说服我,我的技能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位,因为我的文章没有吸引足够的点击量。谎报点击量很容易,因为我无法访问公司的系统。仅凭文章吸引的点击量来评估一个人的新闻技能是不够的。只有小报才会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估其员工作家的表现。
不幸的是,席琳也是我经历过的性别暴力的一部分。她不像姚那样残暴,而是有策略、有技巧。通常情况下,当袭击发生在一个几乎没有既定程序来应对肇事者的组织中时,官僚主义会强烈放大性别暴力。在这方面,我的情况并不例外。席琳是扮演官僚角色的人,但在她自己的任期内,她只代表自己,而不是公司。2023 年 3 月下旬,我被要求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当时我还在犹豫是否要辞职。我不确定这是席琳还是姚的主意。但当我开始要求《南方周末》和姚正式道歉,否则我将公开丑闻时,席琳在 5 月初威胁我,如果我违反保密协议,她将承担“法律后果”。这甚至不是她合作的结束。她想把歧视和骚扰描绘成我和姚的“私人矛盾”而不是社会正义丑闻,以此让《南方周末》免于被追究责任,但同时又认可姚的偏见,避免赞扬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叙事。这是中国异性恋女性在公共领域生存的典型策略。随着跨性别者越来越多地受到当局和新闻机构自我审查的限制,以及性别问题在简体中文世界中日益政治化,对于异性恋女性来说,接受现状确实是明智之举。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部分自称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对跨性别女性采取行动的原因。她们害怕失去现在的生活,就像我在广州生活时所经历的那样。
2023 年 6 月初,我离开广州前往德国柏林,并警告 Celine 不要在中文和英文世界公开这一丑闻。接下来,我争取社会正义的旅程中最戏剧性的时刻到来了。当她玩“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时,Celine 在 5 月份建议我通过“官方渠道”提出投诉,好像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选择。事实上,当我在 3 月下旬决定撤回我的入学文件时,向 HR 提出投诉是我的第一想法。然而,HR 甚至没有回复我的投诉信息。两个月后,就在 Celine 在 5 月份提出“建议”之后,HR 终于开始对我的投诉做出反应,说:“给我点时间了解官方程序。”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没想到 HR 会在处理我的案子之前“了解”官方程序。这里只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公司没有处理性别暴力案件的官方程序,要么官方程序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我甚至要求了解整个过程,但人力资源部拒绝了。两天后,一个自称独立部门的官员就此事联系了我。此后,我整整一个月催促他们,直到我收到警告,他们只说“你的案子正在调查中”。但就在我警告Celine之后,神奇的是,官员一个月来第一次要求我提供证据,但我只有两天时间收集所有证据。这耗尽了我对“官方渠道”的最后一点信任。而我断绝与官员的联系仅几天后,我收到一张盖有南方周末公章的纸条,上面写着我要解决我和姚的“私人矛盾”。可见,所谓的调查独立性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们的策略是连贯的,甚至是协调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尝试其他渠道,但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后,在2023年11月底,我把这个案子发布在了微博和推特上,给《南方周末》施加压力。他们回应了广州一名警察的电话。但别误会,那名警察对我很好,但似乎并不想真正介入这个案子。然而,唯一的问题是,正义尚未到来。

*Celine、Monika 和 Julie 是假名。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