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给我的启示:我们女人生来就是女儿但不一定是母亲
三、四个月前一向乐观开朗的外婆突然和阿姨说自己的生命最多只剩下两年,她甚至说好自己的告别式不要办在教会里,「在殡仪馆简单的仪式就好」。外婆的年纪会想到死亡倒也不让我们感到意外,但是一个对神有着强大信心的人主动提起死亡总让我觉得害怕,我们母女三人很有默契的决定既然阿姨也退休了,就邀请外婆和阿姨一起搬进来,三代五个女人住在一起。
一方面是外婆刚好过了乳癌五年的治疗期,现在开始只要三个月回去追踪即可,她可以离开原来住的城市。听说外婆总在白天一个人看着路上的行人或车辆,应该是很寂寞的,我们也不忍心她这么活着。这几天,我到她的房间看书,她总是害怕我离开视线,我们出去工作回家,她会用力抓着我的手说:「一整天没看到妳,阿嬷好想妳!」以前的外婆和我一样是个有距离感的人,她绝不会抓着我的手。
说起来她是个脾气很好的老人也从来不会抱怨病痛,只是把照顾外婆的责任推给阿姨独自面对也是很大的压力,而且我们都很爱外婆,出于私心也希望能够好好的陪伴她,不论这段时间还有多长。但我没想到没有两三周,我自己也罹癌了,很害怕会增加阿姨和妈妈的压力,本来她们可以不管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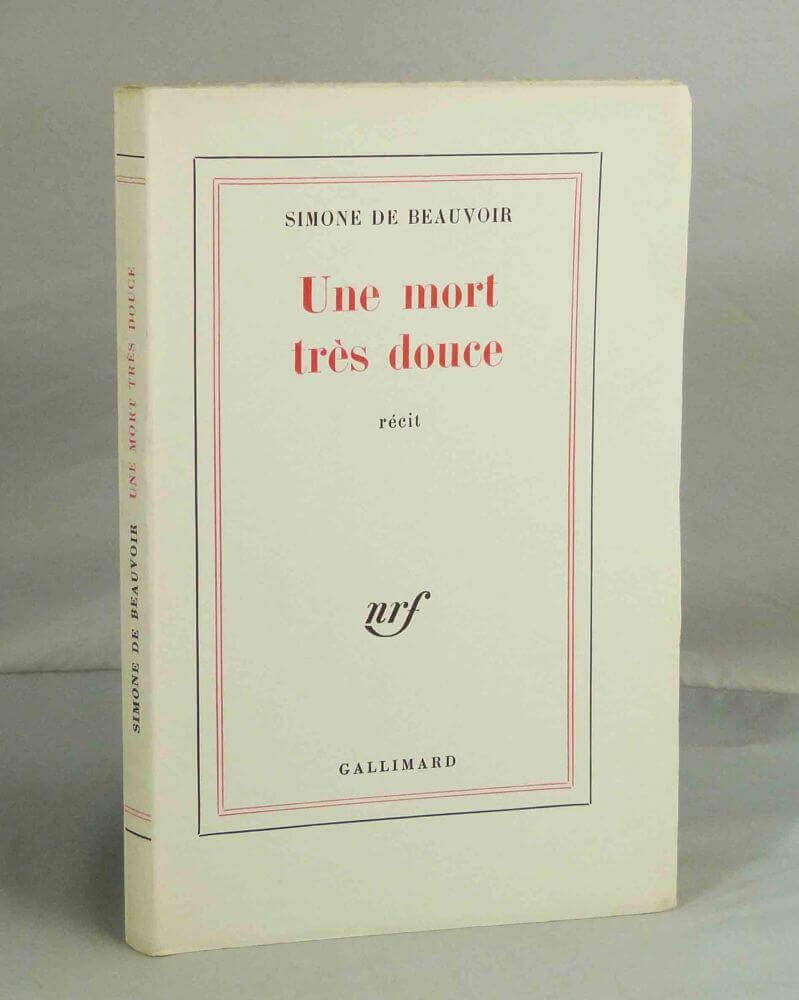
刚好在这段期间阅读了西蒙波娃的伴病笔记《一场极为安详的死亡》,不免将年龄相仿的外婆与波娃母亲做比较。都是虔诚的信徒、出生中产家庭而有相当的教养但也很固执,而因为她们的生病或衰老造成依赖性而让人感觉到一点绝望,同时也因为这种转变而让她们更加有人性——波娃在书中说「动物性」。
1963年,波娃在罗马接到其母亲在巴黎出意外的电话,高龄78岁波娃夫人在巴黎家中摔倒(将近六十年前的78岁应该是很高龄),花了半天的时间才爬行到电话前,拨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来帮忙。因而住院检查,后来照了X光片才发现罹患癌症,这段纪录就从伴病变成母亲临终的纪录。
波娃先是以一名作家出道而后才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而我觉得在这本书中她的身分就是「为人女」。她提到自己母亲因为生病在最后的日子里放下了许多束缚,——宗教上的、社会上的——她过去被囚禁在身为女人、妻子、母亲的躯体中,在住院期间渐渐接受了自己的需要;波娃也作为一个普通人,写出了自己的担忧、猜测,最真诚的回想起自己与母亲过往的爱恨情仇。
另外也写到她母亲在四零年代成为寡妇后积极的展开新生活,丈夫生前是一位逆来顺受的妻子,但丈夫死后急着甩开丈夫的阴影,56岁才重新学习在图书馆里工作,甚至学习义大利语和德语。这段过程就算是发生在今天,好像也可以写进「50+」的网站中,何况是八十年前的老妇人?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于波娃的母亲和她之间的情谊也有许多好奇。身为小小的波娃迷,知道她儿时接受天主教学校的教育,其母亲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却在青少女时期决定放弃信仰,她也选择了一个当时社会上无法接受的同居伴侣关系⋯⋯如此叛逆的女人和一个虔诚的妈妈要如何共处?
书中说她母亲一直让她过于聪颖而害怕她,但母亲总是夸奖她的才华而忽略妹妹——她猜测这或许是妹妹比较像自己的阿姨,而外公对阿姨较为喜爱,因此母亲习惯性的抹灭妹妹——母亲也曾经在她失去信仰时禁止妹妹单独与她见面,并且嫉妒两人间的友谊,但在母亲老年时,她与妹妹较为亲近、与妹妹相处时更自在。
但在我阅读她六零年代的采访时也惊觉发现,即便是被大家视为女性主义,走在时代尖端的哲学家波娃在谈论事情时也两三句不离「沙特说」 ,仿佛以此为依据,当时我想到即使是没有婚姻的约束,女人对男人的爱慕也是一种永恒的定律(我称为诅咒),她提到母亲对于父亲的爱也是以同样的角度陈述。
但读了她在面对母亲最后一程的想法也确实还是很符合现代的思想,「为什么要插管让母亲受罪?」这又让我再度相信她是那位我们认为的哲学家。然而,她对于母亲的爱护与担忧又如此纯粹的就是一个女儿的想法,读了《一场极为安详的死亡》后,我想到我们女人生来就是女儿但不一定是母亲。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