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板凳,沒有拓撲結構
“世紀末板凳的拓撲結構”沒了。
當時五週年慶想了很久才想到一個刁鑽的選題,寫完時我想,六週年慶還能寫什麼。前幾天,我還在想,等成為中年社畜了,我還寫什麼。這下好了,乃末好哉。 “運氣好的話,明天死了就不用再做了”。正如命運看到人們為無法想像美人遲暮而苦惱時,直接帶走了事,所謂“不許人間見白頭”。
當然,仔細推敲起來,我的經歷反而是站在了反面,沒有在最絢爛時戛然而止,而是等思想已成微光,自己蹉跎了幾年才終於被帶走了,反倒是壽則多辱。不過我大可用類似的經歷勸慰自己,該告的別已經提前別過了,真正告別時才不至於太悲傷。
以前的文字只有幾首詩做了存檔,長文都消失於賽博的長河中——我也可以再次勸慰自己,好在自己怠惰,沒白白耗費精力寫長文。我曾經悟出:Conscience, Voice, Safety,構成三元悖論,而詩歌是滿足三者的一個弱解。而今又坍縮成無解。自信於晦澀,“認為已經熟悉了雲和閃電的脾氣”,在懸崖邊走了四年,終於墜落。一切的正常似乎理所應當,所以沒有任何預備動作——然而,一切變幻無常就是理所應當嗎?
上個月我摘錄了一段話,大意是,我們這一代成長的時代沒有落什麼沙,我們絲毫沒擔心過美好的東西會消失。他寫道:“天寶元年的年輕人,沉浸在開元盛世的餘韻中,又怎麼會想到十年後的安史之亂……彼時大唐已經成立了超過120年”。我也不會想到,我的號成為了已經到來的這個不斷失去的時代的腳註——好像每當我以為我做好了面對無常的準備,就會有事情提醒我,不,你沒有。
2018年秋,我寫了《今年黃昏特別多》,那時候好像情況急轉直下,名人密集隕落,平成最後一個夏天也過去了。我寫道(我只存下了這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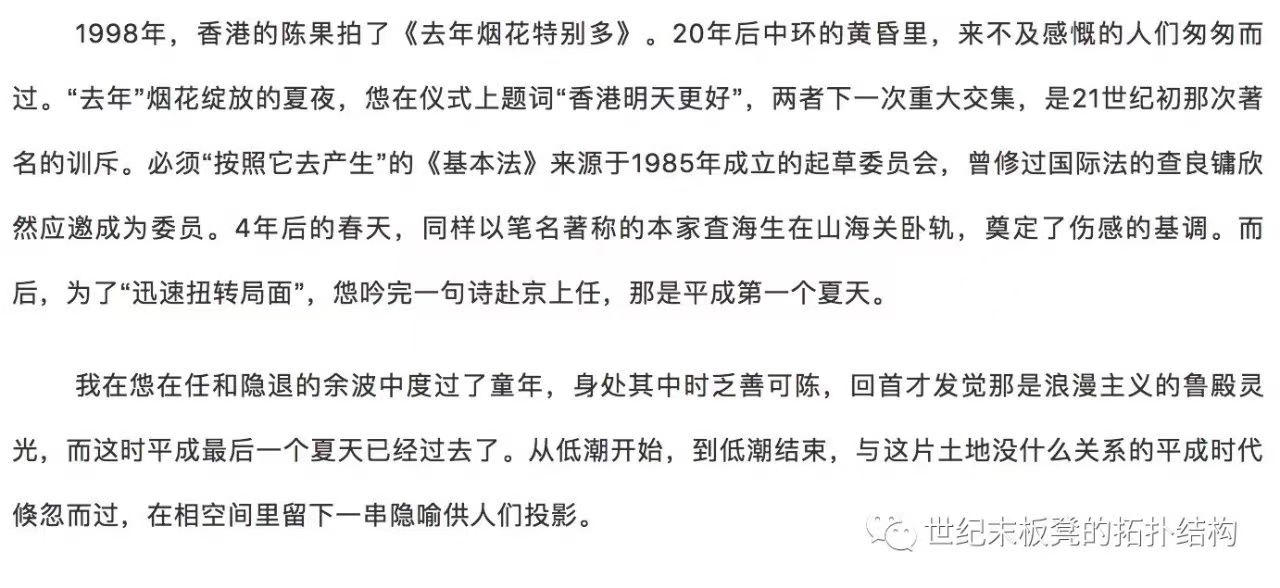
當時我以為,未來回望這年是灰色的。然而現在回憶起2018來簡直像夢一樣。那年我在上海度過了我至今仍懷念的夏天,雖然後來我才知道,這些都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我繼續寫道:“今年,明年,後年,黃昏層層疊加,直到極夜”。那年我還寫了:“以後的每一個夏天都是餘下日子裡最好的夏天”“(奈保爾之後)還有更多的死亡”。這些像是賭氣的話最終一語成讖。然而,果真是不幸言中嗎——其實信號昭然若揭,只是總以為還有餘地。我話說完,卻沒有做好面對這一切的準備——但如果我們本來就沒有義務做這樣的準備呢?前幾天,小西寫道:“若我還在文明社會生活,就別要求我有荒野求生的能力”。所以,最終使我的話一語成讖的,又是什麼呢?我在《今年黃昏特別多》的結尾寫的是:“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我想我還將繼續沒有準備——每當自認為做好了準備,無常便會摧毀這個準備。但我想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雖然還是怠惰——但如果我不寫了,那一定得是我自己不想寫了。
於是轉戰到這裡,起名叫“世紀末板凳”——我曾經以為永遠堅固的拓撲結構已經在冷酷的曲折變換中煙消雲散了。希望你們喜歡。
最後以小謝的文字作結吧(曾經的小謝是多麼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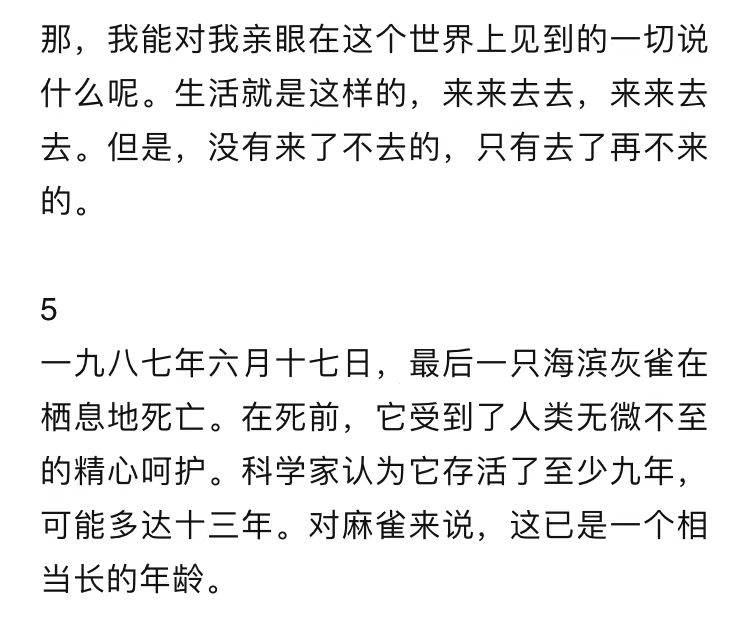
於是我又大可故作雲淡風輕地效作一墓誌銘:2022年6月6日,世紀末板凳的拓撲結構宣告死亡,它存活了至少五年半,對公眾號來說,這已是一個相當長的年齡。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