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的政治學/ 哲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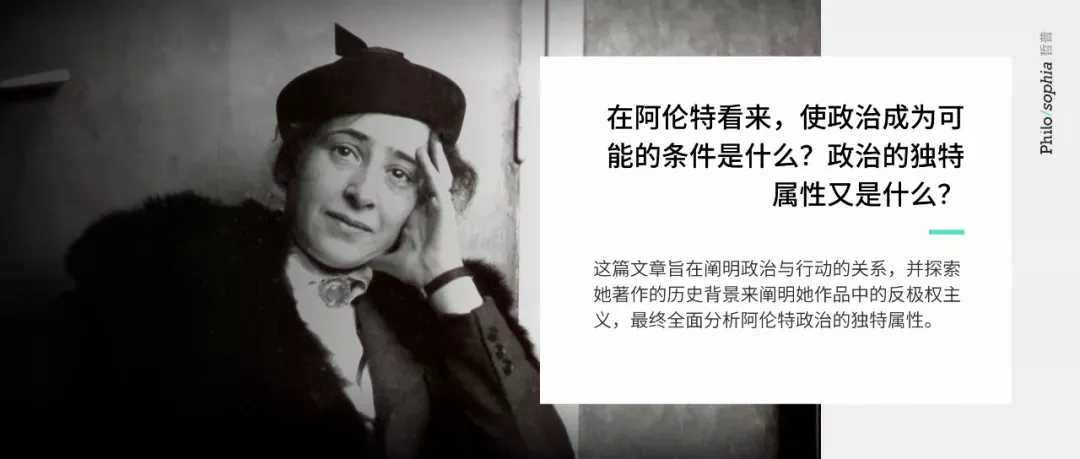
「本文於2021.7.3 原載於公眾號philosophia哲學社」
作者 /烏斷
1 概述
漢娜·阿倫特對政治的定義可以被最好地理解為對人類多元性和自然性的捍衛,及對抗現代性的極權主義傾向,而這只能在掌握她的哲學體係後才能充分理解這一點。她的政治取決於公共自由和對必要性的掌握。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自發的、表達性的、交流性的,但也是不可預測的、捉摸不定的和脆弱的。在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將解釋阿倫特關於人類境況的三元理論,然後通過闡明政治與行動的關係,將她的政治理念置於其中,並最終概述其前提條件。在第二部分,我將通過考察她的方法和探索她著作的歷史背景來闡明她作品中的反極權主義,在她的各種作品之間建立聯繫,並最終全面分析阿倫特筆下的政治的獨特屬性。
2 政治成為可能的前提條件
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認為,人類境況是三方的,包括勞動、工作和行動。由於政治取決於人類的多元性,雖然自然性是「政治思想的核心範疇」,但政治與行動領域的關係最為密切。 [1]
勞動對應於人類生存的生物層面,包括無休止的重複性生產和消費。 [2]在勞動領域,人類是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他們的時間概念遵循自然界的周期性節奏,因為他們像動物一樣追逐無休止的必要性循環。 [3] 然而,人類的存在與動物的區別在於「其運動的直線過程」[4],它貫穿了「生物生命的循環運動」,而這種直線性反映在人類獨特的工作和行動領域。 [5]在「工作」領域,人類是技藝人(homo faber):「世界的建設者和事物的生產者」,能夠駕馭自然,製造出比自然的消費循環更持久的人造物品;因此,在「工作」中,人類能夠展現出自己與動物的區別。 [6] 然而,「工作」的產品獲得了一種異化並外在於生產者的線性生活,因此「工作」是人造的,但不完全是人的。只有在「行動」領域,人類才會通過「行動和言說」在同類中宣稱自己的個體身份:「工作」證明了人類創造能力的集體偉大,而「行動」則允許多元性,即人類的獨特性,而不是集體的「人類」,這使得個人的故事可以得到講述。 [7]更重要的是,通過允許多元中的獨特性,「行動 」實現了「人類的自然條件」,這意味著正是通過言行,每個人都能夠採取意想不到的行動,具有自發性,並為世界帶來一些「獨特的新事物」 。 [8]
「行動」抓住了人類生存的直接性、動態性和自發性,這是政治的基石,而它勞動和工作中基本沒有。 [9]儘管政治不能脫離勞動(生存)或工作(人造),但只有行動才是政治活動的精髓,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沒有明確區分政治和行動,可以說是反映了它們在概念上的接近。 [10] 如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Andrew Norris指出,正是在政治行動中,人們宣稱自己的公共身份,並在此過程中將自己與其他人類聯繫起來,從而賦予「作為人」的意義。 [11] 此外,只有在行動中,權力才會產生:對阿倫特來說,權力的實現「只有在言行未分離、言談不空洞、行跡不粗暴的地方」才可能,也就是說,當言語和行為本身就是目的的時候;權力是一種動態的潛力,在人與人之間「當他們一起行動的時候」湧現,「在他們散開的時候就消失了」 。 [12]阿倫特對暴力和權力進行了區分:暴力是工具性的,它本身不能獲得任何政治合法性,而權力則是從集體行動中產生的,是合法性的根本來源。 [13] 這對韋伯的「目的論」框架提出了挑戰——韋伯認為暴力(脅迫)是政治的核心,因為它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基本工具。就此,她提出了另一個強調集體協議和團結的「交流性」框架。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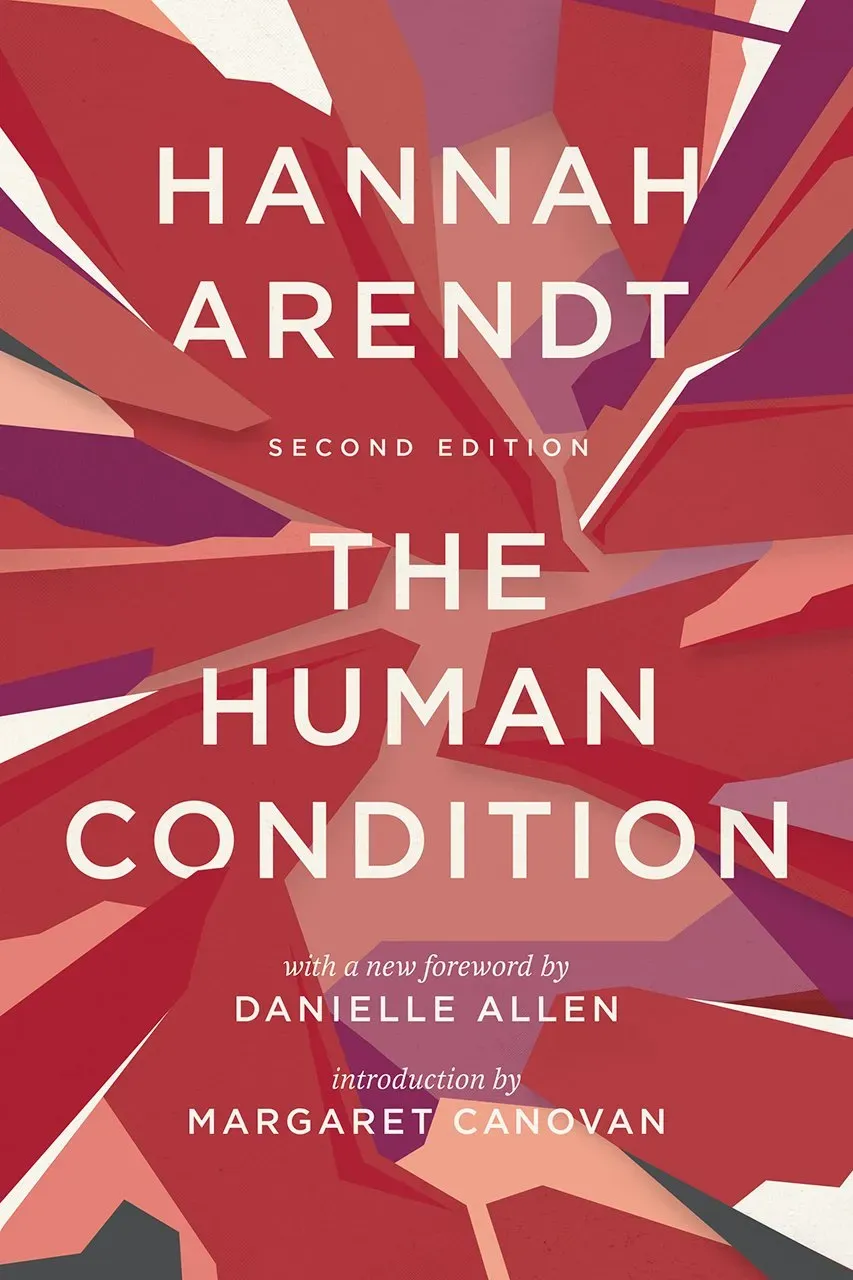
在《人的境況》中,阿倫特斷言,從古希臘的意義上理解,政治本質上是行動和言說,[15]其前提條件是自由。自由一方面需要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需要一個掌握必需品的私人家庭。 [16] 古代意義上的自由既意味著擺脫困境的自由(freedom from necessity),也意味著與平等同伴交往的自由,[17]這對政治來說是必要的,因為前者將人從勞動的維度中解放出來,而後者則使人能夠從事行動的維度。在《政治與自由》中,阿倫特認為,「如果不談論自由,就不能談論政治,」她強調了後者,說自由是「把以前不存在的東西召喚出來的自由」。公共領域是與同伴交往的自由的先決條件,因為它是一個允許人們「被他人看到和聽到」的舞台,並允許「無數的觀點和方面」來說明「一個共同的世界」;換句話說,它是人類多元性的體現,意味著公共性和多樣性,而自然性(行動)只有在有多元性的地方才可能。 [18]公共領域反過來又要求存在一個隱秘的私人領域,阿倫特將其等同於私有財產[19],因為一方面,古代的私人領域,即家庭,是一個人的必需品被管理的地方(通過對婦女和奴隸的統治),沒有它,人就無法超越勞動,進入共同的自由公共世界。另一方面,從更形而上和不那麼殘酷的意義上說,只有從私人領域,人們才能「升入視線」,進入公共領域。如果沒有私人領域庇護人們免受無盡的宣傳,不僅生活會變得「淺薄」,而且公共本身的意義也會喪失。 [20]
如牛津大學國際關係教授Patricia Owens所說,阿倫特關於政治的論點是「主要通過否定來構建的」[21],並且最適合被視為對現代政治或者現代性的批判。她在《人的境況》中對政治的論述具有獨特的難以捉摸和形而上學的特點,這不僅是因為它植根於對人類狀況的整體哲學分析,而且還因為她獨特的注重語源學的方法。她沒有給政治下定義,而是探討了與政治有關的各種詞彙的古希臘、羅馬和教會的起源及其應用;她不以歷史為例,而是傾向於分析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和積極生活(vita activa)的含義變化背後的含義。這主要是因為,如政治理論家謝爾頓·沃林所說,她打算找回在現代化過程中丟失的「過去偉大的政治理論」,以「照亮現在的困境」[22]。儘管她並沒有像他所說的那樣,想找回「佩里克利斯式的民主」或「荷馬史詩般的集會」[23]。在《人的境況》的序言中,她聲稱她並不打算「提供一個答案」或參與「實際的政治」,而是「從我們最新的經驗和我們最近的恐懼的製高點」來重新考慮人類的狀況[24]。她通過「對古希臘政體的理想化描述」來闡述她的政治概念[25]——沃林批評她「歪曲歷史」是對的[26],但她關注的是現代政治世界的不足和偶然性,而不是歷史本身。她對政治的描述更多地反映了現代政治中缺乏的東西,而不是歷史中真正原先存在的東西。

她對現代政治的批判(以及對更廣義的現代性本身的批判)在她對霍布斯、馬克思和韋伯的批判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對她來說,現代性的錯誤在於把工作歸於勞動,把行動歸於工作,而這兩個錯誤往往是相互關聯的。阿倫特認為,霍布斯的政治概念建立在政治對「社會」的錯誤征服上:她聲稱,霍布斯的政治所保護的東西,正是一個由無情的收購者組成的社會。 [27]他忽視了關鍵的「公共和私人」的區別,將與「維持生命」有關的事務公共化,因此將政治變成了以保護為目的的行政管理,通過用工作建立一個偉大的利維坦,使得行動屈從於勞動。 [28]其結果是,積極的政治被理性主義的、工具性的技藝人的工作所取代。 [29]
同樣,馬克思也是政治屈從於社會的產物:在阿倫特看來,政治只是社會利益的反映這一說法,本身就體現了家庭(自然-勞動)的「非自然增長」;而馬克思本人也生活在霍布斯之後的現代,其中公共領域已經「消亡」(wither away)並成為行政管理。 [30]此外,馬克思將工作歸入勞動之下,並主張通過發展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以從勞動(必要性)中解放出來,其結果並不是解放,而是將悠久的工作技巧瓦解在無情的消費循環中,因為大規模生產只會創造更多的貪欲。 [31]在阿倫特看來,馬克思的現代性是對消費主義社會的治理。
她對韋伯的批評沒有那麼直接——但是,在她對官僚機構「作為最社會化的政府形式」的批評中[32],以及對潛藏在「技藝人」思想中的暴力工具性的批評中[33],韋伯所描述的以國家壟斷合法暴力和官僚機構為特徵的現代政治顯然是被指涉的對象。 [34]簡而言之,對阿倫特來說,這三位哲學家的政治概念中(以及延伸到整個現代政治中)都沒有自發性和多元性這一根本性的人類維度。
3 阿倫特政治的獨特屬性
阿倫特對多元性和自然性的再次強調,以及她對現代政治的批判,都可以說是源於她對極權主義的反思。她親身經歷了納粹主義,並觀察了斯大林主義的恐怖,這是現代社會中兩個最令人髮指和最沒有人性的政治制度。她的著作中從未缺少對現代哲學的懷疑,而現代哲學使得這種恐怖機器成為可能。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認為,正是對任何行動的可能性的破壞,以及通過將所有人捆綁在一起成為「大寫的單個人」( One Man of gigantic dimensions)來消滅人類的多元性,才使得極權主義恐怖與一般暴政區分開來。 [35]因此,極權主義的危險性並不僅限於其殘酷性,因為它不僅摧毀了人的肉體,還通過阻止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自發性來熄滅公眾身份的可能性,從而使每個人都可以被替代和摧毀,並在這樣做的時候否認了人類個體的人性。 [36]而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她認為大規模屠殺的核心是在納粹官僚機構中的人放棄了個人自主性和良知——極權主義恐怖的實施者往往是拒絕思考和行動的「正常得可怕」的人,而不是虐待狂。 [37]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診斷為極權主義所缺乏的東西,正是她在《人的境況》中加以肯定的政治的本質,因此可以說她的政治概念從根本上是反極權主義的。 [3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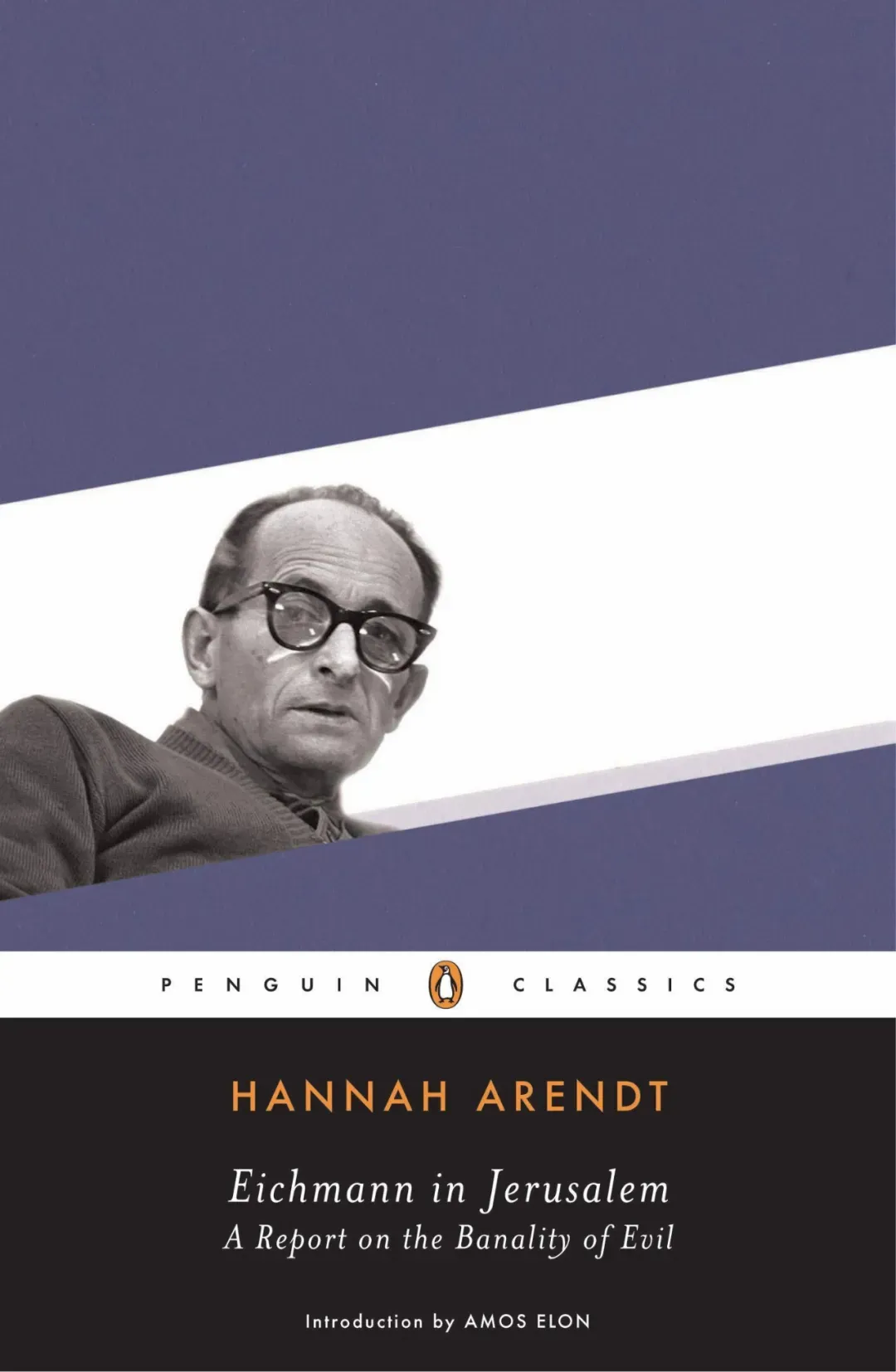
然而,這種隱含的反極權主義也限制和削弱了她的政治概念。一方面,在拒絕現代世界中潛藏的非人性的極權主義傾向時,她的歷史敘述往往忽略了「社會的興起」背後的原因,她沒有解決如下這一惱人的古代悖論:即為了讓一些人從事行動,其他人必須被暴力放逐到私人家庭,接受無情的勞動。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John Levi Martin正確地指出,阿倫特「明知故犯地從一個奴隸制社會中獲取她的概念裝置」,這很令人感到奇怪[40]。而且,也可以說,霍布斯和馬克思的理論所捕捉到的現代性也可以被看作是對少數人的排他性和殘酷的古代自由的反叛,通過將更多的人從勞動領域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正如沃林所批評的,阿倫特的政治常常顯得過於「純粹」,因為它本質上脫離了經濟動機和社會目的,接近於美學領域,因此常常顯得貧乏。 [41]現實中的政治行動很難脫離社會或經濟目的:政治抗議通常涉及某些社會經濟問題,甚至政治討論也必須涉及某些東西。如果公共參與/行動本身不涉及任何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問題,而只是關注表達,那麼這種行為是否會有價值就值得懷疑了。諾里斯準確地指出,她對公共行動本身的讚美使公共道德判斷變得困難,這本身就可能是危險的。 [42]
阿倫特的哲學體系本質上是反極權主義的,而她的政治理念,作為保護極權主義及現代性試圖摧毀的人類要素的嘗試,是獨特、自發、表達、交流的。在阿倫特看來,政治或行動在本體論上是必要的,因為它允許人們超越海德格爾式的「向死而生」的絕望,因為共同的公眾將個人從孤立的死亡中解救出來,而自發的行動與潛在的不朽的言論一起,通過「開始新的東西」,可以打斷毀滅的循環。 [43]用她自己的話說,「政治和行動」提醒我們,「人雖然必須死亡,但不是為了死亡而出生,而是為了創始而出生」,因為它允許個人通過人類世界的故事來表達他們的人類尊嚴。 [44]儘管他們生物意義上的生命是脆弱而短暫的,行動還是拒斥了將個人還原為可替代的部分的極權主義傾向。
此外,儘管這一點在《人的境況》中沒有一貫的闡述而且經常被忽視,但共同的政治世界以及作為政治行為的言論是與「思考和談論我們能夠做的事情」的能力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繫的——而這種能力是針對極權主義無思想性的解藥。 [45]可以說,政治或行動所保留的基本人類要素是面向公眾領域的思考(與之相對的是面向自我的個人沉思),而對一個共同的客觀世界進行獨立思考的能力是良知的先決條件,使人即使在極權主義條件下,在一切都被絕望吞噬、每個人都被暴政隔離的情況下,也能做出分辨是非的道德判斷。 [46]誠然,她的政治觀念也的確是不可預測的、難以捉摸的和脆弱的,因為人們無法知道自發和多元的行動的後果,而「行動」本身的純粹性使它難以獨立於其他事物存在。 [47]然而,正是這種難以捉摸的對人類條件的脆弱維度的表達將人類與工具區分開來,並賦予人類某種尊嚴,這可能會「在罕見的緊要關頭防止災難的發生」。 [48]
4 結語
總而言之,對阿倫特來說,政治是通過自發的言論和行動來表達個人的公共身份,這重申了人的尊嚴。儘管這種政治只有在建立了公共領域和滿足了個人需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而且也是一種難以捉摸和脆弱的表達方式,但它是人性的基本條件。如果沒有它,人類很容易淪入喪失人性的極權主義。 /
註釋與參考文獻:
[1]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7-9
[2] ibid, 96-99
[3] ibid, 160
[4] ibid, 18-19.
[5] Arendt in 3 talks about the life story of individuals and distinguishes eternity(Cyclical) from immortality(linear), which I assume distinguishes the natural/animal from the human. But here she also talks about the life story of individuals, which only corresponds to the domain of action, and I do not quite know where does Work fits in here: it is obviously distinctively human and linear, but it is almost linear on a collective rather than individual scale. Could we maybe discuss this in supervision?
[6]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137-140, 154-160.
[7] ibid, 19, 176-179.
[8] ibid, 178-179
[9] This aspect of human existence described by Arendt reveals much influence by Heidegger's theory of time captured in Nature, History and State, I really do not know whether I have done it justice but I should be able to unpack it more if necessary in supervision.
[10]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8-9
[11] Andrew Norris, 'On public action: rhetoric, opinion and glory in Hannah Arendt's The human condition', Critical Horizons, vol. 14, no. 2 (2013), 212-213.
[12]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199-200
[13]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Pelican Book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81-82.
[14] Jürgen Habermas, 'Hannah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 Social Research, vol. 44, no 1 (1977) , 3-6
[15] To be sure, Arendt did not clearly define politics in THC for the most part of it but instead resorted to exploring ancient notions and etymology, which I will discuss later in the essay
[16]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30-32
[17] ibid, 31-33
[18] ibid, 56-58.
[19] not private wealth
[20]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60-72
[21] Patricia Owens, 'Hannah Arendt: violence and the inescapable fact of humanity', in 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thony F. Lang and John Williams, ed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50-51.
[22] Sheldon S. Wolin, Fugitive democracy: and other essays, Nicholas Xenos,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51-255
[23]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39-240.
[24] ibid, 4-5
[25] Norris, 202-204
[26] Wolin, 240.
[27]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31
[28] Hannah Arendt, 'Politics and Freedom', in Hannah Arendt, Thinking without a bannister: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53–1975, Jerome Kohn, ed.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2018). 246-250.
[29]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99-300
[30] ibid, 76-80.
[31] ibid, 131-133.
[32] ibid, 40.
[33] ibid, 156-157
[34] Max Weber, “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 in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10-313
[35]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2nd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609-611
[36]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612-615; Politics and Freedom, 267
[37]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Classic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2006. 276-279.[38] To be sure, the notion of totalitarianism is not very accurate in historical analyses of the Nazi regime or Stalinism, but her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totalitarianism still sta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analyse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her notion of politics/human condition remains a fundamental one.
[39]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 THC, her definition of totalitarianism expanded to refer more broadly to the deprivation of human identity and the common world, thus of the ability to act and think, which may eventually lead to murderous rule and utmost inhumanity. (THC, 3-5)
[40] John Levi Martin,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the Theory of Action” in Philip Baehr and Philip Walsh. eds., The Anthem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London: Anthem Press). 68
[41] Wolin, 245-247.
[42] Norris, 215-218.
[43]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45-247.
[44] ibid, 246.
[45] ibid, 2-3.
[46] Hannah Arendt,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189-192.
[1]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Pelican Book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3] Arendt, Hannah, and Jerome. Koh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4] Arendt, Hannah. Thinking without a bannister: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53–1975, Jerome Kohn, ed.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2018).
[5]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Classic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2006.
[6] Arendt, Hannah,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2nd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7] Baehr, Philip and Philip Walsh. eds., The Anthem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London: Anthem Press).
[8] Canovan, Margaret. 'Introduction' to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9] Habermas, Jürgen. 'Hannah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 Social Research, vol. 44, no 1 (1977), pp. 3-24
[10] Owens, Patricia 'Hannah Arendt: violence and the inescapable fact of humanity', in 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thony F. Lang and John Williams, ed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41-65.
[11] Weber, Max. “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 in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Wolin, Sheldon S. Fugitive democracy: and other essays, Nicholas Xenos,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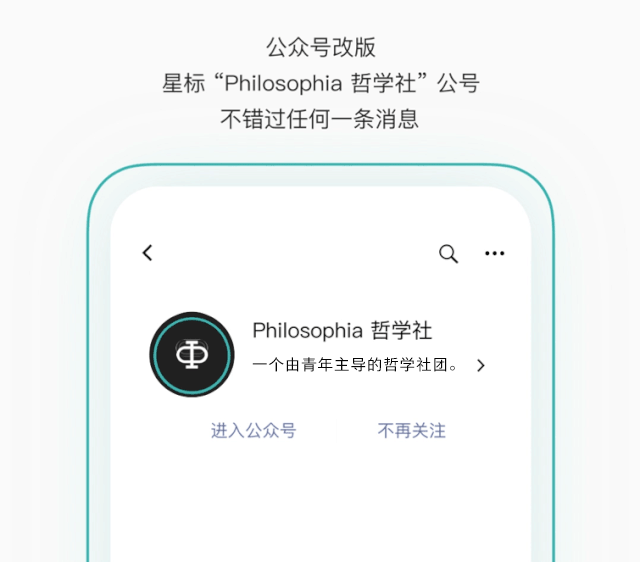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