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评书|细读《Chinese Shadows》之一:「境外势力」
忘记是谁告诉我的还是在哪里听说的,汉学家Simon Leys的作品是学汉语的必读,然而很重要的一本书却再未再版,我千里迢迢买了一本二手书,却收获了惊喜。惊喜在这本二手书扉页上,准备在之后的篇中说,👇说为何细读。
首先,这本《Chinese Shadows》是企鹅出版社在1977、1978年翻译的1974年法语版本的英文版,而似乎之后就没有再版,以至于之前查不到能够买的渠道,只能买二手书。很遗憾,这本书很珍贵,却因为没有再版而不能被更多的人读到,因此,我将把书评写成细读型的,一章一章地读这一本。
其次,Simon Leys是汉学界是一个比较有震撼力的名字,他在其他著作中对汉语诗歌的翻译、分析和文学鉴赏也读来非常的受用,此处按下不表。 Simon Leys是一位比利时-澳大利亚汉学家,真名是Pierre Ryckmans,Simon Leys是他在写作《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时为了避免书籍出版后中共当局禁止他入境中国才开始使用的笔名。果然,在书出版后,他又成功地再次回到中国两次,并就他在文革期间的这些经历写成了《Chinese Shadows》。所以,《Chinese Shadows》是一本非虚构作品,写的是1972-1973年间的事情,但同时也是建立在Simon Leys在1974年就超过二十年的汉语言学习及在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方生活经历上的。文革期间的非虚构,有必要细读吗?有。因为Simon Leys在《Chinese Shadows》中写出的文字至今依然读来如预言一样,或者说有的部分读起来更像是在描述当下的中国。那么,是中国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吗?还是这中国的「阴影」就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这个庞然大物呢?摘四通桥义士喊出的口号中的一句「不要文革要改革」,被之后各个城市的抗议群体继续使用,就说明在当下的中国,倒车进入文革2.0已经成为共识,所以,要细读。
最后,Simon Leys的每一本书几乎在扉页都会写「献给Han Fang」,我想,应该是他的妻子吧。能把每一本书都献给「Han Fang」的人,他一定很爱这位Han Fang,而Simon Leys对于中国的爱也流露在字里行间。那么,他的书我想去读。如果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不爱、可以抛下的人,他再说爱谁我都不会相信(此处参见毛泽东第二位夫人杨开慧和朱德第五位夫人伍若兰)。
《Chinese Shadows》第一章题为「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主要写文革期间在中国的外国人,他希望让读者看到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况以及他们看到的现实——
It may be useful to know what China actually was like when I was there, since it can and will be like that again at any time.
没错,很多那时候荒谬的现实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再来一次,也都有可能降临在你我的头上。
关于游览
Simon Leys谈及了72年中美外交正常化之后络绎不绝到访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到访中国的行程往往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间隙,他们可以游览很多中国人不被允许参观的地方,有些仅仅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些是因为她是汉口一位主教的女儿,而该主教在1920年代是周恩来的朋友。
the foreigners are always put in the same hotel
外国人总是被安排在同一个宾馆, 来来去去就是那么些人,同样的游览路线。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现在,同样有「涉外宾馆」。 Simon Leys幽默地说,如果是列支敦士登也就罢了,中国那么大,怎么能把来游览、到访的所有外国人都安排去看千篇一律的东西、住同一个宾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呢?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农村,乡村中有着非常好客、可爱的中国人,可是为什么要像防贼一样地提防外国人跟当地人接触,而只是给他们看安排好的一切呢?因为有不少在文革期间对中共政府和意识形态怀有「好奇」和好感的外国人很买帐。 Simon Leys指出,这其中不乏在中国因为工作驻了几年的外交工作人员或者到访中国的文艺界外国友人,他们被这样「从摇篮到坟墓」的安排冲昏头脑,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出门不用坐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叫专车等等,而当局这么做可以换来这些外国「友人」在自己国家的媒体上发文对中共进行赞美,然而,他们从未跟中国老百姓说过一个字,甚至面都没见过。
Simon Leys提到一位似乎颇受敬重的外国人,在到访中国后,被当局带到遥远的省份(类似云南等)游览了很多一般外国人到不了的风景区。从中国出来后,他到处宣讲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然而,Simon Leys听到他对一家香港报纸讲自己在那些遥远的省份中的见闻时不断提到在那里的白云寺的见闻,景观和地点没法对应,因为Simon Leys就住在白云寺附近,知道那里并没有在文革期间被很好的保护起来。 Simon Leys提到的这些外国人,很多为人还不错,足够nice,但不知是对极权政权的幼稚还是对自己获得特权的留恋,让他们成为中国政府对外的喉舌,蒙蔽不能够来中国的人。
关于后殖民主义思维方式
Simon Leys在这里提到的不少外国人都驻中国工作,长年配备着翻译员,但是却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中国这个地方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无论在中国多久,都不会说一个字的汉语,也不会有兴趣去学习。在跟其他外国人交谈时,Simon Leys的例子是,餐厅里一位外国友人提起接下来要去一个漂亮的中国城市旅行。 Simon Leys赶忙问是哪个城市。友人说:
「Er, uh, well, you know, these Chinese names...转向翻译员,--Wang, where are we going?」「To Hangchow.」「 Oh yes, to Hankow, I remember now.」
看到这里,我笑不出来。做了几年随身翻译员,我听过太多同样的话,见过太多Simon Leys笔下这样的外国友人了⋯⋯在他们的脑海里,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来未缺席过。带着东印度公司的感觉在亚洲享受着特权,他们从未离开翻译员、专车到过任何一个地方——
Their obedience is rewarded with free trips, which they repay by publishing articles or even books that pretend to describe China.
看到这里,我眼前也确实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一个个外国友人,他们讲英语的时候表现出来对中国的鄙夷用Simon Leys的话说就是从未停止过让我惊讶到乍舌。可惜,他们往往对这种鄙夷没有感觉,继而毫无掩饰。同时,他们更加在乎的是利益、得失,他们可能也有普世价值观,只是他们眼前的中国人被排除在外了。
四种「境外势力」
读到Simon Leys对于中共意识形态中对等级观念的表述,觉得非常准确——
The Maoist authorities, with their fixation on classification, their obsession with hierarchy, arrange them in four different groups.
我很喜欢Simon Leys措辞的幽默和犀利。 👆的「them」指的是「Chinese from abroad who come back to visit the motherland」,也就是说,「外国人」并不被划入这个类别(其实除了「对阶级的执念和等级观念的迷恋」外,Simon Leys忘记提「种族主义观念」了,自然,外国人不包含在内),这四种细分是用来区别回到祖国的海外华人的,文革期间,自然让我想到了众多从海外回到祖国,抱着报效祖国念头的华人,比如老舍⋯⋯所以,四阶层金字塔如下:
最上层「At the top, you have the Chinese who have taken out foreign citizenship.」也就是拿了海外身分的中国人。 Simon Leys举例道,有持有欧洲护照的中国人回来看望母亲,只被允许在家中住一晚,其余在涉外宾馆度过。这些人被严密地跟当地人隔离开来。
第二层「The second class is made up of "compatriots from Taiwan"」,就是台湾同胞了,当然,Simon Leys 也强调,实际操作中主要是指在日本或者美国生活过的台湾人。这部分人很少见。
第三层「The third class, the Overseas Chinese, is more numerous. Usually they are well-to-do businessmen from Southeast Asia who enjoy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patriotic pride in their mother country, wealth and ease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y live.」如述,祖先下南洋的富有华人既在自己的「母国」享有爱国盛名,又在南洋国家享受财富;既寻了根,又不忘本,还可以继续享受并非受限制的小资生活。
最底层「At the bottom one finds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most of whom come to China only to visit their relatives in Kwangtung province.」最下面一层的人数最多,日日过关,更是跟当地人交流密切,Simon Leys也提到正是他们来去之间的带来了港澳如同另一个世界的美好,从而令广州在「山高皇帝远」的情况下最先看到世界的模样。
经过对人「成分」的层层划分,人们被与政权口中的「人民」隔开,为什么呢?因为:
The recurring nightmare of the Maoist bureaucrats is that the foreigners might have fanned out into the countryside and even -- this is the worst -- managed to make some spontaneous and unsupervised contact with people.
Simon Leys对于毛时代官员看得很准。他们重复的噩梦确实是害怕如果有外国人能够跟「人民」进行随意的、不受监督的对话。而文革五年的训练表明,他们是成功的。 Simon Leys讲到自己曾经连问路都被拒绝。 「也不能怪他们」Simon Leys说,毕竟拥有一本Dickens小说都是反革命,跟外国人交谈不知道会被说成是是什么呢。
孤立与隔离
With its nightmarish obsession that foreigners may eventually (though as I say quite hypothetically) achieve unmonitored contacts with the people, the Maoist government has revived a great many privileges, special status rights, and waivers for foreigners in order to keep them even more isolated.
因为他们噩梦般害怕人民与外国人无障碍的接触,他们给予外国人很多特权,特殊身分等等,这样他们就不用跟人民接触了。
有意思的是,Simon Leys有预见性地说,于他们而言,最理想的是一个大型国家公园😄人民在这个大型国家公园里可以住、吃喝玩乐,并自给自足、繁衍生息,里面的人再也不想走出这个大型国家公园。很有意思的设想,这些其实差不多都已经实现了😄只是,因为人不是机器人,有过走出国门的经历就不是所有的人会再次回到那个国家公园里了,总会有人想要有自己的选择,寻找自己的所爱。
人是社会的动物,长期与世界的隔离与孤立让生活在这个大型国家公园里的人听惯了外面都想要颠覆我们的说辞,也逐渐相信了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了「别人就见不得我们好」这样的无稽之谈,久而久之,人性中最原本的跟人(任何人)进行真挚交流的本能慢慢遗失殆尽。这一点, 算是在第一章中我最同意Simon Leys的一点:
「 The perpetual violence done to their inborn feelings, the need to conceal what they feel and do the opposite, the duty to report to the authorities (they inform as informers, but they also confess), the sometimes subtle, sometimes brutal, wrenching distortion of all their human relationships -- all this does not differ in kind from the common lot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but it is brought to such a pitch for them that it can cause a real disruption of personality . 」
后来,我在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知道Personality的扭曲和变态是多么可怕,又是多么有害,对人、社会、环境、世界、地球。而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想像着外部环境都是想要谋害自己的人,失去了对基本人性的信任、认知,自然会失去共情能力、同理心,甚至同情心。这样的情况看得太多,可叹的是,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认识、爱过的人啊。
只剩饕餮
Simon Leys写道,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如果一个外国人能够说汉语,将会非常容易地就融入到当地社会和当地人群中,是毛泽东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和猜忌,并像扬沙子一样弄得一发不可收拾。自此,外国人再不能跟友好的中国老百姓毫无猜忌地生活,甚至连交谈都难。 Simon Leys也感叹曾经的北京是那样一座文化之城,老北京的文化是浸润在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里的,甚至遛鸟人的一举一动都是文化,可是,那所有的文化都被文化大革命抹煞掉了,读他的句子,我的心也一样的痛,痛那个曾经几十年前我记忆中再也找不到的北京,痛一个个其他的城市,痛文化的被消灭——
all that gave Peking its lovely, diverse, and wonderful face, all that made it into an incredibly civilised city, all that made the ordinary Pekingese -- with their truculence, their verve, their quick and subtle minds, their art of living -- a natural aristocracy within the nation, all this has gone, disappeared forever.
当文化不再,人们因为自己家的藏书而恐惧,日常生活也被害怕笼罩,那还剩下什么呢? Simon Leys描述到,最终,剩下或多或少还没有被「污染」的几乎是唯一的可做事情就是到饭店饕餮一番了。当然,这还是指文革时期的便宜饭店,比较有生活气息的那种。或许读者会觉得熟悉,之后,我们生活中也见到很多网红或者一般的人,谈到自己就说自己是「吃货」,其他什么一概不关心,更遑论政治、自由、民主。不错,饕餮而已,却成了几乎最安全的行为方式。
章节末,Simon Leys指出,政府的性质决定了这个国家只会做出一些策略的改变,其本质不会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因此,期盼改变的是做白日梦,也是对历史的perspective没有一个足够的了解,这样的totalitarian政府有的会是「 times of relative relaxation 」,但如果期望政权有个新方向是荒谬的。
第一章的细读已经是长篇大论了。在阅读第一章的时候,我感受到Simon Leys对中国这片土地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热爱,毕竟,这是从他19岁第一次旅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的一门语言,一个文化。然而,那个政权不喜欢质疑与批评的声音,他即便用笔名,最终也被揭发出来,似乎不再能进入中国了。这么多年以后,我读他的文字依旧感同身受,跟他一起哀悼曾深爱的那片土地。之所以那么痛,是因为爱着,在乎着,而一片土地,任何人都可以去爱它,何分你我?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讀者送我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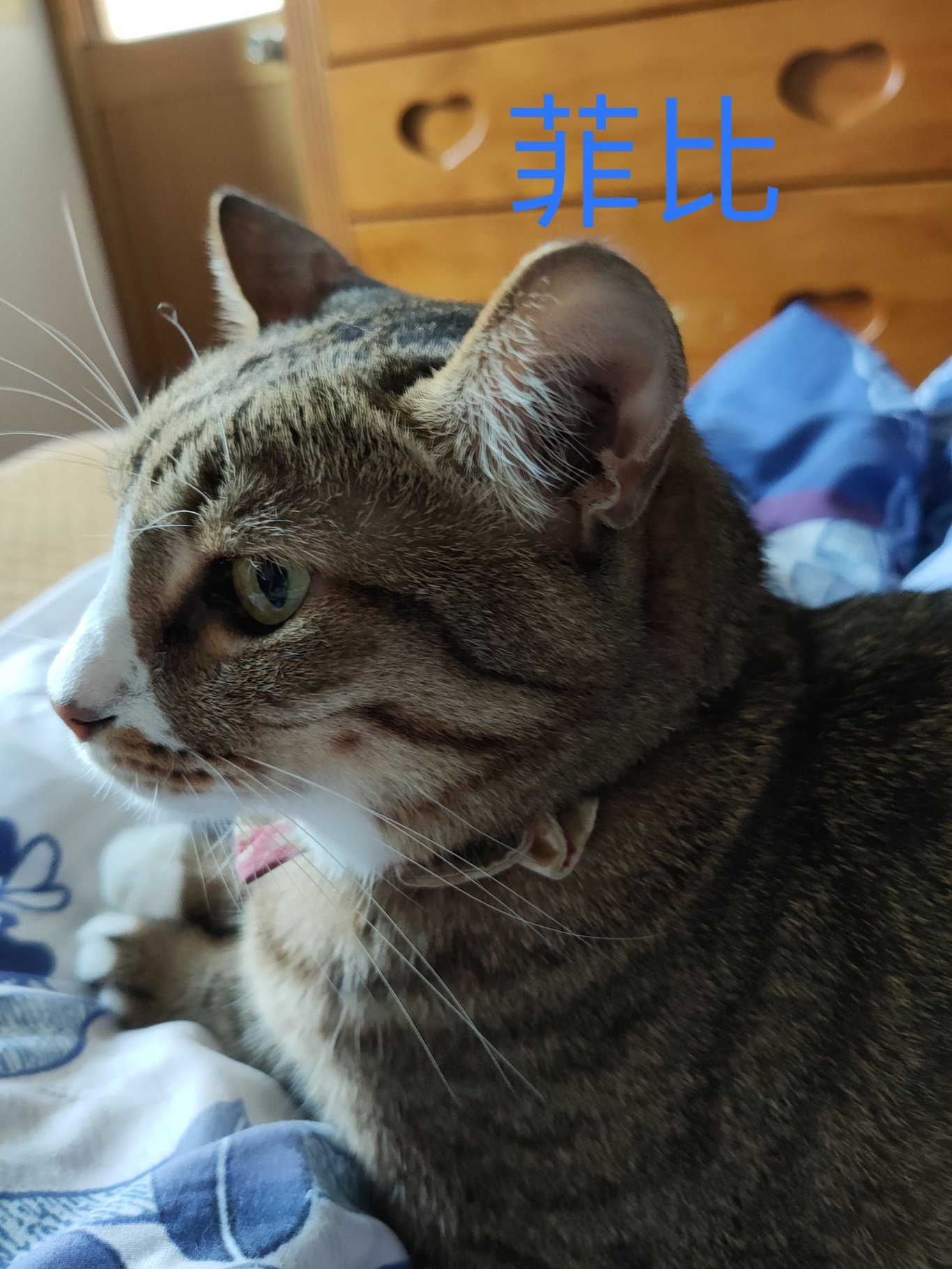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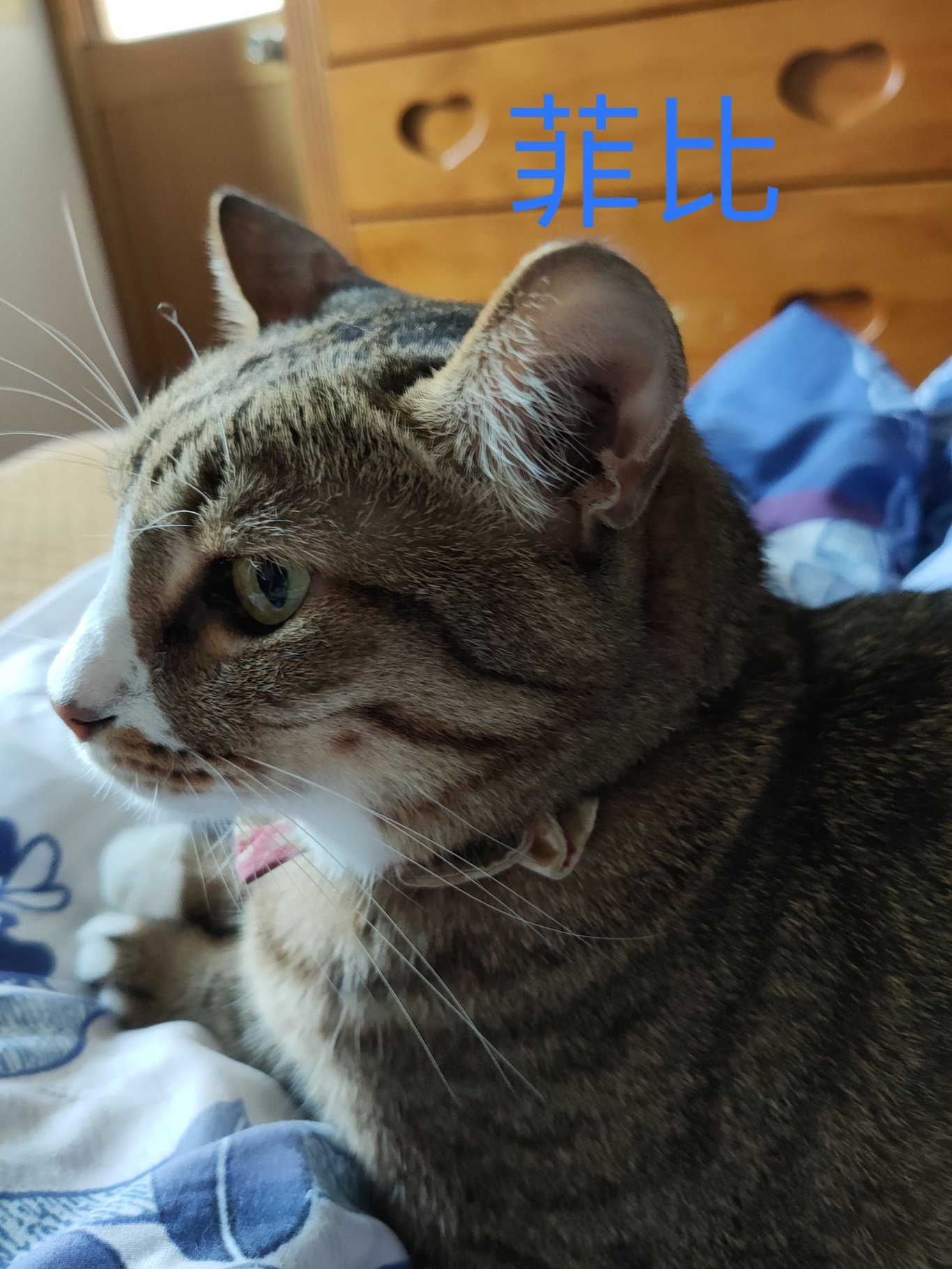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