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超越後蘇聯時代

【注】本文作者Ileana Nachescu 是一位作家和學者。她在社會主義的羅馬尼亞長大,在結束國家社會主義和齊奧塞斯庫的獨裁統治的起義中長大。她作為一名國際研究生來到美國,並完成了婦女研究的博士學位。她的文章曾出現在《密歇根季刊》、《暴風雨》、《阿提克斯評論》和其他地方。她目前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集《社會主義童年回憶錄》。
本文將以第一人稱敘述。
📌 如果您錯過了我們的“烏克蘭系列” ,可以在下面回顧:
- 《一個“賺大錢的完美機遇” 1⃣️ 》
- 《多元化主流2⃣️ 》
- 《 當你處在雙面夾擊的火力之下3⃣️ 》
- 《 ”反對所有邊界,抵制所有帝國,對抗所有戰爭” — 東西方衝突中的烏克蘭4⃣️ 》
- 《 “人民的自由,帝國去死” — 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對局勢的分析5⃣️ 》
- 《俄羅斯的選擇,和這一切災難的根源:烏克蘭系列6⃣️ 》
- 《這一次,不成功便成仁:烏克蘭戰爭7⃣️ 》
- 《制裁的”作用”是什麼? :烏克蘭戰爭8⃣️ — 從“倫敦格勒”到北京》
- 《從北京到世界:烏克蘭戰爭(9) - 一個危機重重的新全球格局》

“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實際上很了解對方。這也許是這場反常的、完全不必要的戰爭中最可悲的諷刺”,烏克蘭記者娜塔莉亞·古梅紐克寫道,“我們彼此知道對方的心理。我們理解對方的語言。我們有著共同的蘇聯歷史”。
古梅紐克的比較強調了兩個如此看似相似的國家可以有多麼地不同。
這兩個國家的共同點讓許多外國評論家感到困惑,並由此產生了很多誤解。以電影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而聞名的詹姆斯·戴維·萬斯,和美國國會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共同點,但他們最初都同意,烏克蘭的戰爭不值得美國軍事干預。他們似乎認為,這只不過是一些東歐人與其他東歐人之間的戰鬥,是一場局部的衝突。雖然他們後來都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但他們短暫的一致性強調了西方對烏克蘭的誤解有時會幻想出怪異的關係。
對戰爭的報導主要由來自西方的白人、以男性面孔主導,這當然沒什麼幫助。很少有外國名字,甚至更少有口音。如果對烏克蘭人進行採訪,他們通常是扮演含淚的、驚恐的證人角色。他們很少作為自己的歷史專家出現。在這些被忽略的人中,有數百萬在後社會主義時期的移民潮中來到西方的東歐人,他們遠遠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作為難民到來的少數人。那些早期的群體受到讚譽,只因為他們關於“社會主義” 創傷的敘述在冷戰的背景下顯得很恰當。然而,較新的移民,是由於東歐社會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開放後遭受的巨大衝擊,而被帶到西方,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
在很大程度上,由於這些沉默,對這場戰爭的巨大誤解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得到遏制,即認為“它僅僅是自相殘殺,是冷戰的續集,演繹著從蘇聯時代開始的沸騰的怨恨”。實際上,東歐和世界上任何地區一樣被全球力量所塑造: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父權專制主義和其他形式的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全球移民(由所有前述內容構成)都與這場戰爭的根源深深糾纏在一起。只有通過超越“自由的西方” 與“專制的東方” 這種過時的二分法來理解東歐,我們才能開始把握戰爭的意義,並想像新的團結。
雖然這場衝突是在國家層面上進行的 — — 而諸如歐盟和北約這樣的跨國實體在背景中徘徊— — 但將這場戰爭放在東歐作為一個地區的背景下思考,是至關重要的。
在下文中,我將重溫我把東歐作為一個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規則、主題和限制的經歷。 2000年,在社會主義結束大約十年後,我參加了在烏克蘭哈希夫(Хащів) 舉行的福羅斯暑期學院,當時俄羅斯和烏克蘭都還對來自西方的新事物持開放態度,知識分子在經過多年的被審查後,正開始嘗試與他們的西方同事進行對話。 20年後,儘管有經濟和軍事聯盟,東歐仍然不是西方,也不是“第三世界”,它以自己的方式體驗全球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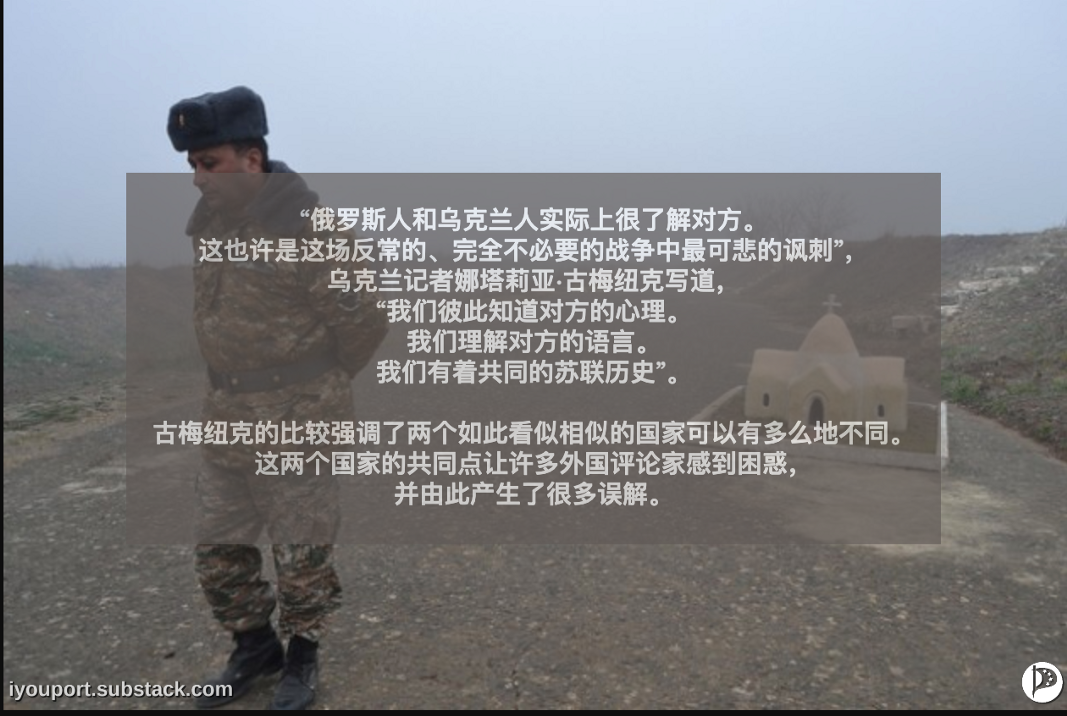
出租車轉彎以避開一輛從相反方向駛來的汽車,它的車燈讓我們有一瞬間的失明。我試著看了看表,猜測我們還有多長時間才能到達。我們的方向對了嗎?迷路了嗎?無法判斷。道路已經從辛菲羅波爾外的一條雙車道公路變成了一條被樹林包圍的更窄的路。我知道這次旅行將持續一個多小時,只是沒有預料到會是在完全黑暗的情況下。我沒有理由不信任出租車司機,但我也無法與他交流。他不會說英語、羅馬尼亞語、法語,甚至德語。而我不會說俄語或烏克蘭語。那是2000年的夏天,當時還沒有手機。我在一個我不懂語言的外國,在一條荒涼的路上,在黑漆漆的夜晚,坐在一個我不認識的人駕駛的車裡。我不斷告訴自己,我在晚上被綁架的可能性並不比白天更大。這個想法並沒有帶來什麼安慰。
我終於看到了一簇燈光,原來是一條街道,不遠處還有一棟高樓。司機把車停了下來,幫我拿著行李。我們穿過一個花園,走在一條由裝飾燈籠照亮的蜿蜒小路上。我可以聽到不遠處的海浪聲。我呼吸著黑海的微風。我來到了我的目的地,第四屆福羅斯性別研究暑期學院。
該活動由哈爾科夫性別研究中心在麥克阿瑟基金會的資助下,在黑海上的克里米亞度假小鎮福羅斯舉辦,旨在將性別研究作為後蘇聯國家的一門學科。在1997年至2008年的十多年間,該活動每年都會舉辦。它鼓勵整個東歐的教員教授性別研究課程並組織學術中心。哈爾科夫中心出版了一本雜誌和一套叢書,並分發了由暑期班學員制定的教學大綱。我在自己的母校創辦了一個女性研究中心,事實上,我在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度過了一年後,正處於過渡期,那是一段幸福的時光,我想讀什麼就讀什麼,也是第一次可以訪問美國的圖書館。我期待在這個暑期學院找到社區。事實上我找到的東西比期待的更多。
從來沒有人認為我同時是“西方人” 和羅馬尼亞人,但這正是那個夏天發生的事。大多數與會者來自前蘇聯共和國 — — 烏克蘭、俄羅斯、格魯吉亞、白俄羅斯 — — 而我們這些來自後蘇聯空間之外的人被視為非常與眾不同。如果我分享一塊巧克力或一支香煙,我的同事就會送來讚許的目光。還有三位來自後蘇聯空間以外的學生,兩個來自捷克共和國的年輕學者,我很羨慕他們優雅的英語,還有我的室友塔尼婭,我和她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告訴我,她教了一門曾經兩次不存在的學科:南斯拉夫經濟學。那是在巴爾幹戰爭之後。
社會主義歷史的殘餘在酒店的野蠻主義建築和家具上表現得很明顯,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美好。酒店的陽台可以俯瞰黑海,寬闊的陽台不僅可以放置桌子和椅子,還可以放置一張床,這樣人們就可以躺在這裡聽著海浪聲入睡。酒店有一個療養院,這讓我想起了社會主義時代我和祖父母一起度假的情景,如果有醫生的介紹,一些服務,如泥漿浴、水療和礦泉浴就可以是免費的。在社會主義時期,我的祖父母和父母以及我認識的幾乎所有人都去過療養院,享受這種治療,通常由他們的工會支付。療養院的醫生給了我一個推薦信,我就享受了酒店的礦泉浴。
參加暑期學校的學者們大多是職業生涯初期或仍在讀研究生,就像我一樣 — — 包括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們來自第比利斯和聖彼得堡、哈爾科夫和莫斯科。會議的語言是俄語和英語,每天上午有一個講座,下午有一個討論。在一個被海風冷卻的房間裡,我們中的一些人坐在地板上,另一些人則坐在椅子和沙發上,在炎熱的天氣裡用我們必須閱讀的文章的複印件當扇子為自己搧風。我們可以使用複印機、圖書館和打字機,我們還收到了書籍和裝訂好的論文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機構無法負擔的。
一些支持研討會的學者曾與Women in Black 運動有聯繫,這是一個鬆散的和平活動家網絡,曾抗議對巴勒斯坦的佔領和前南斯拉夫的戰爭。我們知道,民族主義及其父權制的基礎是敵人,鑑於我們地區復雜的歷史,這是一個恰當的信息。我記得一場充滿笑聲的漫長辯論,討論的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弗拉基米爾·普京(當時正處於他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和弗拉尼奧·圖季曼等民族主義領導人的所謂“陽剛之氣” 的表現。我們了解到,女性給他們寄去了情書和自己的裸體照片。與人們不得不對社會主義領導人、國家的“國父” 表達所謂的革命之愛相比,我們的研討會不正是一種進步嗎?討論在晚餐時繼續進行,我們大笑並抽著煙,儘管我們中的一些人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 — — 一些人懂英語,另一些人懂俄語或烏克蘭語,還有一些其他語言 — — 但很明顯,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歷史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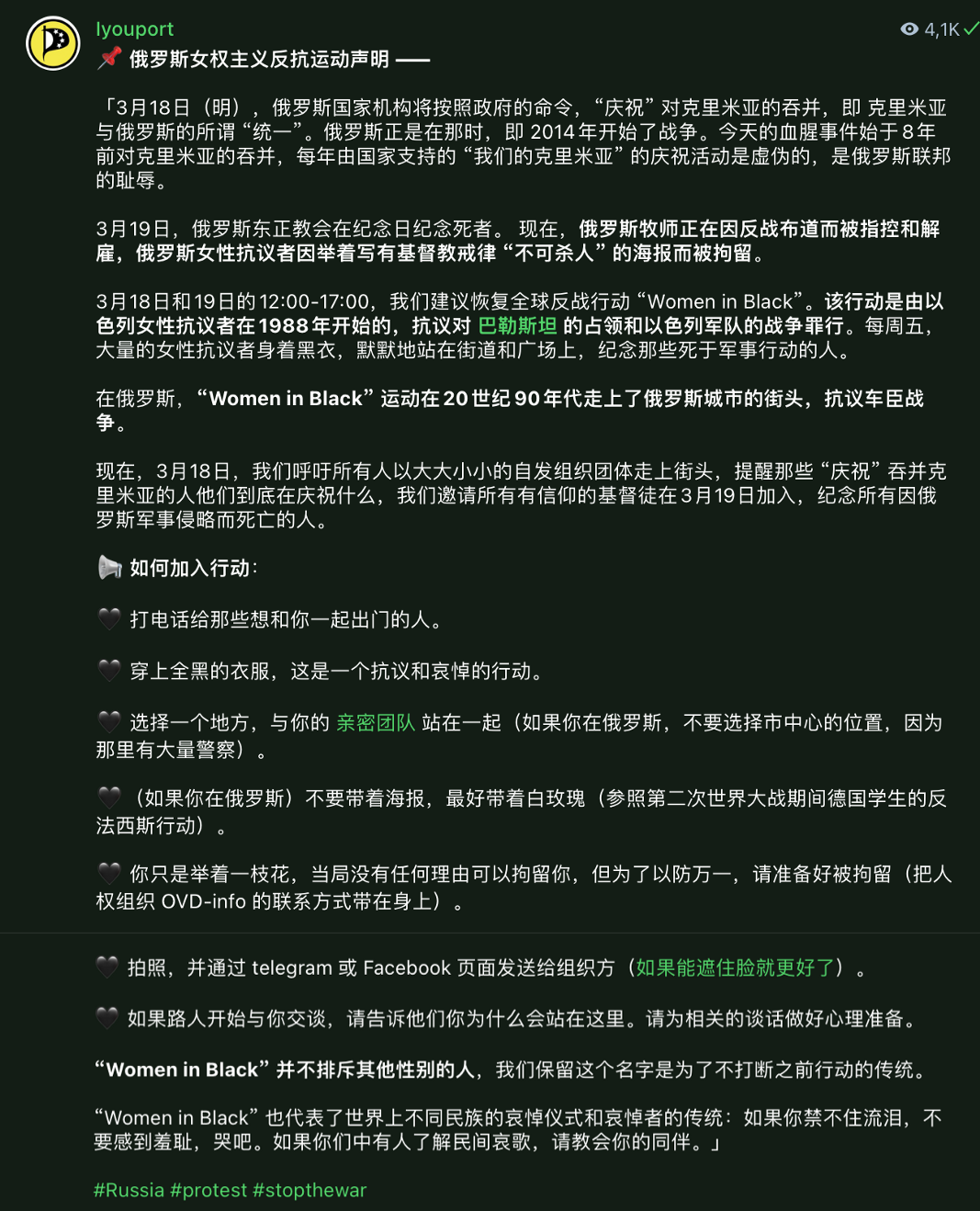
20年後,東歐已經被分割了好幾次:一些國家加入了歐盟,另一些國家加入了北約,還有一些國家一直處於這些空間的邊緣。雖然克里米亞在2014年被吞併,但福羅斯療養院仍然接受預訂。烏克蘭的女權主義者一直在繼續他們的工作。現在所有主要大學都有婦女研究中心。然而,在俄羅斯,異議被壓制了,正如女權主義朋克搖滾樂隊Pussy Riot 的成員在抗議普京與東正教會的緊密聯繫時所遭遇的那樣。
30年的全球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財富積累,尤其是白人男性。歷史上任何時候,地球上的財富都沒有如此高度集中在如此少數的白人男性手中。並非所有這些人都對將他們的巨大財富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感興趣,但這只是一個運氣和利用的問題:今天他們正在發射一枚由穿著燕尾服風格的宇航員操縱的火箭,明天他們可能決心利用媒體將他們最離奇的幻想播撒在數百萬人的心中。今天他們正在為他們的女朋友建造與山巔一樣大的豪華遊艇,明天,他們就可能會決定入侵一個擁有4000萬人口的國家。誰能阻止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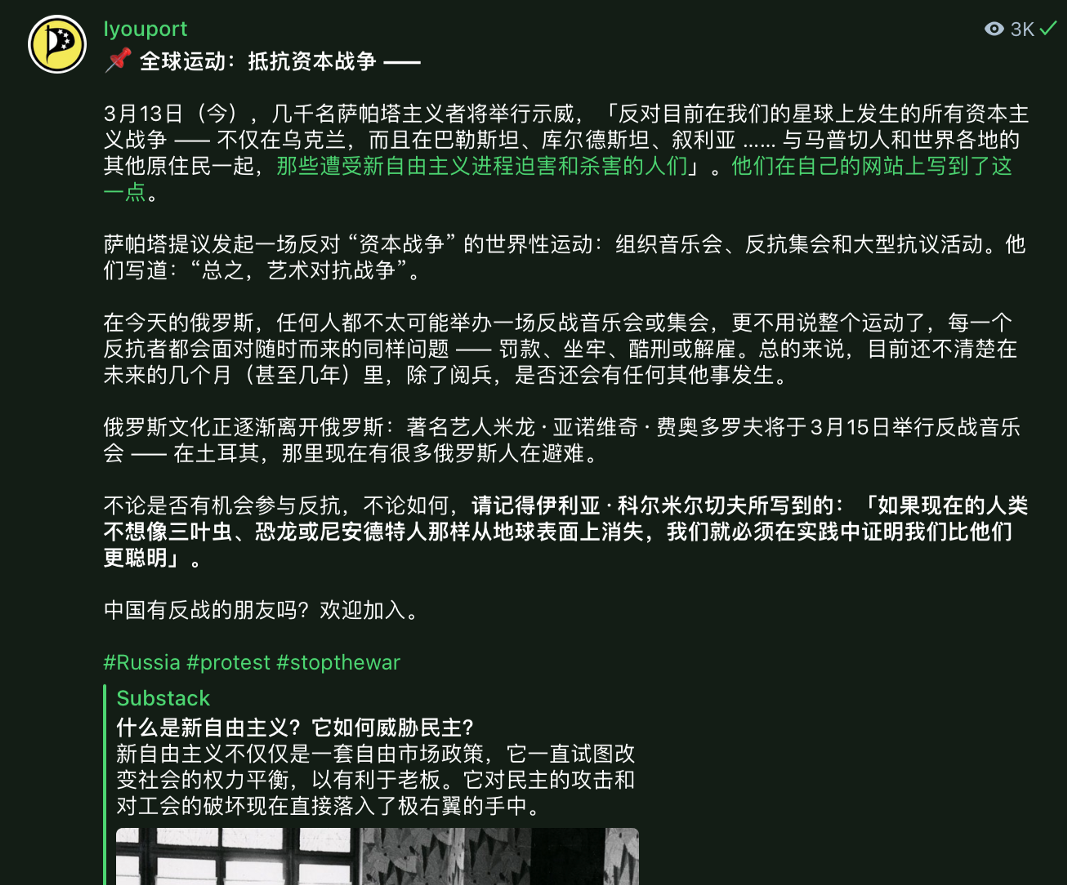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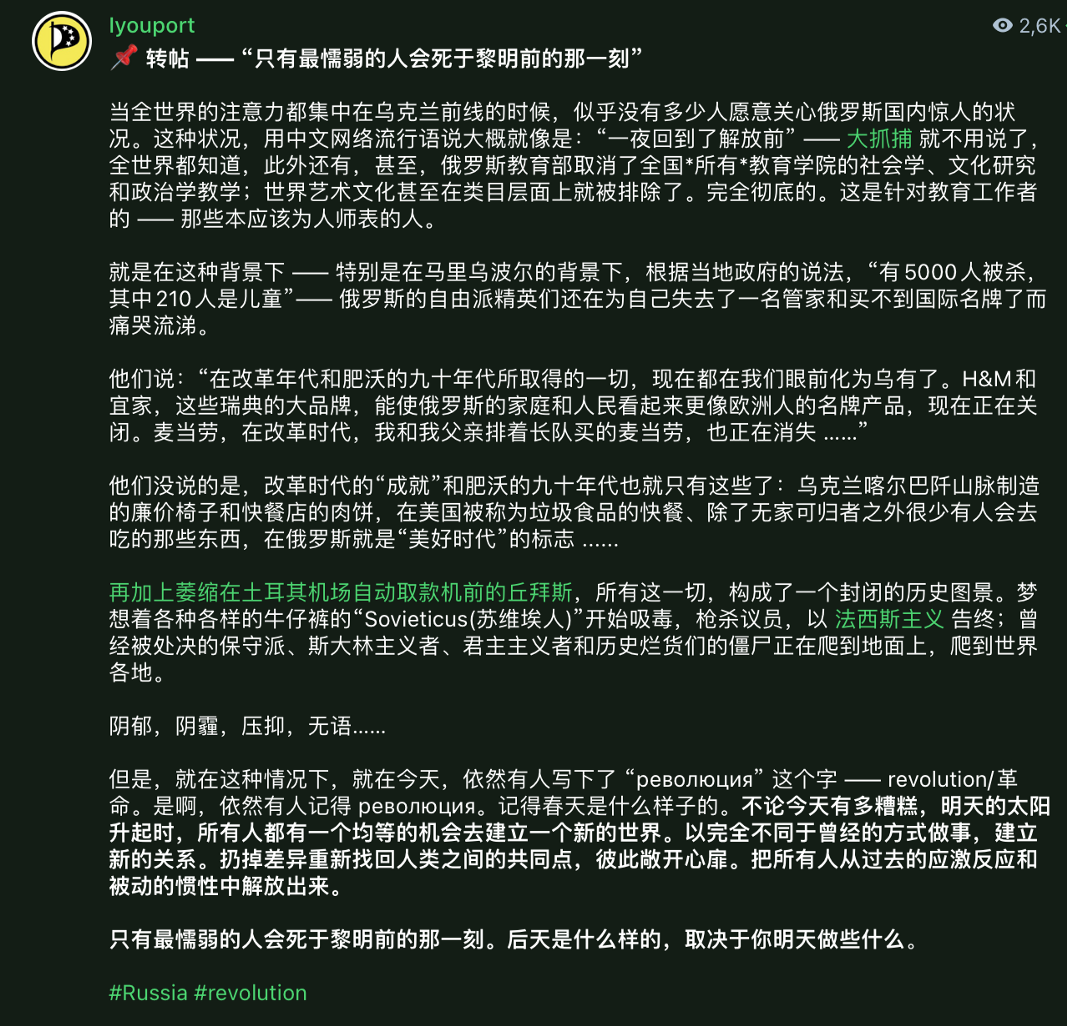
當然,過去也有獨裁者對其臣民積累了無法控制的權力,也有一些人通過許多人的痛苦積累了難以想像的財富。但是,我們當代寡頭的財富規模之大,使得任何與過去的比較都變得無關緊要了。然而,他們也是人類,我們需要提醒自己這點,他們是性情無常的老者,小氣、愛發牢騷、愛操縱,但畢竟不一定能比其他人類更有智慧。然而,由於權力,他們的奇思妙想可以摧毀數百萬人的生活。
普京的行為只能被正確地理解為是這些寡頭之一的行為。雖然他的個人財富隱藏得很好,且可能超過2000億美元,這將使他成為地球上排名前三的最富有的男人之一。因此,普京與其說是某種專制歷史的產物,不如說是共產主義遺產的產物,畢竟共產主義在30年前就結束了。他同時也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產物,他的行為可以理解為與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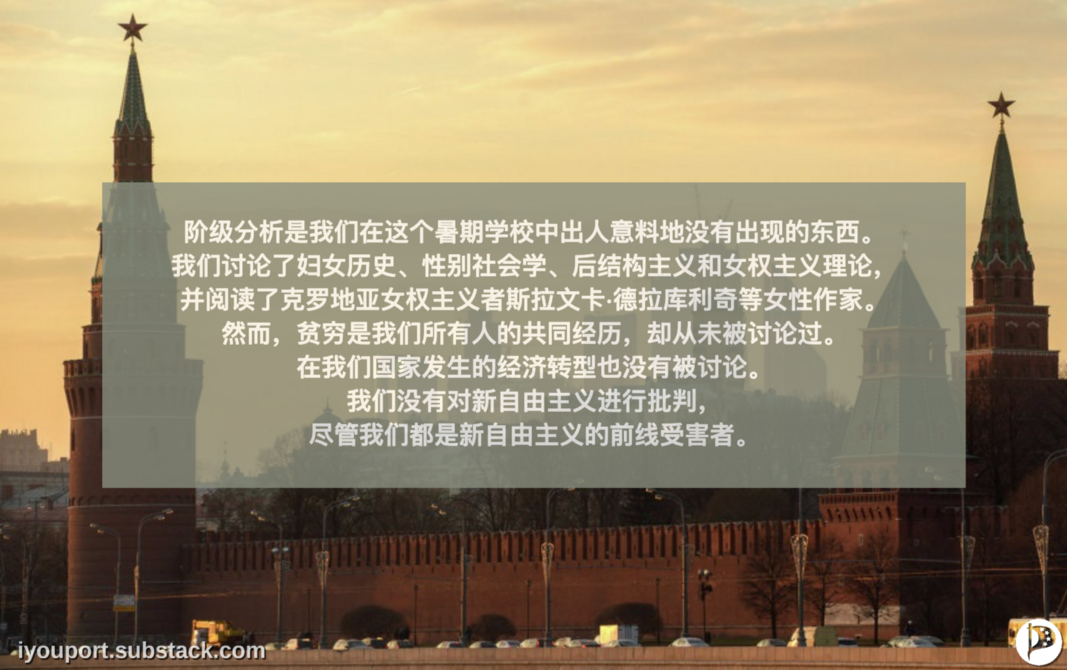
自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的最後時刻以來,從來沒有一個獨裁者聽起來如此地不正常,如此自欺欺人,如此與現實開戰。 1989年12月,齊奧塞斯庫堅稱外國特工在操縱原本順從的民眾,而這些民眾只想要社會主義和他的領導,而工人就在他發表最後講話的陽台外抗議他的統治。沒有什麼能刺穿他的信念— — 甚至,顯然,直到他被帶到行刑隊面前。同樣,沒有什麼能戳穿普京關於吸毒者、納粹分子和性變態者據稱威脅到俄羅斯邊境的巴洛克式想法— — 也沒有什麼能戳穿戰爭的普遍藉口,即編造的關於另一方的侵略行為。
同樣,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不是一場“俄羅斯” 的戰爭,這是普京的戰爭。非營利性監督機構“記者無國界” 將俄羅斯的新聞自由度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50。然而,在俄羅斯有近6000人在反對戰爭的抗議中被逮捕。 《新報》(Novaya Gazeta)以烏克蘭語出版週五版,以示反抗,普京警告其主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國際獎項不會保護他。俄羅斯女權主義者也一直在呼籲抵制戰爭,概述了戰爭是如何影響大部分平民和婦女的。

畢竟,富人總是有辦法避免戰爭的危險。富裕的烏克蘭人已經能夠乘坐私人飛機離開自己的國家;他們很可能已經擁有多個公民身份,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難民身份。在另一邊,正是最貧窮的俄羅斯人充實了軍隊的隊伍,他們來自沒有資源或關係的家庭,無法避免義務兵役。美國製裁造成的通貨膨脹,拜登政府希望能藉此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俄羅斯的寡頭,已經開始對普通俄羅斯人的生活造成嚴重破壞。普通的烏克蘭人正徒步逃離他們被圍困的國家,手裡拿著自己僅有的一點點財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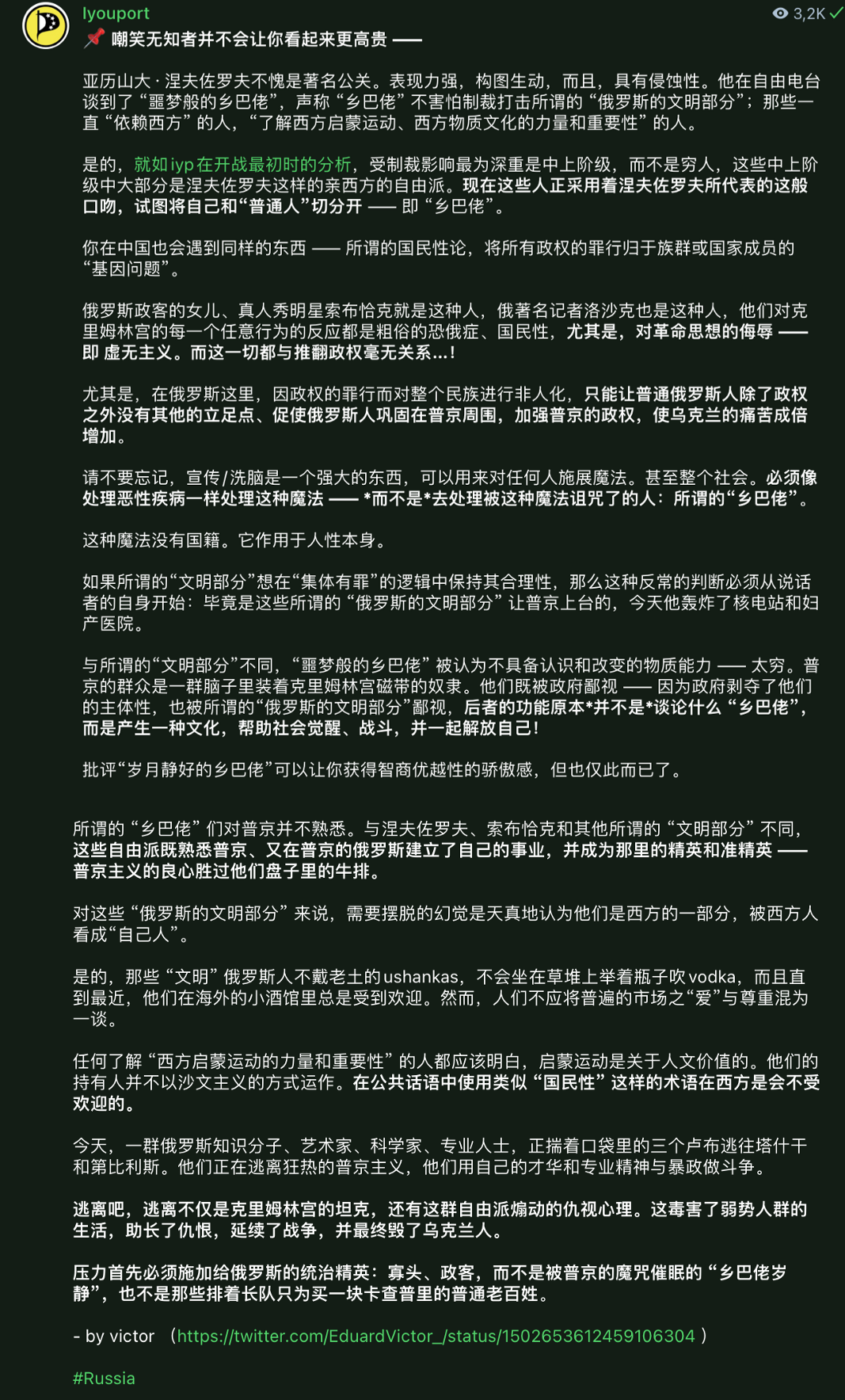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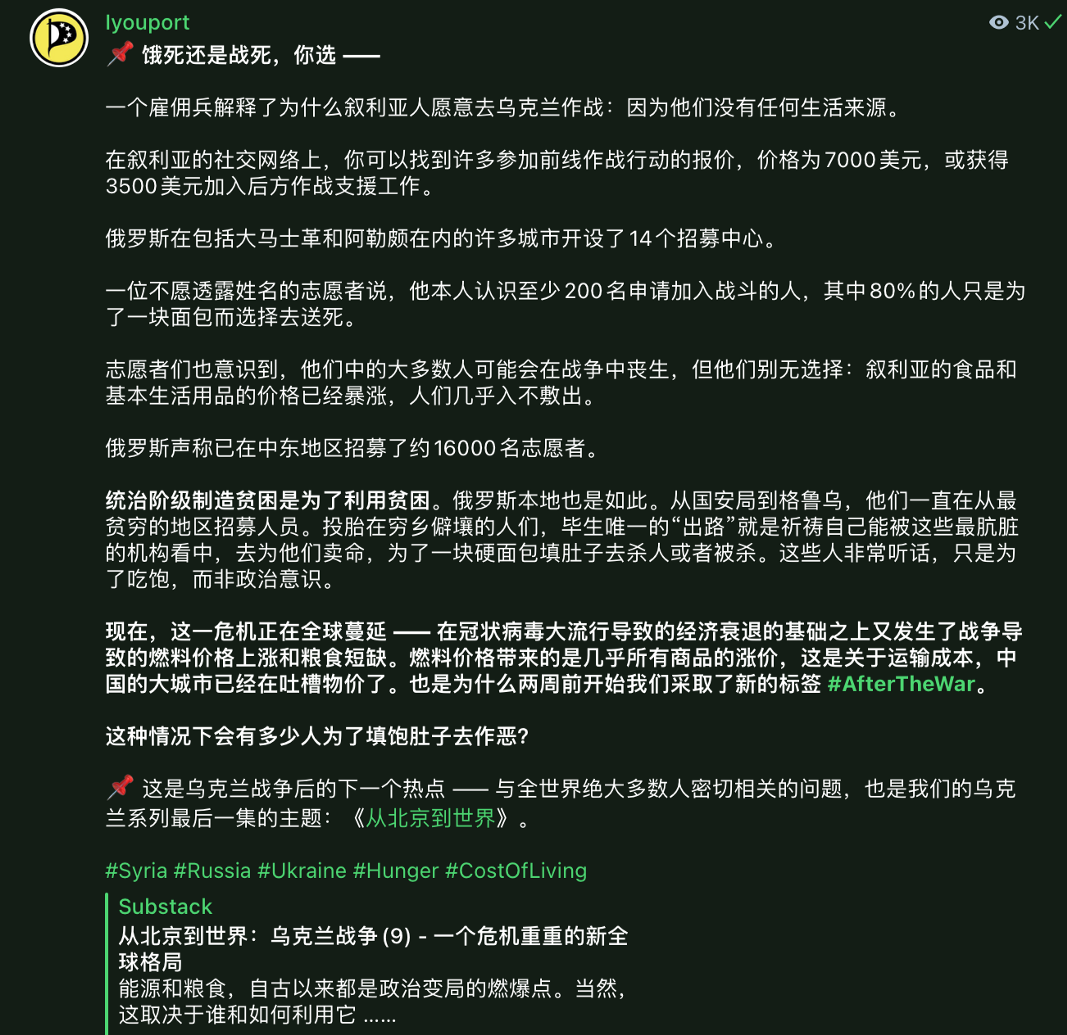

階級分析是我們在福羅斯暑期學校中出人意料地沒有出現的東西。我們討論了婦女歷史、性別社會學、後結構主義和女權主義理論,並閱讀了克羅地亞女權主義者斯拉文卡·德拉庫利奇等女性作家。然而,貧窮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經歷,卻從未被討論過。在我們國家發生的經濟轉型也沒有被討論。我們沒有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儘管我們都是新自由主義的前線受害者。
我當時的夢想是去西方旅行,比如住在巴黎或倫敦,參觀科隆和哥本哈根,米蘭和巴塞羅那。由於缺乏資金,這個夢想從來沒有實現過 — — 即使我有錢,我也沒有簽證,而當時我需要簽證才能去西方旅行。我的東歐同事都破產了。我們掙扎著用微薄的工資支付賬單,從慷慨的西方同事分享的複印件中閱讀後結構主義理論。就像窮人們經常做的那樣,我們開始迷戀神秘經濟所帶來的希望。朋友們會嘗試最離奇的計劃,突然有一段時間,有人會賺錢,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賺的,每個人都想知道。但是,大多數嘗試這些快速致富計劃的人最後只是變得更糟了,失去了他們的儲蓄,有時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家園。
在福羅斯暑期學校的最後一天,我們去了克里米亞最大的城市 — — 塞瓦斯托波爾。我走在通往海事博物館的陽光大道上,在城市的老城區,地上的黃葉宣告著秋天的到來:那條街道,和其破敗的外牆,就像很多地方一樣,從斯普利特到塔爾圖,從布拉格到聖彼得堡。在社會主義時期,它是過去的遺跡,我們並不關心— — 社會主義畢竟建造了現代的、舒適的公寓樓。社會主義垮台後,這樣的街道成了我們不可避免的貧窮的象徵;只要我們能修復它們,那麼我們就能與我們社會主義之前的榮耀重新聯繫起來,我們的城市就會像“西方” 一樣。但在那個下午,我看到了它們所懷念的、不完美的詩意。和我們一樣,它們是見證者。

事實證明,我回到羅馬尼亞後並沒有一個全職職位在等著我。到了10月,我已經適應了三份兼職工作:管理一個關於家庭暴力的項目,在大學兼職教學,以及翻譯。這樣做,我能夠拼湊出相當於150美元的薪水。 “美元” 並不是對西方讀者的事後翻譯;這確實就是我們當時對自己的收入的理解。經過幾年失控的通貨膨脹,政府將列伊的價值減少了一萬倍,使羅馬尼亞的貨幣非常不穩定,因而太難以理解,無法思考。
我的收入很一般,按照當時羅馬尼亞的標準,不算太差,儘管每份工作需要的時間比我最初想像的要多,除了工資之外,更像是一個全職崗位。我幾乎沒有時間睡覺。我記得我去超市買東西時感到很無助,因為我的一半工資都用來買酸奶、麵包、意大利面和蘋果了。到了月底,我不得不借錢生活,但我想,其他人也是如此。
而且,在當時,羅馬尼亞人的收入遠遠高於他們在東方的同事,無論是俄羅斯人還是烏克蘭人。我了解到,格魯吉亞人每月僅靠相當於15美元的收入生活,而且每天只有幾個小時的電力供應。
“你是說50美元嗎?” 我記得我這樣問道。
“不,15美元”,那個女人回答。
那一年是2000年。那時,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都已經結束十年了。關於任何改善的想像都毫無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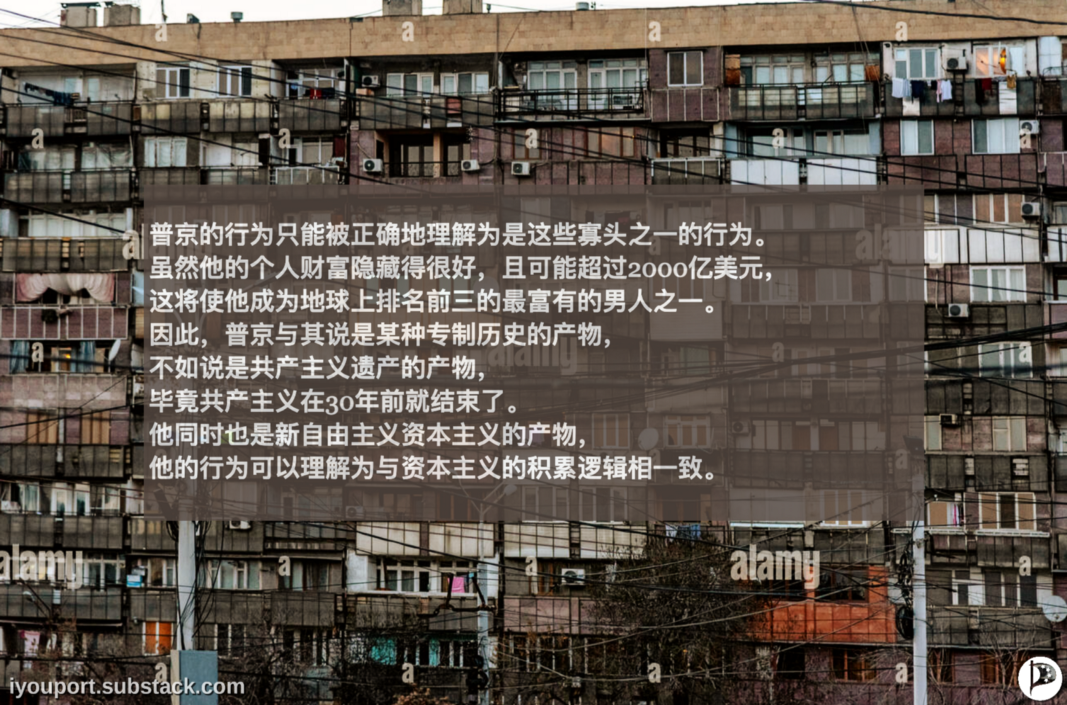
我開始向設有婦女研究博士項目的美國大學遞交申請。我對其他事情不感興趣。在我寄出四份厚厚的申請書的幾個月後,我的雅虎郵箱收到了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我已經被一個博士項目錄取為研究生,我將獲得為期四年的助教職位。消息的署名是一位美國教授,她對我以姐妹相稱。我想表示感謝,但我無法想像任何一種平等能夠克服我們之間的地位差異,無論是在行動自由、權力還是財富方面。
當時,我也還不了解東歐人對白人的不穩定控制,以及它如何讓我們陷入權力和缺乏權力的複雜的中間空間。現在,我意識到,如果不反思種族的作用,就根本無法理解烏克蘭的戰爭以及西方對它的反應。學者們為與白人相鄰的種族化類別創造了各種名稱,但也許理解東歐人所代表的種族悖論的最簡單方法是:理解我們是白人,但不是西方人。這種白色也許在作為反對羅姆人的大棒時最為明顯,羅姆人是烏克蘭的一個少數民族,在該地區有著漫長而痛苦的被剝削的歷史,包括五百年的奴隸制。
然而,非西方的地位顯示了我們在全世界的無力感。 “相對文明”、“相對歐洲”,查理·達加塔在CBS新聞上這樣說,這個非同尋常的聲明(雖然他已經為此道歉)向我們直截了當地展示了在西方人眼中的全球等級制度。一方面,“文明的” 和“歐洲的”,比來自全球其他地區的有色人種更“像我們”(西方人),例如,敘利亞難民危機,僅僅在幾年前就得到了非常不同的新聞報導;而另一方面,東歐國家被認為只是“相對” 文明,只是“相對” 歐洲,只有在與其他人— — 有色人種、其他宗教的人— — 進行的比較中,烏克蘭人才會被承認為可以被西方接受,然後它就會處於某種服從的地位。
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總統說,烏克蘭正在為成為“歐洲的平等成員” 而奮鬥,這相當不可能實現,即使烏克蘭在歐盟的成員資格奇蹟般地被快速推進。從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來看,即使加入歐盟也不一定會帶來繁榮,大多數東歐國家都經歷了連續的移民潮。東歐家庭有成員生活在三個或四個不同國家的情況相當普遍,這是對社會主義結束後開始的社區聯繫的進一步解體。只有極少數波蘭和羅馬尼亞公民從歐盟中獲得了經濟利益;而許多人仍然很貧困。在國外工作的能力可能減輕了貧困的最壞影響,但它卻導致了人才流失,因為東歐國家的醫生和護士正在流失到西方國家,而西方國家並沒有對他們的教育進行投資。在歐盟,東歐工人仍然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二等或三等公民,儘管他們對當地經濟是很必要的。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羅馬尼亞的農業工被空運到德國,在不衛生、不安全的條件下在農場工作。
因此,這場戰爭的答案並不是回到不加批判地使用“自由世界” 這樣的表述。正如普京不僅是後社會主義的產物,並且主要是貪婪的新自由主義的產物一樣,烏克蘭不僅是一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它也是全球移民線路的一部分。逃離該國的難民中不僅有烏克蘭人和羅姆人,還有印度學生和各種背景的烏克蘭黑人。 “東方”與“西方”的舊框架沒有考慮到種族化的經驗,也沒有考慮到一部分烏克蘭人可以希望獲得的白人特權的程度,而其他烏克蘭人卻不能。然而,只有考慮到種族,考慮到種族化語言對經驗和痛苦的排序方式,以及駁斥那種衡量誰“值得同情” 的標準(特別是通過衡量他們與白人的接近程度的那類標準),我們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一個不分膚色和無所謂原籍國的任何人都可以體驗的民主。

2月27日星期日,擁有三十八所大學並具有前瞻性的性別研究中心的哈爾科夫,遭到了俄羅斯人的火箭炮攻擊。平民不是職業軍隊的對手。
我開始寫這篇文章時,只是希望戰爭消失,擔心烏克蘭可能成為美國人在本世紀無休止戰爭的下一個實例。導彈摧毀了公寓樓,拆毀了基礎設施,平民在爆炸的混凝土碎片中尋找自己之前的生活遺跡— — 這些圖像令人心碎地熟悉。戰爭已經在破壞烏克蘭城市的生活環境。留在哈爾科夫的平民認為自己很幸運,如果他們住在靠近雜貨店的地方,可以冒險出去買點東西。站在美國的安全地帶,我唯一能問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的軍事幫助還沒有在前往烏克蘭的路上?
而後社會主義空間的區域團結正在再次出現。 Pussy Riot 最近在推特上發布了一段哈爾科夫被炸毀的研究中心的視頻,回憶起性別研究中心是他們第一次閱讀女權主義書籍的地方。烏克蘭難民正在摩爾多瓦、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找到庇護所,前兩個國家與烏克蘭的邊界最長,被認為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他們的努力是必要的,而英國、西歐國家和美國等較富裕的國家仍在等待決定他們是否會做出貢獻以及做出哪些貢獻。
有報導稱,在邊境地區發生了種族主義事件。戰爭和災難放大了已經存在的等級制度和脆弱性;LGBTQ難民的生命受到了多重威脅。不幸的是,很多在後社會主義框架下運作的東歐籍主流知識分子迴避了對西方國家的任何批判,但是東歐新一代的學者和活動家,多元文化支持者和女權主義者,已經準備好了接受一種反種族主義的政治,這種政治是全球性的,它以最弱勢的人的需求為中心,相互交叉。有色人種的記者已經表明,將種族類別放在分析的最前沿,對於理解該地區至關重要。
從東歐的二等公民身份、非西方白種人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下的貧困的歷史經驗中,應該出現一種新的團結形式,一種與各地的貧困人民和有色人種相聯繫的團結形式,從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與其要求只能暫時和部分授予的“白人”或“文明”,無論這意味著什麼,從邊緣,我們完全可以要求結束世界各地的寡頭統治,結束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為所有人帶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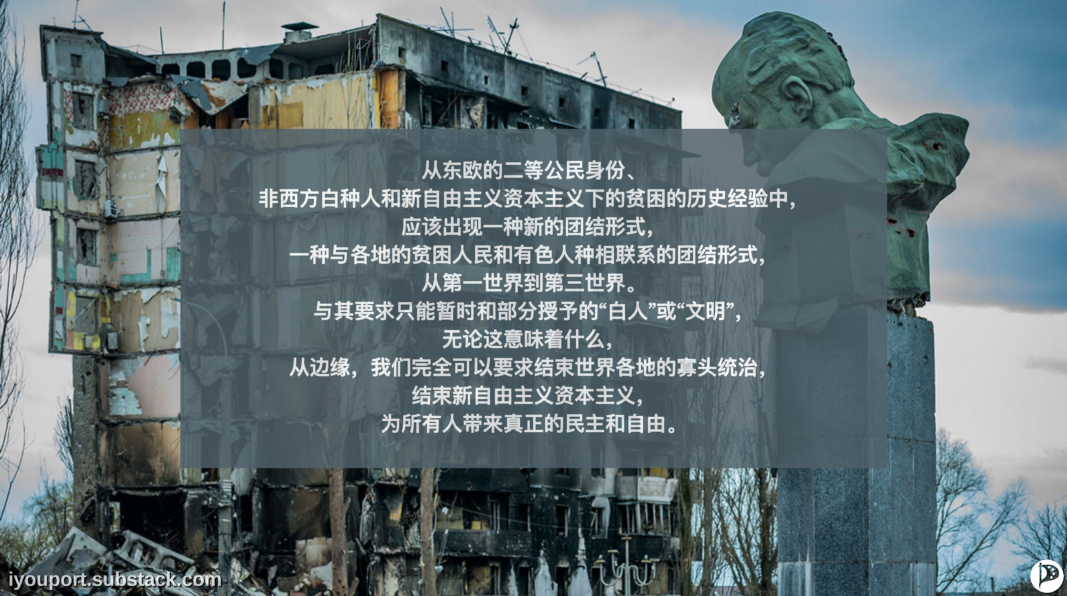
Ukraine: Beyond the Postsoviet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