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刺激.碎片中的城市男女——近年来城市电影当中青春叙事表达的变化
提纲:本文想透过近年来都市爱情为题材两岸三地的电影来分析其中的性别形象表现,又以台湾与中国大陆社会的性别表现以及对性别认识的变化所带出的议题为主要分析对象。主流电影里聚焦在都市空间的性别关系如何建构消费社会的爱情神话?如何将性别形象予以类型化的设置并构筑爱情神话?并且站在科技媒介发展的进步观念上,将科技的发展作为电影情节的人物关系的联系,展现的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发展出更细致的性别关系的选择,如何对性别气质的变化产生作用?相较于主流电影市场表现的爱情神话和艺术电影节参展片,性别身分的显影如何对现实中城乡发展的矛盾有效弥合其所伴随的性别分化的矛盾? 艺术电影节参展片又如何揭示爱情神话的失效,并与主流电影市场形成对城市中的性别表达的多层次的张力关系?
关键字:城市想像、性别气质、社群关系
前言
以白领工薪阶层为青春主体的主流商业电影从《失恋三十三天》(2011)、《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会撒娇的女人真好命》(2014)、《滚蛋吧!肿瘤君》(2015)、《七月与安生》(2016)、《后来的我们》(2018),延续着《致青春》当中的叙事方向,不同于80后们在城市求学、创业,跻身大型企业成为成功人士哀悼青春的叙事脉络。在《七月与安生》(2016)中则表现为留在城镇的七月与从城镇出走的孤儿安生,二人所遭遇到的爱情,爱情作为电影牵引的线索,表现二人面对城市发展趋于成熟后个体在城镇与北漂者在城市里逐渐安定的过程,两个因不同选择走向不同方向的女性则为彼此性格上和生命上互补的关系,爱情与友情的黏着性叙事弥合了城市发展造成人际之间离别裂隙。
本文希望透过分析近年来两岸三地合拍片表现的“青春”与“性别”内涵诠释发生的变化,并透过分析对青春、性别不同的诠释来反映当下的社会状况。
一、 城市青年的爱情叙事
以上提及电影表现城市女性拥有更多的主动性的追求,对生命力量的肯定,同时对生命力量的肯定奠基在当代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之上,是城市空间的消费方式变得更为便利。女性角色在城市的生活里藉由物质的消费来展示都市消费的场景。女性受众是否透过青春片的观影经验获得主体性?女性角色在什么意义上是富有主体性的?以城市题材为背景的青春片这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是包含着一个或多个时尚走秀的场景,时尚走秀又来自于对城市面向国际的自我推销,将女性形象等同于城市国际形象包装。也可以说这一种女性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实际上有一个都市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背景,但实际在青春片背后被表现为女性在城市的职场,面对总总困难并且完成各种任务后,在其间阴错阳差的遇见心仪对象,最终幸运的恋爱,走向婚姻的道路。
或许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故事情节事实上可以置换成男性角色带入,不过会使用的不会是鼓励女性独立自主而仍是强调推销不同性别受众消费的时尚,在当下以城市为背景的青春片当中的男性形象的呈现也未比以“英雄”作为出场或建立一阳刚男性的主体。在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男性所处的位置却也时常被表现为于现代化城市里办公室或是封闭空间里,不具备武侠片或是抗日电影或是武打动作片当中强调习武之人男子汉单一阳刚气质的男性形象,在办公室场景将男性更赋予阴柔气质的形象。
在恋爱关系的塑造上,仍是以男性主动,或将其关系颠倒来强调女性更富有在情感的主动性,强调制造恋爱浪漫的气息,以及制造恋爱的氛围,但不涉及任何具体的“生活”的讨论,在情节设置上更关乎“生活”则仍是选择个人奋斗的路径,或是抛弃前项选择而倾向走向二人“在一起”的圆满结局。二选一的情节设置却又全然是为制造浪漫氛围与哀悼青春的伪命题。电影首先只是制造了关于生活、以及浪漫青春想像的爱情氛围来推动故事向前进展,但全然没有关于当下生活的内容与状况进行讨论(或说这已经形成电影提供的场景空间以及角色们所处的当下无须讨论的前提),而是对“梦想”的未来的讨论。
如若选择了前者,则成为了今日在电影叙事里,可以看到在对八O后创业奋斗贯穿的青春叙事的哀悼。而在电影也展现了白领职工的生活空间场景片段,生活的消费型态(办公室、度假旅游),又虽然强调个人的移动但是仍是关于同一阶层的移动或什至上升,仍是建构在受到大学教育毕业后,留在城市获得工作对于城市的情境来发展电影的叙事。
大多数的青春片与强调同侪竞争、各自恋爱的关系《小时代》(2013)、《致青春》(2014),相对于赵薇导演、李樯编剧《致青春》则讲述了对于不同离乡背井不同家庭状况的学生,就学到毕业并且在城市成长并经历创伤(在建立自我价值的同时,是完全强调其作为职工在职场的工作专业性而非其他)的故事。由郭敬明小说改编、并由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以经融之都的上海作为背景,表现大学同侪之间的同居关系,呈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女学生逐步进入社会的状况。但在表现同侪竞争的同时却又削弱了阶层之间的鸿沟,从而选择性的不具体化阶层之间造成的矛盾。到了《七月与安生》、《后来的我们》则因互联网科技带来的便利,居于都市空间而形成更为单薄更孤独如蝼蚁般的个人,孤独的状况不只是作为在现实空间呈现的阶层固化和到城市打拼的难处,更是将个人奋斗的精神“上线”到互联网之后,相当于截断了对现实探究的可能,甚至仍无可弥补作为“外省青年”来到城市所面对现实空间的疏离感受。
以外省青年移动为主要叙事背景,不同于整家迁移到异地的状况,电影也并非表现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儿女到异地城市发展的感伤气质。青年人离开城镇到城市的北漂的命运便得更不确定,“梦想”也不同于以往所呈现的青春片里面所期待的成功学书写,反而呈现个人在公司的奋斗要获得职位的晋升与成功在所处社会环境变得更为艰难。男性在大城市生存所面临的挑战呈现的犹疑与怯弱,在女性身上则成为为对生命的确信与无所畏惧。表现了在独生子女世代,青年男性不仅紧要便对来自社会家庭的责任与压力之外,在移动与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当下以市场竞争为前提在以新儒家为标榜的当代华人社会,对工作能力的淘选,要实践并建立自我价值承受了高度的社会期待与自我压力,并且这种犹疑与怯弱是不为打破对秩序的绝对臣服。
在这几部电影叙事的表达中的共性是,最终性命凋陨的是单支形影的女性,女性生命的凋陨、死亡不完全是作为两性爱情哀悼,或是青春消逝的一部分,更指涉了当下城市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城市生活人与人的关系解离,女性所联系的孕育生命、连接同性与异性的情感不复存在,正因为难以存在或不复存在,才予以回忆的形式展开。藉由记忆片段的重组固定不复存在的联系。
甚至在刘若英编导的《后来的我们》(2017)中,女主角巧巧(周冬雨饰)甚至不再具有同性的友谊,从在城镇生长到城市里生活,相对于见清(井柏然饰)所拥有的家庭,以及电影里设置的人物性格作为家庭中独身子所背负到家庭中的期望与社会上对“成功”定义的压力,在城乡、城镇之间,巧巧更像是孤儿的化身,呈现女性从城镇到城市生活的各种保障仍处弱势,尽管生活的流动性是作为电影的喜剧性的情节呈现,作为青春片电影当中多次表明,男女主角的性别气质状态已变得趋同,在男女主角身上都在中国城市消费社会、科技社会的崛起,内部的高压规训导致角色趋于阴柔,并且阴柔与阳刚兼具的气质,但是二人所面对到的事实上是不完全同等的社会就业条件。
电影讲述了二三县城市出来的青梅竹马的青年来到城市求学毕业后,留在城市打拼,遇见彼此之间的爱情,然后又因为总总原因错失彼此的故事。其特色在于将电影角色的主体聚焦在互联网、科技公司上班的上班族离乡背井来到城市发展为主要聚焦群体,从而呈现了在北京中关村的“电子商场”的现实空间,不同于对于青春电影描述当中将角色安置在适合于青春主体所在的消费空间的场景(好比:溜冰场、大排档、购物中心… …等等)。青年角色出现在电子商场的时刻,并非作为消费主体的身分,不同原先第二产业工人的劳动身分,展现青春主体所处的劳动空间。联系着青春主体必须面对走向未来的道路时,学生同时间有打工身分的工作准备,流动的临时工作中、巩固的友谊也是在近年来多数的青春类型片当中,人物关系的友谊则更像是将不同类型人物牵引到同一个故事场景中间的元素,强调的还是每一个角色在城市中以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在城市独自拼搏,并且最终获得成功的事业与爱情的结局。
从农村、城镇来到城市求学生活打工打拼的青年主体在青春电影,呈现相对于消费空间而更贴近写实社会场景做为过场,《后来的我们》当中以不再拥有紧密同侪关系的青年奋斗为主题,表现了北漂青年来到城市后各自拼搏,并且在一现代科技化的城市空间当中,爱情的情愫与怀念是为“青春的悼念”,“青春的悼念”则是对于个人来到城市打拼奋斗的自我价值的一次否定,这一自我价值的否定来自于青年主体遭遇到与原故乡里自我期望完全不同的空间状态,并且经历了城市空间的辗压后,成为城市运作当中的一分子。原先所希冀的成功圆满的人生,对来到城市念书工作获得个人的自由的观念而言,前者相较之下则成为了一种没有目标的念想,这一念想也在成长的过程中转变对于“大步向前”打上问号。也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中,既不具备绽放的青春,也未曾抵达过完满的爱情,仅仅剩下的是落单于互联网之中,又透过互联网联系的失落在资讯之海的个体。
反映社会问题的艺术电影《醉生梦死》(2015)、《路过未来》(2018)表现城市底层为主要群体的青春叙事,在此之处,“青春”不同于前者所讨论的,仅仅只能透过单一的个人奋斗获取成功的叙事,或是北漂到城市里回首发觉遭遇到凋零的青春与错失的爱情。
李睿珺编剧导演的《路过未来》(2017)里,以父权为主导正在进行高度资本开发的南方城市里,电晶面板工厂的移民女工成为主要的工作群体,女性的青春不再成为某种可能获得上升空间,青春并非社会中层以上的青年群体的浪漫爱情叙事,或在满足物质生活之后可供哀悼的情感。 “青春”则成为奠基了城市发展,然而牺牲了青春与身体,并且青年面临城市房价高涨,不可能购房并且无法回到农村的社会困境。在城乡之间的迁移与往返,电影里反过来打破了既定对于男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印象,则呈现了底层女性所面临的严苛条件,电影里包含了两次女性的死亡,第一次的死亡是女工身体在面对消费社会下的审美标准,试图获得社会认可与自我认可而死于手术失败,而另一次则是在为筹钱买房落脚于城市试药兼职,导致肝硬化末期死在往内陆回家的归途列车。
《路过未来》当中表现的“青春”的内涵是:不可能获得对爱情可能性的意义,不同于在《后来的我们》里面,将在青春成长里错失爱情的遗憾仍上传到云端并作为程式工程设计中游戏的一部分存留在生活之中,在《路过未来》的女工身上,现实生活的无尘工厂里既不包含可供仰望的青春或爱情,只拥有最简单、虚拟化的若有似无地偶然存在的谈话,以表示自身存在,存在世界有“人”关切彼此,女工所牺牲的青春、爱情表现在城市空间难以获得精神的寄托,电影后半段,所展现的女工的处境与城市的流氓无产者所构成的情感关系时,在结尾给出了二人从虚拟化的网路关系到坐落到生活的现实时,才暂时有建立彼此之间的共识的可能性,然而这一从虚拟到现实的相遇,电影在画面当中以无声的字幕来表现当下年轻人更普遍习惯的沟通方式,似乎成为了整部电影里女主角耀婷唯一发出的“声音”,以文字代替声音,在电影里基本上没有女工的“发声”,作为最长者的“红姊”(娜仁花饰)至始至终除了在面对到工作机会时提出要求一些简单的兼职工作之外,但大多数的场景却成为了“哑巴”般无声的状态,这一种沉默在工厂生活里是为工作专业的标准,一种“友好”的表现,但事实上这一种“友好”则表现为在无声的电子版面工厂的生活事实上是“噤声”的状态,在多数时刻人物在画面当中却又是隐身的状态,在现实中在脖子上刺有蜘蛛纹身的男子新民(尹昉饰)在网上匿名为“沙漠之舟”与女工耀婷的虚拟身分“雾中风景”在通讯软体里相遇,埋线伏笔到最后,作为现实相遇的俩人,却无法挽回女主角在回乡的列车上面临死亡的命运。
不同于主流商业电影里强调在经济迅速发展扩张的大都市,居于消费社会的城市中产阶层以上透过消费享用来获得城市的“新感觉”,或在今日要寻求一种透过科技技术来达成的超感觉,宣传凌驾于个人与集体之上代表对世界全知的感知能力,当将个体自我的精神上线(上传)的同时,实际上却是对生活环境的一种毫无感觉的感知状态。
丧失感觉、麻痹感觉、丧失感觉来自于环境和个人的身体感觉的剥离,个人的精神与现实生活感受的剥离,城市现实的生存环境成为了对个人的压抑,而作为无法在现实的流动性的状态里获得安放个人的居所,在《路过未来》当中,工人和打工者是奠基都市的未来的建构者蓝图的一部份,但在当下的状况却是在围绕着科技技术的厂房、医院和空间分配不足的狭窄工人宿舍当中只有关于一指令一动作的军事化的工作情境,群体内部的互动关系的声音却在电影当中有意的降到最低,主角只能透过文字代替声音,是以一种拜物教的形式使其精神逃逸到手机的通讯交友软体之中,传达出来微弱的日常聊天的文字实际上是精神的扁平化,但却又是对于如同沙漠般的生活状态的呼救声。
在《路过未来》当中,现实里有蜘蛛刺青的新民和耀婷作为网友的“沙漠之舟”和“雾中风景”相认之时,并不是作为一种浪漫的氛围,甚至在耀婷得知自记肝硬化已经到需要动手术时,选择到KTV唱歌,并且出于一种绝望而非喜悦的情状,与红姊、新民在梦幻的KTV包厢里唱歌场景不同于在以往在青春片里将唱歌的KTV场所作为表达爱情、浪漫、欲望张力象征暧昧不明、五光十射的现代城市,是比来到城市早已无梦,虚拟世界原有的精神依托也从来虚妄。
二、 性别气质的变化
在2003年《绿茶》当中赵薇饰演的大龄女研究生白天不断在相亲的茶水桌上,通过谈话来选择合适的交往对象,到了夜晚则成为在都市夜生活穿梭的精灵来代指后现代北京城市的两种面貌,其中作为观看客体的女人的二分形象,被动/主动、不可欲望的/可供欲望、清秀/浓艳予以模糊化的表现成为整部电影往下推进的情节,投射着在城市发展的过程里捉摸不定没有方向性的欲望。到2008年《女人不坏》当中多种类型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在城市中以及彼此之间互动关系。一系列的以题材的青春电影里表现白领办公室的爱情以男性对女性自主性的认可,同时表现了当代的工作伦理赋予男女的性别平等的观念,但同时这种男性对女性的自主性的认可,同时是基于对爱情叙事的铺垫,所以构成在情感上的认可。所以角色拥有的自主性,以当代社会的女性自主独立的性格为支撑,这一种自主独立是将女性作为一富有时尚的城市气质的符号商品其存在才得以成立。
2011年滕华涛导演的《失恋33天》除了指出青年在城市面临的婚姻焦虑以外,却反转了以往大众对爱情想像的设置,对于爱情关系不再必须是充满阳刚气质男性对应着的包含“三从四德”、娇美的女性形象,电影里则凸显以“女子汉”成为了职场女性的气质特点,搭配对公司企业适应既有决断的执行力但又不同于“阳刚气质”心思细腻的男性同时认可女性自主性,从同事发展成了恋人的关系。 在《失恋33天》当中,更展现办公室白领女性如何面对情感关系发生变化,在婚礼包办公司的职场职工也面临着婚恋高度的压力。
不只是女性并且男性在当代都市当中的爱情关系的个人的情感关系的失控,在办公室空间受到一定的压抑,并且获得“爱情”的方式只能从谋略与计谋还有一系列的安排与计画当中获得婚姻,而“爱情”的失去与获得沦为电影推动剧情并展示一系列的安排与计画获得“婚姻”的一部分。
《失恋33天》里表现对感情的安置,透过失恋而获得感情的成长。在电影最后画外音女主角的内心独白,将情感关系中形成的变动仍旧归咎于个人人格上不够“完美”的缺失,这种“不够完美”在职场和人际的逆境当中奋力要长成更完美的人的追求,事实上仍是在商业类型电影要打造白领女性在生活职场中工作伦理的范畴。关于个人情感的困境有多少程度上在社会的公共空间备受允许表达,以女主角黄小仙(白百何饰)个人独白的形式的呈现,给与观众对的感情成长主题的正面观感,但对于女主角作为女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旧没有给予相应的回应(因为后面她获得了对于过去经验的反省之后获得了另一段感情并且嫁人了… …)现代社会普遍发生在人情感上的痛苦和挫折在一个社会、企业有多大的包容度?电影聚焦在这一白领女性的失验经验的刻划上也揭示在职场的女性所情感经验的纤细与脆弱性质,职场男性所面对的情感的态度却成为一种完全符合社会规则运作的选择与程式,相应之下更表现出在职场的空间、当代中国社会对于职场上个人情感发生“失误”的低包容度,甚至男性角色的情感表达只能从计谋、谋略与对程式的应对自如中以专业能力呈现其自信,摄影镜头聚焦女性情感经验的受挫透过男性长者与同事的引导来获得治愈,反过来想是否也只是展示了一种男性对于婚恋的程式的运筹帷幄?失恋的超出“正常”情感规范的女主角则在人生这一时段成了职场上错误百出的失败者?又无不揭示了构成当代中国父权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空间作为着整部电影的叙事前提,对于职场所面临的个人情感关系的失败只会造成工作的失败,这种工作上的失误与情感的失败又归咎于人格缺陷,在此对于爱情或是女主角独白的个人自省都只是构成对于当下办公室文化与城市男女情感关系疏离造成的问题予以回避的处理方式。
同样以喜剧形式呈现城市婚恋议题的电影,一方面以聚焦女性如何在职场转化个人的失恋问题,但在商业电影当中却不涉及职场当中不同角色所具有的政治主体性,而更多的在打造主流意识形态下所赋予的工作角色与性别角色位置,所以在电影当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状态的变化塑造仍多是可以预期的爱情喜剧。从2011年的《失恋33天》甚至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城市发展所处的经济上升期的位置,所以以男主角将城市广告看板的夜间亮灯做为对女主角的浪漫长情告白。
主流商业电影当中试图打造出对以女性为聚焦的青春片的同时,在近年来参展艺术片当中也可以看到倾向以城镇少女的成长为主题的《少女哪吒》(2015)、《黑处有什么》(2016),二者皆把电影时空场景设定在九O年代的二三县城市,不同于主流商业电影表现职场女性在都会里面对到的生存与情感问题,少女作为“未成长完全”、“未达心智成熟阶段”的阶段,在电影当中所建构的空间当中成为电影建构出城镇、二三线及城市所压抑的符号对象。
王一淳编剧、导演的《黑处有什么》(2015)不同于第六代导演电影表现90年代的县城因体制改革导致原有军工体制发生的变化,沿海城市作为经济发展需要而使得多数人下海到沿海城市去打工,表现当时青年对于中心城市与港台流行文化的向往,移动到城市所面临的震惊状况,面临城市失速发展,求取狭缝之间生存的可能。近期的导演重塑关于90年代的记忆,已经不再是对于城市发展的批判与城乡矛盾失衡的揭露,更聚焦于关注二三线城市父母一代以在公家单位工作的小镇青年的成长经验,在《少女哪吒》或《黑处有什么》表现的城镇不是电影在批评面对城乡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导致农村城镇的贫富分化以及人口流动的问题。在近期的青年导演里表现二三线城市的空间的聚焦人物是随军工体系或部队长大的小镇青年,城镇则是一相对静止密闭并且没有外部的社区空间。这种完全封闭的社区空间再现对于90年代记忆的重塑,并非表现当下性的问题,而更接近要追问父辈对于九O年代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城镇青年在成长期间所经验到封闭社区内部的变化,电影一方面给予了模糊化的视角,以至于很难看清体制运作的状态,相对于青年的父辈则熟捻于政治游戏的运作,青春所代表的则是对于体制的“懵懂”、“无知”,并且除了逃离行政体系与公权力的良性运作早已坍塌的城镇、一直迟迟停滞发展的内陆城市之外,别无选择。
《黑处有什么》开头即以“猪头”、“活鸡新杀”的招牌不无嘲讽意味的在暗示,九O年代所面对到体制另一次的变革造成的体制变化。体制的空转与死亡对于活在体制底下的人而言都成为事不关己的闲谈,而事不关己成为整部电影里的市民态度,但同时又是高度紧张的监视与检查的高压状态。体制的死亡从城镇里发生的奸尸案展开,电影在大量的镜头里面呈现曲竫(苏晓彤饰)的父亲(郭笑饰)同时做为公安局的医检官但在执行奸尸案的任务,以相机记录作案现场的时候,摄影机给与父亲的镜头,则将父亲构造为一个窥淫并且有恋尸倾向的父亲。警局、社区发廊对奸尸案有共识的表演着无知的认识,并且作假案卸责给当地的流氓,面对体制的颓败,父辈非但不是作为承担者的角色,反而成为说风凉话继续扮演着遵循法与规定的角色游戏扮演,并且对动物、死尸在电影里做为某种社会表征的状态的观看表示冷嘲热讽的态度,再次呈现了“严法”然而却全然的失度与失效的“法” 。导演在对于父辈以及上一代面对体制的模样以戏谑的手法来呈现的同时,把少女作为一面涉世未深的镜子来对比父辈看待社会的态度,学校里的教导主任、知识份子成为了苟且偷生照本宣科的角色,不同于对于校园青春电影里面表现的校园和乐的状态。在父亲的规训与教导之下,女儿于变成了尸体般的存在,相对于父亲镜头里的女儿,消失了的同学在曲靖的梦里构造了她同被奸杀的猜想,而背后监视的狗牙的眼似乎是带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怨恨而存在并跟踪着,甚至所有关于性或性启蒙的知识可能都是在一间破败的录影厅完成,电影中再次出现的录影厅对港片的播放是再次复制父亲的眼睛,女主角在录影厅的哭泣则是她从而得知她所有的欲望都是被强迫/强暴赋予欲望的意义。电影当中呈现了封闭形式剧场感以呈现对熟人社会中运行的潜规则的批评,但所谓的“体制”却又是一个早已颓败而“各种都不行了”的体制,同时呈现“青春”气质的少女全然受到压抑,与家庭、父亲捆绑再一起,并且“青春”意味着在没有动静停滞读时间里窒息为一团肉块。
这两部艺术电影不同于第五代或第六代电影人对城镇或农村的电影表述,知识青年下乡面对到的农村状况试图改变农村状况,并见证农村的凋敝,又或是从城镇出生,在青春期成长时期面临的个人身心及同侪之间与大环境剧烈的激荡,选择留在时间停滞的城镇。电影中所展现九O年代初期城镇的政治真空状态的“青春”也不同于前者所呈现过早成熟并且快速萎谢的青春,而在《少女哪吒》(2015)、《黑处有什么》表现的“青春”始终是一个发育不全,甚至幼稚的青春主体。同时两部电影都试图对于女性的政治主体性进行提问,但是以个体所呈现的“幼稚的青春主体性”,以女性为聚焦的政治主体性,却伴随压抑的青春流逝早早夭折。 “青春”所具备的意涵是青年敢于突破社会上过于陈旧、滞涸的规定,并且创造新的生活可能性。在情节推展当中,青春的夭折也意味着突破桎梏获得自主的政治主体性过程面临失败的局面,女性做为电影形象来呈现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表征,时常是商业类型电影里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主体的欲望投射对象,相对于“机制的运作”一直以来多象征以男性为主体的权力的上位,女性形象所指向的则常是代表民众居于体制内的弱势位置。在两部青春电影大幅呈现的“始终没有成熟的女性政治主体性”,始终没有发育成熟及衰老或是夭折的青春,同时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面对九O年代社会改革至今以文化侧面给出的一项警语。
三、 透过媒介所反映的青年与家庭关系
以上讨论的电影当中,呈现中国当代社会内部人际与科技的伦理关系当中产生的性别变化之外,同样在台湾电影《醉生梦死》表现2014年以后台湾政治困局造成的青年贫穷的困局(蝼蚁、老鼠、猪头来作为对底层青年的指称),电影的背景前可以看出,当代台湾透过网路来传达与发声的议题趋向多元化,尽管多元观念的出现,台北为发展多元文化社会议题,导演对青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再现却更加凸显失业青年、流动性工作青年的孤独感。使用新科技的弱势群体,并非在现实空间获得更多人际拓展的空间,而更近似于将工作与生命绑缚于新科技之中,新科技在电影里的运用呈现的性别关系是失去声音的青年女性与一直晃荡没有目标的男性无言以对彼此的关系,但这一无言以对的状况并非不正视彼此,而是电影呈现作为台湾的城市中心的由台北城市幅散的肃穆秩序,以及台北的经济凋敝给予青年人的生存压抑感受。
当中呈现的底层女性则相对于表现男性对欲望的奢求,不同于酒醉的昏沉的男性状况,女性在城市里更任命的留在所属的工作岗位维持社会的运作,但女性面对的青春,是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边缘实际上已满目疮痍充满欺罔的青春,面对在城市边缘构成的爱情,也是作为这座城市发展中冗余的谎言,所以在刺杀依附于这座城市如老鼠般苟活的男朋友时,更接近是对于在这座窒息并且奄奄一息却仍坚持有某种生命力的城市,实际上行使的是对自我青春的扼杀。
对于多元化的新兴观念反成为现实生活里母子或男女的冲突,并且是无法展开对话,无从对话的关系状态。从美国失魂落魄归来的大儿子,不断向母亲咆哮,指出自己离开台湾源自于母亲的压力,酗酒的母亲在面对儿子的咆哮时却完全失去发声的能力掩面痛哭,原有歌唱、戏曲背景富有生命力的母亲,竟已经无法歌唱并且因酗酒而在爬上架,摸索橱柜取酒继续麻痹自我时,失去意识跌落在仓房里丧命,在《醉生梦死》当中,直到发现那个身上曾有乡土、但同时有批判力以及曾经单独持家,并拥有威严的母亲已经生蛆腐烂在仓房里。在2014年后政治上强调的多元文化政治与底层社会状况的脱节,其青年世代所呈现的对于多元文化与多元政治的认同,与母亲所认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完全无法沟通,最后,长期因孤寂酒醉的母亲则倒在了阁楼当中腐烂死去,儿子对着新店溪前祭上手边的绍兴酒时,指向了对于晃荡游走在城市之间的台北失业的、以最低临时工薪为主的底层青年在近些年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中对于社会改变的茫然感受。
《醉生梦死》之中聚焦底层(或可以说是衰落的台北边城)对生活讨论与改变的可能性的困境,电影场景选址的宝藏岩空间与主流媒体广告宣传当中所描绘的台北印象不同,并非国际现代发达、高楼大厦、光鲜亮丽的楼宇形象,紧挨山边面对新店溪如层层堆叠迷宫的低矮楼群,是作为表现底层青年家庭状况与其关系的同时,做为城市的台北所处的贫富分化状况,并且电影的指向的是新科技并未疏通与或得到更有效的如当下媒体所宣导的民主的效果。
同样在《大佛普拉斯》(2017)的电影对科技使用的再现也有着相似的倾向,场景拉到台湾的中南部城市,主题表现的则为城乡发展不均与地方政治贪腐的问题,以及在城镇与农村的无业者与无产者藉由行车纪录器对权力的窥看,底层对于地方桩脚是力的欲望的渴望同时反映了普遍在农村流浪的农村无产者全然无能为力的状况。 《大佛普拉斯》与同年上映的《血观音》(2017)两部电影虽然在呈现的调性与风格上不同,但两部电影在不同层面上都表现对台湾近三十年来的政治恶斗的批评的意向。
杨雅喆导演《血观音》不同于《大佛普拉斯》表现底层男性的弱势的状况,也不同于近年来的青春类型电影当中定型化的女性形象,也并非单纯作为青春类型片所打造的女性成长故事。 《血观音》里则将女性角色塑造为台湾城市所代表同时具有商业买办与政治影响力的仲介身分,凸显女性在台湾政党政治运作与政商勾结当中具有强而有力的处事策略,有着不同于以强调的家父兄长来主持家政独当一面的暧昧形象。这一表现的前提是以过往在台湾作为父亲、父权为代表的政治秩序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效力,转而由女性做为政商强力的形象代言人。在呈现女性的“女力”的同时,在表现上层社会的家庭内部当中的女性关系,也否定了女性身分之间单一正面的互相扶持的“姊妹情谊”叙事。女性互相的依赖与依靠,更接近为联系着家用网路在生活中对物质的依赖性,无父的权贵家庭被围困在一个紧密交织的政治与商业网络之中,除了照规矩办事(或照潜规则的贿赂,电影《血观音》影片的命名及指着是政治饭局当中以一尊佛像当作送礼,但实际上是作为接下来政商争地建设一连串杀戮的警告)之外,没有从此局中脱逃的可能。
《血观音》当中虽凸显台湾的权贵家族中的女性作为“女力”的政治性,以及在这一系列的争夺当中人性的挣扎面向,但对其所呈现的更近于揭示:尽管在政治口号上强调台湾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但实际上台湾作为多方势力接管所造成内部政治恶斗的状况。电影当中所展现的“政治性”也并非良性的互动关系,是政商角力中的互相利诱与需要,以及在上层权贵的游戏规则之中,牺牲在地的弱势者与居民,彼此相残的过程。
两部电影当中对通讯媒介的再现的表现上,如果说《大佛普拉斯》,对媒介使用的再现是以嘻笑的形式呈现,台湾农村的无产者透过漫不经心远端一萤幕监视行车纪录器,来窥视地方权贵势力享乐的欲望。在《血观音》当中所呈现的则是,尽管作为上层的权贵,彼此之间无所不在的并非是“监督”而更接近于监视着彼此,并且彼此之间的监视又是出于对于拥有“自由的空间”忌妒与渴望,或者说是在“监视”与“奸视”丛林法则的竞争之中,互相挤压而导致的恶性结果,同时彼此之间的监控的影像则是作为小到当作要胁个人把柄而大到政商谈判的筹码。
若将两部电影相互对照,则呈现台湾的两种极端阶层,两阶层丝毫不触及彼此的目光,尽管多了更多新鲜与刺激窥视、监视的方式,如《大佛普拉斯》当中对上层的“窥探”,来自台湾新闻媒体报导形式借用,也同时嘲讽了当前的媒体生态形构民众旁观的心态),在台湾底层所面临贫富分化逐步扩大,上层政党政治的恶性斗争与政治表演中,牺牲了被围困在窥视的欲望(欲望的窥视)之民众生活的基本权利。
结语:对当下新媒介使用的再现与反省
除了以上分析电影当中性别与媒介的再现之外,因互联网形成的全球的公民意识与社会运动的连带推动的关系,在2017年的电影除了聚焦在对社会议题与性别意识的关注之外,近期电影所表现都强调了当下生活当中对于新媒介的使用,并且对于科技与媒介的使用都指向反省与批评的态度。在讨论社会儿童性暴力问题的电影《嘉年华》(2017),指向法律、媒介对于底层男性至妇幼的无所保障,并且提出尽管科技造成了个人生生活移动往来的便利,但是并非使得民众有同等的获知的管道,并且新闻媒体并没有作为民众的获知中性公开公正报导的资讯的守门人的批评,科技使得新闻媒体尽管在今日有了多元化与多层的获知权利管道,但对于未获得同权利或是没有同等生活条件的“非公民”(电影中所呈现的以身体兑换身分,可望获得新身分的外省份的移民的身份)而言,并非拥有对等的资讯条件,在人口流动的灰色地带,往往是科技与资讯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张艾嘉编导的《相爱相亲》(2017)里,则体现了当下社会对媒介科技在生活中运用的仰赖,新闻媒体对议题报导的失焦,凸显了无所不在的科技媒体造成的科技与个人伦理之间界线的模糊,表现电视台制作助理的薇薇(郎月婷饰)的母亲岳慧英(张艾嘉饰)想为死去安葬在农村的父亲捡骨火化迁到城市与母亲合葬,与丈夫到民政局请求对旧式的婚姻关系取得一当下法定所认可的结婚证明,薇薇和母亲与姥姥(吴彦姝饰)之间的关系,则代表老中青三代代表不同女性言说的位置,面对媒介则产生不同的反应。
女儿代表了当下年轻人当代对生活开放与性别议题开明的态度,在表现农村姥姥的家中,墙上装饰了女书成为标本女书文字,女书本来作为湖南江永一带女性社群之间使用的文字,或多或少电影里想表现的是在旧社会妇女仍有自身的主体位置以及社群交流的方式,但是电影里出现的姥姥则是一从农村里来为孤僻、“难沟通” ,在家族里除了宗族之间的长幼有序的秩序关系之外,是一没有归属的老妇形象。在面对以城市、城镇为主要受众以再现当代社会状况的谈话节目的空间效果,谈话节目则有意引导舞台上的姥姥则成为了一失语(没有属于农村也不所属城市以供对答的语言)的客体,并且将平日在职场与生活中表现坚强主动的母亲在节目中形塑为失控的疯妇。虽然女儿作为电视台制作助理的工作,媒体造成的偏颇的传播效应导致的失控局势,并且将家中的三名女性的表现都呈现了劣势位置,此时的父亲或是男性的缺席位置却恰好获得了幸免。电影指向了当女性曝光在媒体的镁光灯之下时,常常被呈现的形象多是负面或是基于刻板印象的描述。在电影最后,母亲攀爬在贞节牌坊的墓碑上的竞赛中,象征性地表现中年女性如何突破当下社会既定规范与刻板印象束缚的步履蹒跚。对照电影表现的新生代中产阶层出生的青年,则是不管过往的宗族制度或是面临核心家庭关系重新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代表在城市的青年女性作为个人试图克服社会舆论,并且接受多元家庭关系的可能性。
综观以上,近年来不同类型面向的两岸三地合拍电影强调了对于新媒介的再现,强调新媒体在人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新媒介如何在当代社会带来良性的互动关系,以至于达到不同文化社群以至于不同阶层间资讯上良性沟通的作用仍有大幅进步的空间。在影像里也多表现当代华人社会中所面对的多元性别平权仍有漫漫长路,如何在资讯过剩的媒介时代如何有着相应平衡的报导,不再只是求新鲜、快感的片面与碎片化描述的新媒体平台。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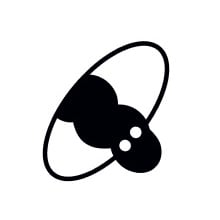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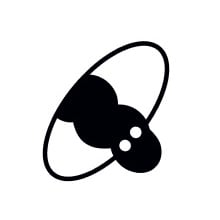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