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麟:文化“破壁人”,突破中西隔阂的尝试与回望|围炉·NYUSH


疫情时代到来后,全球化的浪潮有所衰退,我们也囙此而担心跨文化的交流会越来越困难。无可否认,不同的文化之间总存在着一定的壁垒,但从不缺乏想要打破壁垒的人。陈麟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破壁人”。他在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美十年,专注于比较文学的研究,相继获得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硕士和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的思考兴趣并不局限于他博士阶段研究的英国浪漫主义和中国古典文学,从本科学习文学开始到完成博士论文《陶渊明和华兹华斯:一项平行研究》(Tao Yuanming and William Wordsworth: A Parallel Study),他一直思考着中西文化精神的异同。如今作为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部写作课程的高级讲师,他潜心教学,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理性思辨和文化自觉,希望帮助他们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找到新时代的精神座标。

炉|游怡婷石雨歆苏子晋殷凯文徐文哲
陈|陈麟

1
从语言到文学和思想
炉|是什么样的机会让您接触到文学?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意识到自己对文学的热爱,选择以文学为专业,而后为职业的呢?
陈|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喜欢文学的。起初喜欢的其实是英语,因为我英语不错,后来高考填报志愿时阴差阳错读了英语。当时国内的大部分外语系都是以语言教学为主,复旦因为有些文学教育的根基,所以在专业教学中还比较重视文学。我在大学高年级有幸接触了一些文学方面的课,零星地读了些英语文学作品后才真正喜欢上文学的。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这条与文学结缘的路其实不太“正常”,因为我是通过英语文学进而喜欢中国文学的,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现在看起来,这种由外而内的联动变化正标志着我的文化身份意识的萌芽。
当时读莎士比亚和许多英语作品,总能感觉到那语言的美,而要通过翻译用中文传达那样的美却又如此困难,当时觉得非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不可,于是就开始读《离骚》、先秦散文、唐宋诗词等,一时不亦乐乎。这条曲折的道路让我意识到中国语文教育的缺憾。相信现在的语文教育已经有所改善,文言的教学似乎是加强了,不过应试的倾向依然,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喜欢国文的人依然不多。国文教育本来是传统教育的核心,学生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少有真正喜欢上的,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即便是选择了文科,那些文科生却往往给人一种更加擅长死记硬背的刻板印象,而很少被评估为“很有思想”。这是我们现在文化教育中的弊端,值得深刻反思。
炉|那您认为文化教育的关键是在语言吗?
陈|也不是,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媒介,是文化修习的阶梯。现在一般人使用中文写作太过随意,往往缺乏基本的自觉和敏感。我所谓的敏感,不是说作文一定要有文采,而是要认识到语言与思想和情感之间的联系。对语言麻木不仁不但会限制我们的表达,也会限制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这方面,用英语写作和中文是一个道理,要做到清晰实在,就先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和自觉,为此我们的大学生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炉|您所说的作为表达思想的利器的语言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的区别是什么呢?
陈|思想家往往对语言有比较深的体会,因为他们要表达的东西很精细,很绵密,很复杂,日常的表达很难准确而充分地呈现他们的思想,囙此他们往往必须对语言做一番改造。哲学家经常有一套自己的术语,这是他们为了准确表达思想与语言不断较劲斗争的结果。同理,艺术或者说文学的语言是文学家用以传达他们特殊的体验感受和关照的工具,也不是日常的语言所能应付的。能体会到这一层,才算对语言的高级用途有所了解。
当然,要学生使用语言时达到这个境界,早已超越了一般写作课的要求,因为这需要高度的悟性和长久的磨炼。现代的人文教育如果能够把学生带到这一境界,大概就算实现了它的真正目的。
2
教育何为
炉|您也进行了十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结合您当时的学习和最近几年任教的感受和思考,您怎么看待“教”与“学”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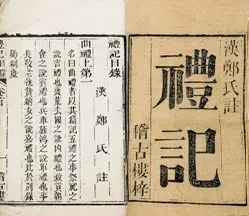
陈|《礼记·学记》曾提出“教学相长”,这是中国古人有关教学关系的至理名言。大家都听过,能明白并真正做到的大概不多。我们的教育里有多少是教学相长的?老师能通过教育促进学问吗?学生能意识到“教”——也就是一定程度的输出和回响——对自己的“学”是一种必要的激励吗?就拿上纽大的课堂来说,中国学生课堂讨论的参与度相对外国学生往往要低不少,积极的学生不是没有,但被动的总是多一些,都等着老师来灌。这种一对多的模式其实不利于达成教学效果,我觉得这方面可以适度借鉴美国学校的做法,在老师不放弃干预和引导的前提下,多给学生点主动发挥的空间。
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自觉长进比较大的时候,是自己开始做老师的时候,而不是做学生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总是一种被动,至少是半被动的状态。做老师的时候,角色不同了,你要言之有物,要把话讲清楚,让人听明白且有收获,这份为人师的责任感促使我更认真地读书、更认真地思考,同时还要给学生有益的回响,这些就是教对于学的益处。
对于学生而言,要能收到教学相长的效果,首先要完成一个观念的转化,要有一种主动意识,是自己要学; 要有一种参与意识,上课不只是来听,也是来说,这听和说的对象既是老师,也是同学,课堂是个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场所,不是一个各行其是、你赢我输的攀比过程。当然这种参与也是有前提的,即认真的准备,对同僚的尊重和一定的自信心。这就是一种教学文化,它的实现需要我们自觉参与和共同塑造。
炉|您认为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陈|现代学校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能不能转化你的观念和思想,从而转化你这个人,“悟”就是转化的标志,信心和人生目标都是通过这种转化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真正的教育你才知道自己是谁,才能拥有目标并为之奋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许都是给别人看的,但是,什么是你自己真正要的?你如何去塑造自己的人生和你所处的环境呢?这原本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特别强调的。
现代教育跟以前的管道不一样了。现在学生是在学校被动地接受教育,仿佛在走一个程式,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停地被考核。但教育本身并不是这样一件事情,你能想像孔子一个个考核他的学生,给他们打分排名吗?我有时候想,在中国这个考试文化特别发达的国度,从前为什么没有想到用精确的分数去衡量考生,难道是因为古人的智力不及吗?我总觉得考试跟教育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因为考试是一种淘汰机制。在现行的体制里,似乎只有那些能够在教育路程中不断走下去的人,才能跟成功挂钩,而被筛掉的人就是失败者,所以考试和分数才会这么重要,于是教育的目的就异化成考高分了。
炉|那在现代教育管道的这样一种变化下,是什么支持着您始终坚持在教育的道路上?
陈|谈不上坚持。我从事教育所面对的一个客观的现实是,我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我不能去做很多实用的事情,但也有主观的原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跟人打交道,尤其是青年,看到他们的进步,我很开心。另一方面,环境是由人去塑造的,我希望能够让教育环境变得更好一些,但是我的能力很有限。如果学生都很积极,我对自己也会多一份责任感; 但如果大家都是一种很功利的态度——反正我来修个学分,然后一拍两散——那教育就没有发生,只是走过场而已。
这大概就是现时教育的困境。西方是把压力放在老师的身上,以学生为中心,让老师变成一个服务者,而在中国的旧传统里,老师本是一个权威,现在却慢慢失去了这种尊严,社会地位越变越低,所以老师和学生都不安其职,老师不能专心于教学这件事,而都去关心那些外在的评估和名额。如此,教育就很难实现自身真正的目的。
同时我也不认为改革这个教学体制就能解决问题。从体制的角度去思考,能够看出不少问题,但如果把问题的解决全都依赖于制度改革,那是天真的。没有师生心里的认同和投入的热情,好的制度也只能沦为外在的规定。我以为只有把教学的理想种到老师和学生的心里,真正的教育才会发生。
炉|那您觉得有什么是当代大学应该可以调整的,以使真正的教育更有可能发生,但是现时缺失的呢?
陈|如果我们不考虑体制改革的问题,就在现行的教育体制里思考问题,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我想答案一定是多元的,我就抛砖引玉,提一点想法。既然现在教育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学生过度看重成绩,那么我们能不能设想,给学生创造一种环境,让他们适当地忘记成绩呢?我觉得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少算分。就拿我上的论文写作课为例,如果平时的作文不用量化的管道打分,而是作质的评估,或者给的分数不能简单地转化成ABCD,或许情况就会有所转变,这也正是我在尝试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做法有时候会有点自我冲突,一方面不希望学生太过看重成绩,另一方面又给几乎任何一项课程任务或行为计分。分数本来就是一种实现教育目标的权宜之计,大家把手段当成了目的,逐渐地就忘记了接受教育本是为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拿成绩这件事来说,尽量少打分,让学生多参与,把上课变成一件让精神愉悦的事,最后还能够转化成不错的成绩,这可能是大家都想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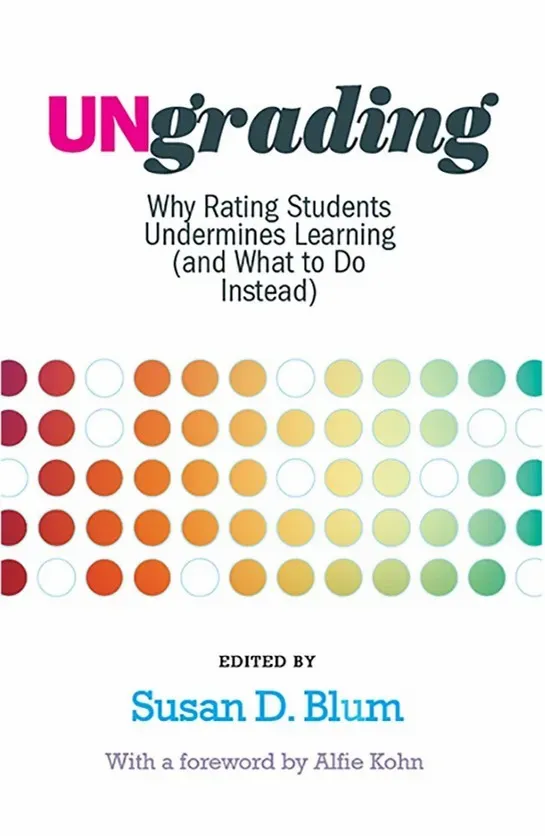
3
我们如何理解文学
炉|知人论世是一种我们比较常见的解读文学的管道。有人认为是时代成就了文学作品,有人认为是文学作品塑造和改变了时代。那您怎么看待历史行程中文学和其对应时代的关系?
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读者一般不会把时代、作者和作品之间截然切割。作品反映了作者和时代,同时作者和时代造就了作品。解读作品时,我们习惯性地从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入手,去框定其意义。好像弄清了前者,对后者的诠释就顺理成章了。这是我们大一统的国家格局所造就的文化心理、思维习惯,虽不必错,其弊端则是把两者的关系看得过于直接和简单。然而我们知道,同一时代同一作家的作品也是各种各样的,你无法解释那种多样性,所以这种或明或暗的时代作者决定论从根本上低估了作者的能动性以及作品的丰富性。但我们也不能全然否定两者的关系,问题的答案应该就在这种若即若离中。对习惯于中国式阅读的读者来说,尤其要当心跳过作品看脉络,毕竟作品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和重心,脉络的确立离不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两者的互动可以说构成一组阐释回圈。
炉|您认为文学需不需要承担起记录时代的责任?
陈|作品跟时代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想完全跳脱时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记录的就是这个时代,因为你生活在其中。哪怕你写历史小说,或者科幻小说,要想完全剥离了所处时代的印记,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看《三国演义》写的是三国时期的事情,但字里行间也反映出很多元末明初的问题; 又比如《水浒传》写的是宋代的事情,其实反映了很多明代的现实。你无法彻底地跟所处的时代切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记录的肯定是和时代有关联的。
你所谓的“记录时代”如果是刻意的,那就是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就不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空想的或者浪漫的,后者好像是要跟时代做一个脱离。现实主义写作与记录的关系更显然也更紧密,但也很难说作者的目的就是记录而已,因为文学总有一定的自由度,一定的虚构性和理想化,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它是一种创造。创造本身就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人的直觉,不是完全通过理性可以控制的,所以很难把它浓缩成一种教条似的东西。如果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去写作的话,可能已经违背了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好的文学是没有thesis(中心主旨)的,而是多义的,是丰富的,它有很多阐释空间,是对真实的创造性还原,并不是拿个摄影机把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拍下来。当然即便是摄影也隐含着摄影师的视角,传达着他的感受和关照,好的文学就更是如此了。
炉|有些所谓的名著尽管具有很高的文学性,但对于福斯,其可读性是不高的,您认为文学性和故事性是相互冲突的吗?
陈|首先我想质疑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成立,预设了两个前提:首先,我们知道你所谓的文学性是什么; 其次,这种文学性又是和故事性冲突对立的。其实这两个前提假设并不成立,或者说并不明确。我前面对文学是什么有一些总体性的论断,其实那也是粗说,并未做学术性的分辨。不过即便我们暂且认为那种论述是充分的,第二个前提也未必成立。文学和故事真的冲突冲突吗?要知道文学的一大主要类型就是叙事,就是以故事为中心的,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两者冲突呢?
我想用电影作类比的话,你要问的大概是故事性很强的商业大片和小众的文艺片之间的差别。但是文艺片为什么就不能说故事呢,可见这种艺文是相对商业娱乐而言的,没有这种高潮迭起的商业大片也就没有反大片模式的艺文制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特有的对立,而不是“文学”与“故事”本身的对立。囙此你说名著的可读性不高,这一前提也是不成立的。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趣味受到了商业文化的侵蚀,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文对这种侵蚀的抵拒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所致吧。
4
不同文化中的“意境”
炉|我们说中国古代作品的时候常常会说言有尽而意无穷,那么其他的文化中的作品是不是也有意境之说呢?体会意境是否和每个人的想法和文化背景相关呢?
陈|“意境”这个词挺难翻译的,而难翻译的多半就是有文化特色的。相对于“意境”,英语中近似一点的概念大概就是“world”。康德用“精神”“美感观念”等谈文学的丰富性,某种程度上与“意无穷”就有相通之处。我觉得海德格尔把语言说成“存在之屋”(house of being),与意境也有几分相似。有意思的是,这些概念按照字典的解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要确立这种相关性,你必须先在不同的文化中得到浸润,既能从他的角度看问题,又能从我的角度看问题,然后发现相似性,望文生义是无法搭起这种桥梁的。
语言并不只是描述客观世界的符号。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都没有客观世界的具体指向,而是一种观念建构。翻译的使命在于打通不同文化的隔阂,如果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足够大,翻译就是极其困难的事。我们常错误地以为翻译就是同义代换,学习其他语言时背单词、用字典又强化了这种认识,似乎不同语言之间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其实这是虚幻的,至少是不牢靠的。当然,这种障碍也不是不可跨越的,你到那个陌生的语言文化里生活一段时间,多用多想,慢慢就能心领神会。
所以“意境”这个词,我觉得在西方文化观念中应该也存在近似的东西,但不像在中国文化里这么强势。我们的诗词为什么突出“意无穷”?这和汉语精炼含蓄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诗文化如此发达绝非偶然。意境可以说是中国诗乃至文学文化追求的特殊的艺术理想。而在西方,即使有近似意境的观念,在诗文创作和评鉴上也处于比较后起和边缘的位置。
炉|您现在能想到有什么其他文化中的具体的作品,也营造出一种意境之感的吗?
陈|那我觉得伟大的文学都有意境,比如《哈姆雷特》,它会不断地给你提供阐释的空间,这就是一种“意无穷”。伟大的作品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确定它的意义,而是可以不断地挖掘出新的内涵。只不过可能不是通过那种诗的形式来实现的,而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文学样式,比如戏剧、小说。能让人浮想联翩大概就可以称为有意境吧,可见语言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是可以一定程度打通的。
5
中西方文学的平行
炉|我们发现您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很有意思,题为《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一项平行研究》(Tao Yuanming and William Wordsworth: A Parallel Study),我们很好奇您当时怎么会确定这样一个主题的?

陈|这个说来话长,我只能点到而止。我的根本目的还是要通,这个观念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钱钟书先生的影响。不过学通中西谈何容易,个人才疏学浅,看书太少,起步又晚,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而有限。所以面对中西方文学传统,既不能全通,又不能强不通为通,安全起见,还是决定以两位大诗人为抓手,而不做泛泛的比较,那种做法有违学术研究的态度。
两位诗人都是我极为欣赏的,大学时因学英语而爱古文,研究生时在海外又因爱中国诗而努力读西洋诗,最后选择华兹华斯是我的幸运,因为曾给予我最大的灵魂冲击的英语诗人,除密尔顿之外就属华兹华斯。
至于论文,也谈不上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是在方法上求得一点小小的突破,论文题目中所谓的parallel(平行),意思是不要捏在一块儿,应该让他们平行而不相交,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内在的完整性,但同时又能因相互参照而给人启发, 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不过对我来说,论文只是一个开端,是一场没有完成的思索,成熟的想法还在酝酿中,期待以后问世能得到你们的回响。
炉|您对于跨中西文化的思考,是不是也启发了您在上纽这样一所中外合作大学的英语学术写作必修课程中,选取中国古典文学作为阅读资料呢?
陈|对我来说,思想启蒙的第一步就要重新思考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我并非给你新的知识,而是让你意识到原来常识其实是有问题的,应该要重新思考。就像一个前沿的科学家都要重新思考已知的规律一样,因为那些规律对他来说未必是结论,而可能也是问题。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探索者,而不是简单的知识接受者。
英语课用中文的资料一方面当然是考虑到学生的文化身份,想通过对资料的讨论帮助中国学生建立文化自觉,如果有外国学生,也能促进文化交流。当然也有学术上的考量,上纽大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这个国际化的环境很容易让我们不自觉地部分接受了西方观念和话语,而处于一种文化无意识的状态。在教学中加入异质文明的元素,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从而求得真正的理解和启悟。
炉|在上纽用英语教学的环境中,您把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加入到课程体系中,有什么挑战和困难吗?
陈|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语言和文化差异。在美国式的教育环境中,英语教学天经地义,然而语言与文化是相关联的——如果只能使用一种语言,文化的丰富性也会受到限制。文化多元一定程度上是要在语言多元上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一种语言下提倡的文化多元只能是表面的。我校的中国学生至少可以使用两种语言,外国学生必修中文,在理论上他们也应该能较熟练地使用中文,事实上却未必,这就限制了大家的交流,于是文化交流就很难在教学里真正体现出来。对中外学生来说,通过一种语言去了解其他的文化会有巨大局限,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文化。
6
人文学科在当代的边缘化处境
炉|在您从事文学之前,有没有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您怎么看待就业前景等现实因素对大学生选择专业的影响?
陈|我们当时跟你们现在不一样。以前那个环境下,英语专业不怕没有工作。当时专精英语的人相对少一点,专业学英语的人当然会比非专业的人要好一点,可以做翻译等工作,长辈也不会担心你找不到工作,所以烦乱会少一点。
可现在状况不太一样,现在压力更大,竞争也更激烈。其实这个激烈也是你们共同参与造就的,很难扭转。现在你们的教育支出那么大,那些能够跟职业、前途、成功挂钩的专业,大家自然就趋之若鹜。流行的专业庞大起来了,而很多基础学科,却门可罗雀,慢慢地被边缘化。人文学科首当其冲,在西方,基础的自然科学无人问津的现象也愈加明显了。从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这样的后果是令人担忧的。
炉|那在专业热度差距悬殊的当下,您又怎样看待博雅教育呢?
陈|我认为任何学科,凡是纯粹的知识都可以成为追求的目标。一个真正对智慧、知识、真理有兴趣的人不会限于自己的领域。当然,一个人总要有自己的座标,有一个出发点、一个落脚点; 但也不能只看自己熟悉的某一个领域,置其他于不顾; 应该拥有不同学科的基本常识,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
事实上,我并没有觉得文理是打成两截、完全不通的。以前有写作课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作文写不好,因为我是个理科生,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我的回答很简单,不要被妄想蒙蔽了。西方很多思想家都是数学家,理科头脑怎么就不适合写论文了?人文思考难道是非理性的,不要逻辑的吗?我总觉得文理之间根本不存在冲突,两者的隔阂是一种人为塑造的错误观念。对大学生而言,多看看其他的东西是有启发的。在不迷失自我,找准自己的座标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宽度,不然就容易变得很狭隘。过度专业化的教育很容易使人视野狭隘,所以许多中国的一流大学现在也在向美国学习,推行博雅教育,这是对的,但是难点在于如何让这种教育真正实现它的价值。
炉|最后,我们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给我们?
陈|这是所有问题中最难的一个,因为没有范围和目标。在我们这个资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似乎很难再确立共同尊奉的经典人文典籍了。中国古代有经,近代推倒了,西方也一样,上世纪中叶,英美学院中经典(Great Books)课一度成了博雅教育的重心,后来被六七十年代的新思潮冲垮了,经典的确立一度成为学院中的热门话题,现在似乎热度也过去了,专业化的趋势总体恐怕有增无减。
我还是保守一些,学院的争论就留给学院,对普通大学生而言,我们还是不应抛却人文经典,中国的思想文化当然少不了先秦诸子、司马迁、屈陶李杜、四大名著等。西方的经典更庞杂,哲学文学也是汗牛充栋,尝试性地了解,可以从荷马开始,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圣经》、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康德、马克思、托尔斯泰……尽量读原典或优秀的翻译,实在有理解困难的可以参考辅助读物。
多读人文典籍并不是要今天的大学生忘记当下,不去关心自己的处境; 恰恰相反,有选择地读书、学会读书正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心胸和视野,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空环境。至于说阅读的步骤和选择,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所近,从一门入,专精一隅,最后的目标还是要通,“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古人的知识没今人那么多,所提的理想却很伟大。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大概也是不错的。

文|游怡婷石雨歆李永馨苏子晋
邓可欣徐诺李非凡谭晓彤
图|来自受访者及网络
审稿|张雅淇言冰天天
微信编辑|姚亦楠
matter编辑| Marks
围炉(ID:weilu_flame)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选单栏目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