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90:爱荷华的平和交锋
爱荷华城,位于美国中部,是只有6万多人口的大学城,在密西西比河支流的爱荷华河岸边,风景优美。 1967年诗人保罗·安格尔与小说家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创设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招待世界各国的一些作家来这里过过美国社会的自由写作生活,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交流。至今这计划已招待了来自120个不同国家的达1100多名作家。台湾许多作家都有爱荷华渊源,中国自1979年开始也有作家应邀参加爱荷华计划。我1979年参加爱荷华「中国周末」讨论会,1980年在爱荷华住了一个月当「访问作家」,1982年再去爱荷华会晤和访问刘宾雁,也访问了台湾老作家杨逵。后来我的小女儿在那里念大学,我多次去美国都在爱荷华短暂停留,探望老朋友聂华苓,和她的舞蹈家女儿王晓蓝。
安格尔和聂华苓的家,是建在山坡上的独立屋,门口挂着中文「安寓」的牌子,屋子宽敞舒适,常有许多作家聚集在各角落聊天。屋后是一个小森林,有野生动物出没。
1980年一个月逗留。在这里见到我年轻时就倾慕他诗作的艾青。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诗句是抗战时我爱国思想的启蒙。他见到我没讲几句,就说他在延安时认识我的姑姐李丽莲。所以,我相信他来前已经看过关于我的资料了。另一位王蒙也是我心仪的作家,年轻时读过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文革后他的作品也出色。艾青的太太高瑛跟我说,王蒙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关系匪浅,他来这里是有任务的。我们访问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我不大会煮饭,那一个月多次在艾青家吃高瑛做的菜。她说,在爱荷华最开心的事,是走进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
第二次「中国周末」,和第一次一样,广邀在美加的华人作家出席。设两个分组,同一时间在不同地点讨论。在安寓举行的是「诗组」,在王晓蓝家的是「小说组」。诗组由郑愁予主持,小说组由陈若曦主持。我在小说组,「国际写作计划」为参加者提供了我编的《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讨论就由此而展开。王蒙维护中国的政策,认为那时的中国正是处于作家的写作环境最好的时期,不同意我编的选集只集中在揭露社会黑暗,认为党提出的「识大体,顾大局」「安定团结」都是作家们切盼的。我和其他一些作家不同意任何对作家写作题材的干预,以粉饰太平的方式来维护表面的安定团结,只是藏污纳垢的安定团结。总的意见是党对文艺最好少管。这一场的讨论,是颇为激烈的意见交锋。但彼此语调平和,没有人动怒。
不过,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我发觉1979年固然是中国的文艺之春,到1980年,虽然有党官对文艺写作有种种批评和提出规限,但没有把作家打成什么「派」,没有惩罚的行政措施,也没有搞大批斗,不得不承认如王蒙所说,这是中国作家最能够自由写作的时代。跟着下来的十年,中国的言论操控还算比较宽松。那以后,是1989年六四,我想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王蒙在讨论会上说,文学的路子应该很宽,什么都可以写,我们过去太窄了。但是,李怡选的集子比我们写的还窄。
他批评我选的集子窄,也没有错。但不是比这之前的中国更窄。我选本的「窄」,是没有从广阔的文艺角度去选,而是从突破言论自由界限的角度去选。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文学写作的「虚构」性质,是不用真人实事,却写出最真的现实。 「虚构」使文学有了揭露社会真相的空间。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于是从批判《武训传》《海瑞罢官》一路下来,使小说也没有了写实的空间也。
我在这个时期关心文艺,毋宁说是关心言论自由,希望批评的声音通过文艺在中国打开缺口。我相信只有批评,社会才会进步。一言堂或鸦雀无声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不应该存在的。
我没有参加「诗组」的座谈,作家张错记下艾青说的话:「我的沉默就是我对国家的沉默,我沉默了21年就是我对国家沉默了21年。20多年,被打下牛棚,个人与外界完全隔绝,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接触不到外面如台、港、欧美的作品。……可是声音就会这样消失吗?不会的。……如果不能写诗,就干脆去打扫厕所好了,如果要写,我就要写自己的话。」
一个优秀诗人沉默21年,有比这个更「窄」的写作空间吗?
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还会偶尔想起意见交锋的王蒙,和年迈而眼神坚毅的艾青,尤其是在新闻上看到样子跟他酷似而神色同样坚毅的他儿子艾未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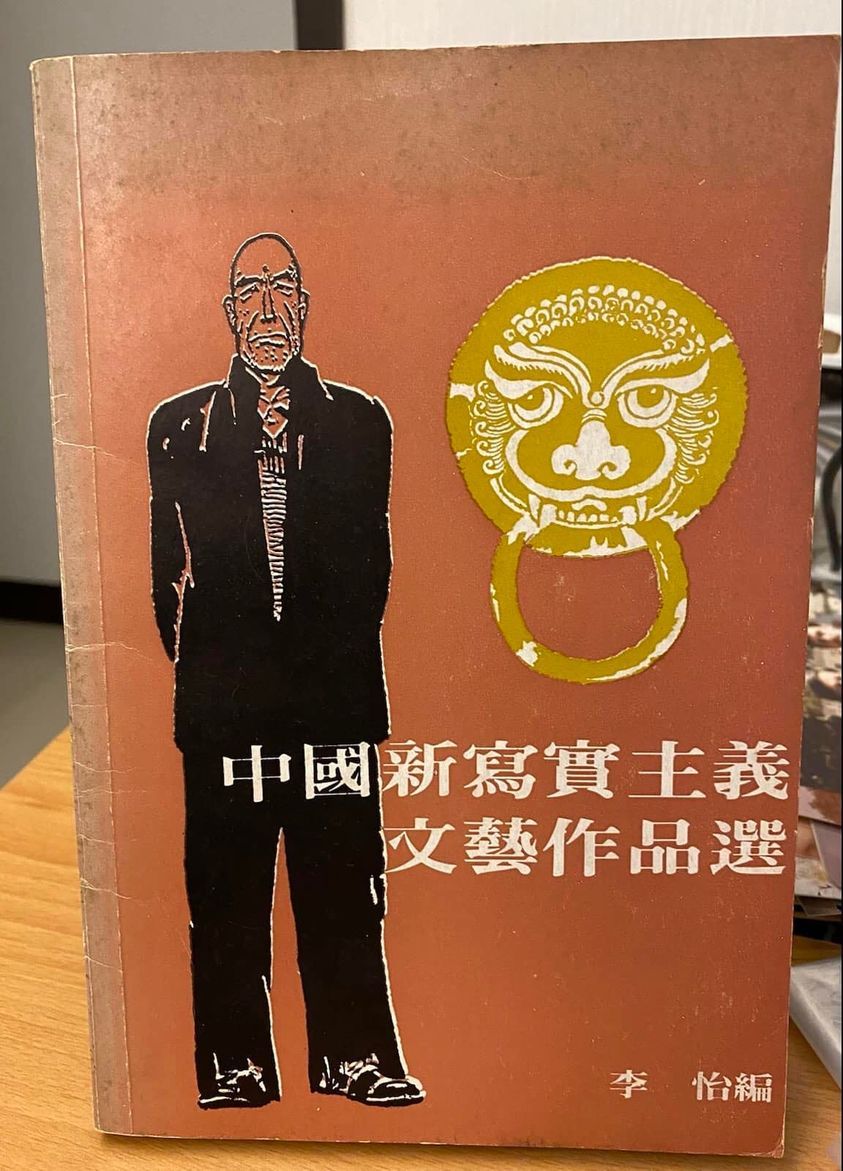
(原文发布于2021年11月19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 极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极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开始
- 太岁头上动土
- 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 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 那几年,文艺的沉思
- 爱荷华的平和交锋
注:11月22日,作者因病暂停「失败者回忆录」。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