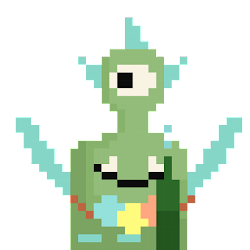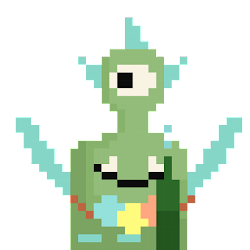去年,在太鲁阁号事故后写下的一则演讲笔记
太鲁阁号事故一周年,想起去年(2021)在屏东给青少年的一个演讲,提到了这件事,随后我在脸书写下了这则笔记。那是一个很寂静却有张力的经验。
2021.04.11
今天下午到屏东的青少年中心做了一个分享。
社工来邀约我时,我原本相当犹豫,因为大帽子是司法正义、参与式民主等等哉问。一般来说,我不会应这种没有把握的邀约,但也能感觉到接洽的社工们做了不少功课,对他们的青年需求有独到的观察。我想,几年前「死替」专案从屏东开始第一场,或许趁此机会再回顾一次,也是好事。
原先听到有「儿少代表」们会来参加,有「系列中有只报名这场活动的人」来参加,以为会是神采奕奕、自信满满的那种孩子,甚至以为是那种,可能会让人有点侵略性的青春者。
然而不是。我只是太久没走出北部,走出中年。
当我带着黑色鸭舌帽到投影幕前坐下来时,就发现不是我原本想的样子。由于那是一个采光挑高的自由空间,环绕于运动公园的生态与休闲人们的地方,我选择了将桌子撤掉、大家都坐在地上的轻松形式。即使如此,我提前20分钟到,坐下来时,他们就安静了。
即使我假装工作人员一般地兀自搞着转接头、电源等等东西,假装没看到他们,也无法减轻自己仿佛是一个压力存在般的「老师」感。我不想强迫他们提前进入状态,于是又出去和社工闲聊。
面对这样的孩子们要更专注才行,不能只顾着说话。我暗自这样想。不过并没有办法即时思考怎么整体性地调整演讲内容。我把护目镜的照片放出来,孩子们猜了很久才猜到是拍摄于香港。
社工温柔地开场。口罩下的安静,羞涩,小小动作的扭捏,和煦的眼神。早上准备的简报,精练的词句,于是被抛诸脑后。
演讲中,我把该交代的基础事实,以原先预期还要缓慢一倍的节奏,确认着气息,穿插着影片媒介。然后终于来到唯独这次才新增的一页简报:原先是想借着过去的经验,好像同作为年轻面孔的讲者我,为了要增强说服力,选择一些炫目的包装词汇,准备好要服贴那些躁动的青年,的那样内容。
嗯,这页简报不能这样说,「我想说的是,」所以我站起身挡住投影片,身体往前抛似地前倾,「可能不是什么时机都适合这样谈死刑,对吗?」同学们口罩外的动作上,看不见有什么反应。提到郑捷时,有些微的点头,但我想或许还不够贴近。
「我换另一个例子试试看,如果现在,我们谈,」然后我停滞下来。
我知道这个停滞是演讲过程里面奢侈的一声疾呼,因为一旦停滞过多次,观众会有感官上的疲劳,狼来了一般,再也不理会你的强调。我注视同学们的眼睛,三秒,同时是自己思考缓冲,措辞之间。
「我们现在,如果谈,譬如说,台铁的改革,」紧张拿捏之处在于,若有任何一个人有接近的创伤,要怎么样说出口才能不造成伤害,而又要怎么样,才能去传达我的要旨,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有效。大家都很安静,可能为我紧张,或为了什么紧张。
「我们是不是可能也没办法,现在就这样直接开始讨论呢?」我见到一些同学的眼神有点震动,「我们可以试着去想想,搭乘火车的经验,例如说我们是怎么去花莲台东的,从这样的方式去谈,而不是先去讲述那件意外,对吗?」有些同学点了头。
后来又有更多同学似乎将眼神更集中了起来。
不知道这些在十几岁的年纪,桎梏在校园里,以社工的话来说是「带着一种莫名的自卑」的人们,会怎么感觉此刻。
但那些点头和眼神的集中,清澈地治愈了当下的我。抛出去,轻柔地碰撞。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安静害羞的听众,我没有像往常那般焦虑于自己的表演,以及表演的回馈。
没有谁说出了动人的言词,没有谁大方表露情感。那种肯认,却好有力量。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