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关系本体论中的“自我” | 围炉· 冬日文艺

两个月前,我读到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关系里的“我是谁”》。文章探索了西方“自我”概念和中国“自我”概念的不同,作者认为西方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中国的“自我”是关系性的存在——在中国,人总是关系的附属,比如作为子女、下属、妻子、父母,并因为缺乏时间去思考、探索自己,而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独立的“自我”。这导致的一重结果即是自我物化——人们不重视自己的情绪,只把自己当成工具(达成某一目的的手段),然后把自我的价值寄托在外界对自己的估值和评价上。
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在大概两百年前的时候,西方哲学就已经有了对“自我”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反思,继而发展出了一种叫做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的哲学。其中一位代表性的哲学家就是马丁·布伯,他写出了在西方哲学以及宗教研究上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书,如《我和你》、《人与人》等。这继而影响了一系现象学家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对于关系性,尤其是自我与祂人的关系的反思,哲学家中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就是深受布伯影响的人之一。在列维纳斯之后,很多当代哲学家如朱迪斯·巴特勒、丽萨·冈瑟也在她们各自的作品中探讨了“关系性”的“自我”。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沿着关系本体论在哲学中的发展思路,介绍马丁·布伯以及上文提到的另外三位哲学家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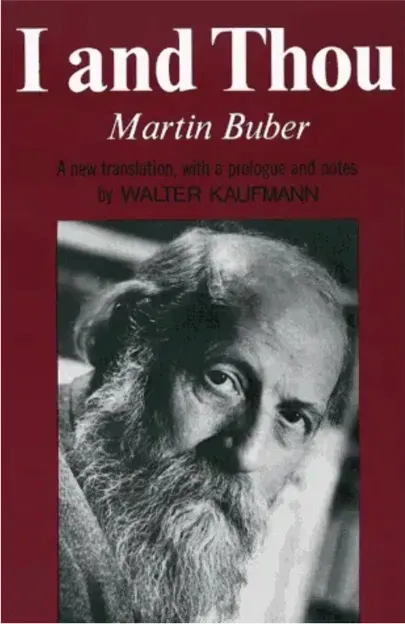
1
什么是关系本体论
假如要探究什么是关系本体论,则需要先探讨本体论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本体论研究的是“存在”的本质,它试图解释什么是终极真实的。一些问题包括:什么是存在?存在的事物有什么普遍特征?在终极现实(the ultimate reality)中什么仍然存在?
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曾经主要是实体本体论。实体并不是指一个可以触碰到的、非空心的物体,而是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其它任何事物也能继续存在的事物。换句话说,西方哲学家们曾经认为世界的终极现实是由一些独立的、脱离了任何关系的实体所构成的。
关系本体论则认为关系先于实体,它认为一个物体不能脱离它与其环境的关系而独立存在,任何物体都被自己的情境(context)或者关系所构成。或许更形象的比喻是,想像一些点和线,那么我们可以把关系本体论看作是认为事物(包括人类)是网络中的一个点,作为无数条线(关系)的交叉点而存在,也就是说,点的存在是由不同线条的交叉和移动形成的,如果没有那些线的话就不会有我这个交点。
非关系本体论,比如实体本体论,则认为是点(实体)先存在的,然后那些不同的、已经存在的点被连接起来,再形成网络——形成线(关系);线条或关系在实体或点的存在之后出现。因此,点的存在不再以其关系性为条件,而是变成了产生关系的前提;实体本体论有时候会更进一步地认为,每一种关系——无论是人与物的关系(如认知),还是物与另一物的关系,或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对事物的扭曲。
2
祂心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一个古老的问题是祂心问题,即我们相信自己具有意识,可是我们如何知道祂人也具有意识——比如,会不会祂人只是有着表面和我类似的行为,但实际上却是没有意识的空壳僵尸?
行为主义给出了一种回答:人的行为就是人的心理状态或者心智本身。当我们说一个人感受到痛苦,“痛苦”这一心理状态并不是什么神秘、内在的私人情感,而就是此人的行为——比如皱眉、抽噎、呻吟、哀嚎,或者诉说“我很痛”。因此当祂人展现出任何相关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祂人具有相关的心理状态或者意识。
然而,包括马丁·布伯在内的这一派提出关系本体论的哲学家则给出了另外的回答:祂们认为祂心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几百年前,笛卡尔提出“我思”,将“自我”定义为一个“思考的事物”,以“我”的思索来确定我的主体性和“我”存在的确定性,因此才会出现主体(我)和客体(“我”以外的祂人、世界)之间的对立,因此出现“祂心问题” (对祂人是否具有主体性或者意识的怀疑)。
然而在马丁·布伯看来,关系的存在先于自我的存在,并且自我与世界也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构成和成就。人无法脱离其关系存在,人的“自我”从初始就已经和祂人的存在纠缠不休了,也因而不存在部分哲学理论里预设的原子化的、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分离的个体自我,也自然不存在一个跟祂人完全分离的自我、或者与自我完全分离的祂人。换句话说,在关系本体论看来,人是因为祂人的存在才产生了意识。
3
我-你和我-它:
关系世界和经验世界
在《我和你》中,布伯区分了两种生存模式,这两种生存模式可以被用两个原初词概括:我-你和我-它。布伯认为前者属于关系世界,后者属于经验世界。在他看来,我-它本质上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它只是一种经验和利用,是一种对对方的物化。他写道,“我注意到了什么,我感觉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什么,我想要什么,我觉察到了什么,我在思考什么”(p.54)属于典型的"我-它"经验世界。在这里,“我”只自我,而这个“什么”是一个被主体思考、描述、体验和期待的对象,是一个"它"。他还写道,“那些体验者并不参与世界。因为体验是'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他们和世界之间。世界不参与体验者的体验。它允许自己被体验,但它并不关心,也并没有任何贡献,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它身上”(p.56)。
也就是说,“我-它” 经验世界是单方向的利用,“我”去使用这个世界,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或者东西;相对地,在我-你关系世界中,当"我"和"你"相遇时, "我-你"的关系出现了,它意味着一种相互的尊重,一种真正的连结,而不是单方向的利用和物化。
比如,如果我把一个人只当作功能性的存在——我只有需要人一起吃饭,或者需要人干活,或者需要一个随便什么对象听我倾诉的时候会想起祂——然后当我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想的只是如何能从这个人身上榨取最大的价值,那么我们的关系就注定只是“我-它”。那么,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你”关系呢? “我-你”关系意味着在我眼里,对方是一个独特的、具体的人。对方不是或者不只是功能性的,也因此无法替代。
“我-你”关系中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去接受这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就是知道对方不是一个被我掌控,或者应该被我掌控的对象。比如,当我问出一个问题、发出一个邀约的时候,当我展露出我脆弱的一面的时候,我是无法判断对方的回应的。在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经历,我是永远无法说“啊我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或者“我有完全一样的体验”,因为作为具体的个体,我们的经历无法被总体化、被还原成完全一样的东西。在“我-你”关系中,“我”可能会觉得不安、脆弱,甚至感到危险,但是这种脆弱和不确定性是“我-你”关系中的一个固有部分。
我-你中的“我”与我-它中的“我”也是不同的。正如布伯所说,经验世界中的"我"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东西,而"我-你”的关系是一个互惠的、相互的关系,启动了“我”的生命的其他维度。在一个"我-它"的经验世界里,"我"永远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因为在一个"我-它"的经验世界中, "我"从来没有被"它"当作"你"来称呼,在“我”把对方物化的同时也把自己物化了。而在我-你关系世界中, 在用“你”来称呼对方的同时,对方也以“你”来回应称呼“我” (ie, 我也被认真地当成“你”来对待、没有被物化为工具),所以我-你中的“我”是多了个存在维度,或者更圆满的“我”。
布伯显然更倾向于我-你关系,但在他的叙述中,我-它和我-你不完全是对立的,它们也互相需要。正如布伯所说,"没有它,人就无法生存"(p.85)。想像一下,如果没有对世界的感知、相信、渴望、想像和记忆,简而言之,没有“经验”我们怎么可能形成关系?因此,每一个"我-你"关系都是双重的,它同时是"我-你"关系和"我-它"经验。所以,与其说我-它和我-你是对立,不如说它们是不同维度(也就是布伯所说的“存在的不同模式”),一个人像潮水一样从一个我-它世界涌向另一个我-你世界,再涌到我-它世界,因为我-你关系总是危险、不安、短暂、难得的。布伯的预测几乎是准确而悲观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你'都至少要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它'的状态"(p.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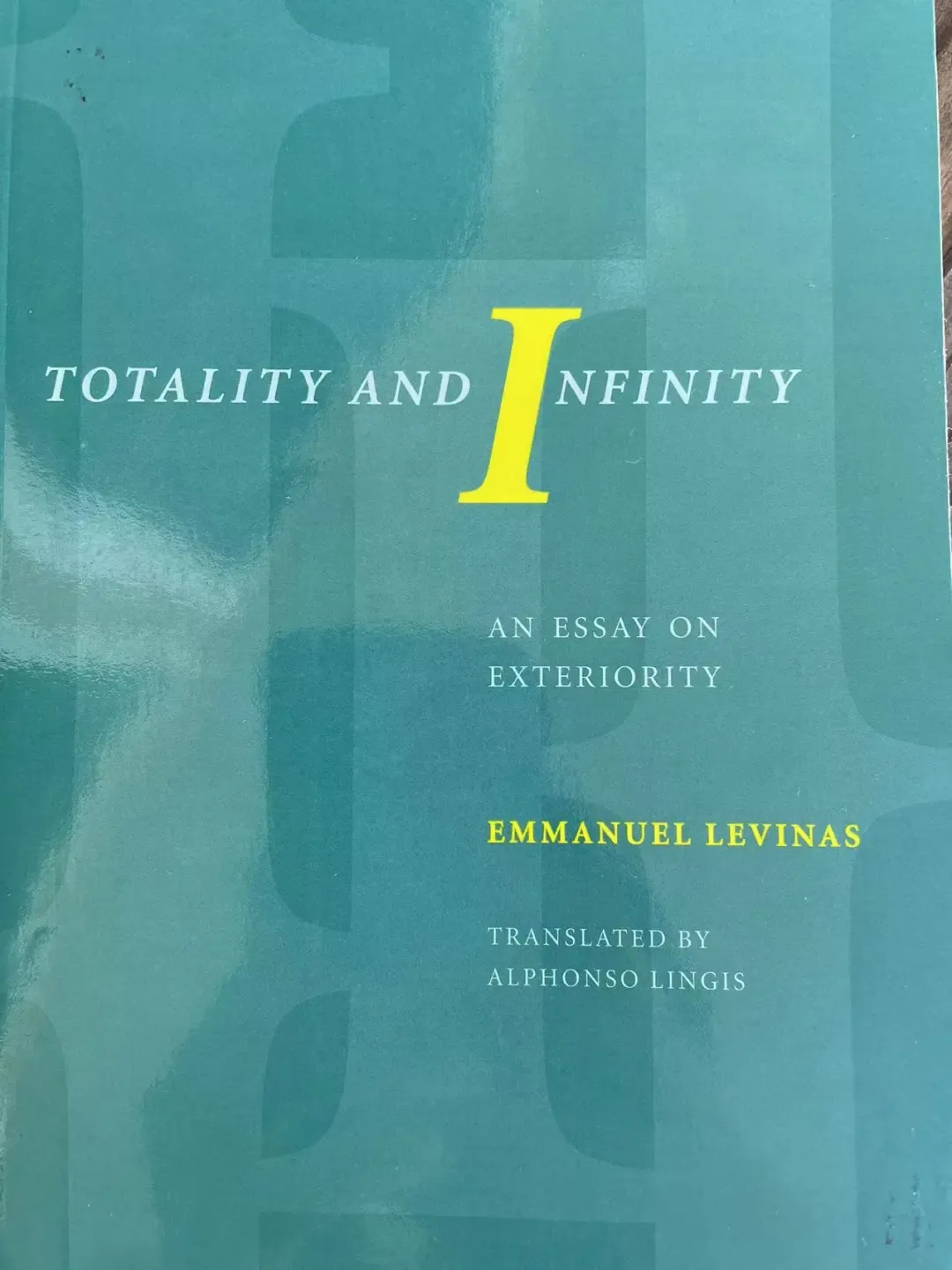
4
关系性的自我和祂者
列维纳斯则在布伯的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在《论逃避》、《总体与无限》等作品里,他探讨了人的主体性是怎么产生:正是由于祂者的呼唤和我们对祂者的无限责任,主体性才得以出现。
几个世纪后,朱迪斯·巴特勒也在《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里谈到主体性与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的关系。她认为,主体(比如一个“我”的存在、一个个体)和社会规范(比如道德准则)并不是先各自存在,再产生关联;相反,主体本身是被道德规范制约并且构建的。她提到,谈论一个主体如何去适应社会规范是一种思路,但去讨论主体本身如何由社会规范而被构建出来则是另一种思路,她想探讨的是第二种。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预设规范(norms)在主体的外部,与主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主体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利用这些规范、接受它们、与它们建立联系的方式。但是,在巴特勒看来,规范本身也预先决定了谁将成为以及谁无法成为主体,换句话说,她更想探讨的是社会规范在主体的构建中的运作和作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我-你的认识论框架,其中,自我被世界和关系创造和塑造。
社会规范总是在我们存在之前业已存在,并已经以我们无法掌控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主体性,因此巴特勒认为一些人所想像的透明的、理性的、连续的伦理主体是一种不可能的建构——我们总是只能部分地了解自己。可是,如果连对自己,我们都是部分不透明的,那我们要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伦理上的责任?一个要求我们对不完全自知的行为负责的伦理体系难道不是一种暴力吗?我们要如何重新构想主体、知识、规范、行为和伦理责任之间的关系?巴特勒在《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的后几章深入讨论了这些问题,她解开了几百年来伦理责任与完全的自治性(autonomy)之间的关系,而延续了列维纳斯的伦理体系,把责任(responsibility)与回应(response)相关联。责任(Responsibility)被解释为在祂者的召唤和命令下对祂者的回应(Response) ,而一个人需要回应或者负责的,不只是那些由于自己的错误行为而造成的后果,而也包括了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物,因为人与世界与祂者有着无限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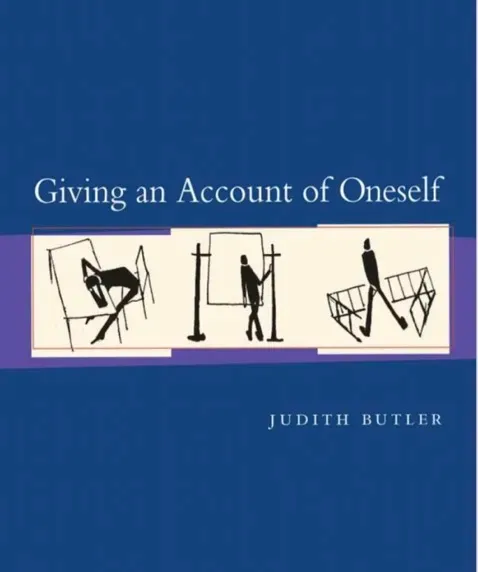
另一本书《祂者的礼物》(The Gift of the Other)中,另一位当代哲学家丽萨·冈瑟也引用列维纳斯的哲学理论,探讨出生伦理、责任和主体性的关联。与巴特勒类似,她也提出,我们对于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之一——出生——是无法掌控的,因此一个自给自足、自治的主体在最初就是一个幻象。而与马丁·布伯强调的我-你关系中的相互、互惠不同,在列维纳斯和冈瑟的哲学里,伦理涉及一种非对称的、单方向、无条件的、“我”对于祂者的回应(Response)以及无限责任(Responsibility) ;在这种回应中,“自我”自给自足、独立不依的幻像被干扰和打破,“我”发现了自己跟祂者最本源的关系性以及无法斩断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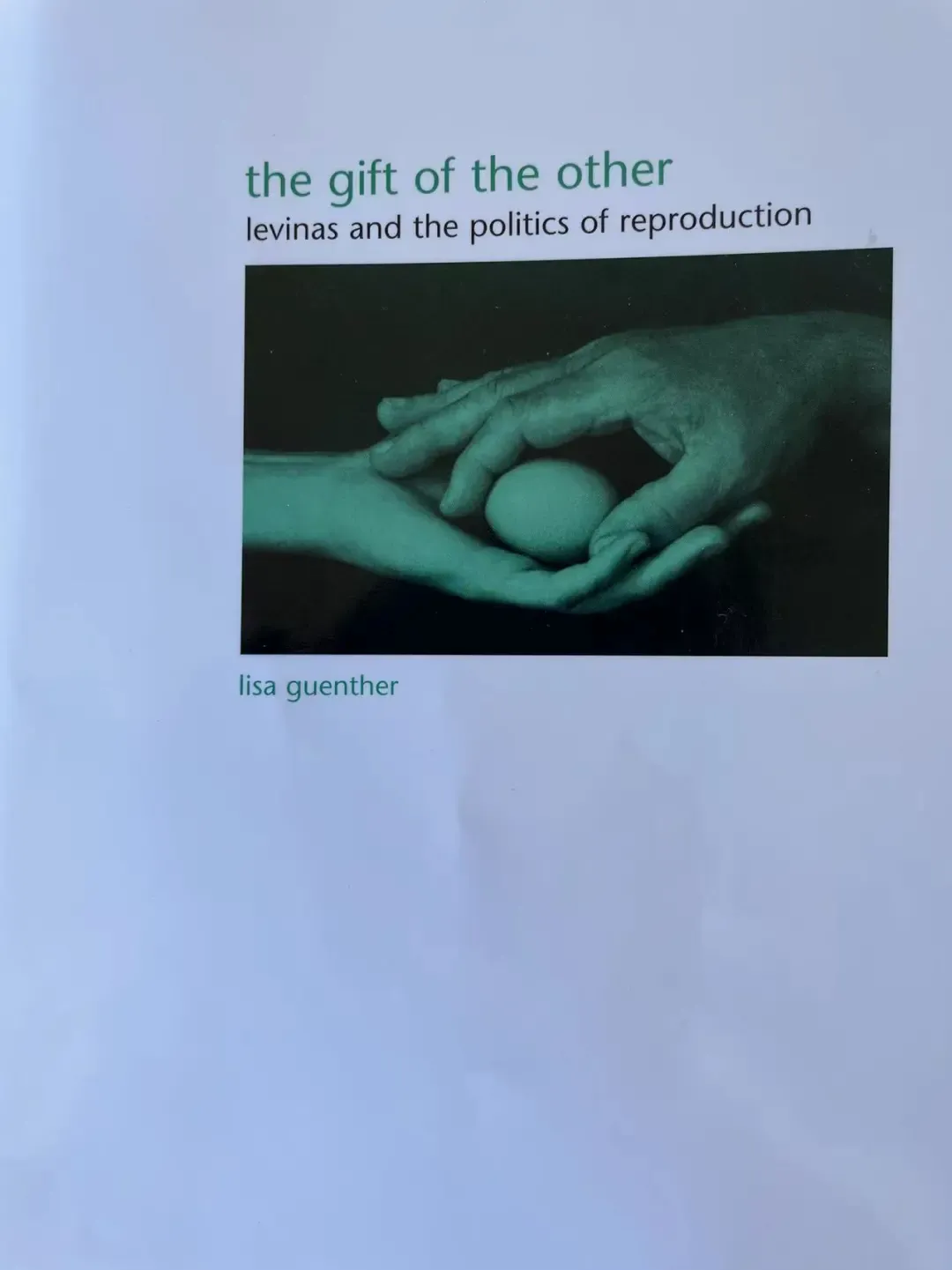
5
人是否可以跟自己
形成我-你关系?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希望回到开篇提到的那篇三联上的《中国关系里的“我是谁”》的文章,并更具体地讨论上文提到的关系本体论的一些可能的回应。
文章的作者写到,“当一个人明确知道,他脱离了所处的家庭、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定义时,他是谁,这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了。如果一个人发展出独立的“自我”,处理亲密关系也好,其他问题也好,都会迎刃而解。但当下的中国人没有从关系性的“自我”,发展成西方意义上的成年人具备的独立'自我'。”
“由于自我物化是把自己当成工具,让人完全脱离了自己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这件事情,于是,人就不会重视自己的情绪、社会和生理需要,因为'工具不需要去在乎它的感受'。不仅如此,一旦把自己看成物品,而不是拥有独一无二属性的存在,他自身的价值感就不稳定或者特别低。因为他把自己的价值跟外界对物件的估值等同了,而外界对物件的估值是不可控或者变化的。” 我觉得这两段文字都非常有意思。我的观感也有点复杂,既有赞同的部分,又有不赞同的部分。
我赞同的部分在于作者所说的人不要去自我物化,把自己当成工具和物品。换言之,我觉得一个人也要努力尝试和自己形成我-你的关系,以动态的视角去看待自己、探索自己、与自己沟通。
另一方面我觉得发现自己的价值寄托在外界对自己的估值和评价上没什么好羞愧的。事实上,人就是这样的——依赖祂人和被依赖着。一个完全独立、自给自足的“自我”,一个全然独立于祂人判断的自我判断,或许本身就是个幻象。曾经我为此挣扎着——每次因为其祂人的批评或褒奖而情绪波动的时候,我都会感到羞愧,因为我没有做到独立自治、自给自足。但是现在我接受了这一点,我接受了我们本来就是在不断地影响着祂人,并被祂人影响着——而或许,这种接受也不妨被视为一种勇气。类似地,我觉得作者所说“当一个人明确知道,他脱离了所处的家庭、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定义时,他是谁,这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了”,这也是一个伪命题。人处在关系之中,处在家庭、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中并被其定义和塑造,或许可以被视为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境况。
但另一方面,虽然人不可能脱离全部的社会关系,但人的灵活性和特殊性在于祂的一生中能同时处于多种关系之中,这些不同的关系塑造了一个人的独特性,就像是一张交织的网里一个独一无二的点。正如黑塞在《德米安》中所说:“如果我们并非独一无二的人,如果我们真能用枪炮任意将他人从世上抹杀,那么讲故事将是多此一举。然而人并非仅仅作为个人而存在,他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永远是一个关键而奇妙的点,在这个点上,世界的万千现象纵横交错,充满不可重复的偶然,因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神圣的。”
作为世界的万千现象、无数关系和社会情境纵横交错而形成的点,关系本身的存在并不是人自我物化的原因,只有当人被禁锢于某种关系或某种身份之中、无法灵活切换到另一种关系或者身份,也无法有不被这一种关系或者身份定义的行为的时候,才会导致自我物化以及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关系或者一个身份吞噬了一个人的所有其它的关系和身份的时候,当一个人把自己还原到某一个特质上、并且被唯一一种关系来定义时,问题才出现了;而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灵活地利用自己的其它身份或者关系来帮助调整自己在某一个关系里的行为和相处方式。
参考文献: Buber, Martin and Kaufmann, Walter (ed). I and Thou. New York: Scribner, 1970. Butler, Judith.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Guenther, Lisa. The Gift of the Other: Levina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Levinas, Emmanuel. On esca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Lé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庄晓丹、杨璐,中国关系里的“我是谁”,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2021.10.11,https://mp.weixin.qq.com/s/NozTujX2W34esIjz4-TOPw 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文| 刘可萱
图| 来自网络
审稿人| 言冰天天
WeChat编辑| 张宇轩
Matters编辑|Francis
围炉(ID:weilu_flame)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