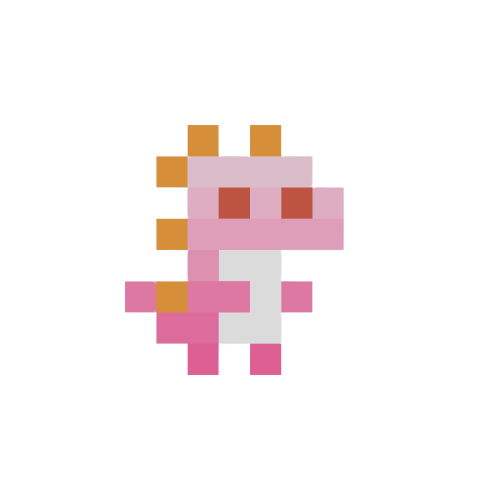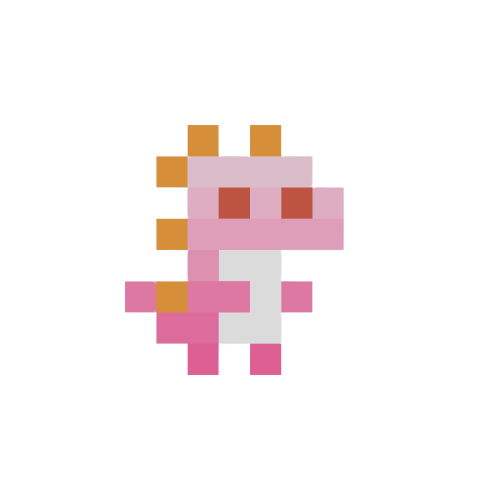Matters新人打卡|20歲的思想史,與所有人坦誠相見的邀約
我是Toothbrush,2003年生於江蘇無錫,在那裡度過了生命的前十八年,目前來到北京念本科,剛度過了二十歲的生日。
在同儕中,對未來的迷惘成為共性體驗,我也並不能例外。同時,我也渴望理解我是什麼樣的人。在友人的評價中,會出現自己從未意識到的特質。因此我深感有整理自己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希望沿著過去二十年的生活歷程建立起線索,透過回望“是什麼使我成為了現在的我”,指向未來“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另外,我也希望我的剖白能提供陌生朋友觀察理解這世代特定一群人的切口。
故這篇自白既是我作為迷茫中的大學生對過去二十年的精神審察,也希望成為我作為一個人,代表一群人,希望與所有人坦誠相見的邀約。
無論是依賴自我的感知或外部的評價,理想主義、嚮往自由、善良勇敢都佔據了重要的比重。何處是我理想主義的濫觴?我的自由主義的傾向又是怎麼形成的呢?要解答上述問題,我覺得不妨從生活史展開。
首先提供一些基本的背景。在來到北京讀大學前,我成長於無錫城市中心,鋼筋叢林中的現代生活整齊劃一,足以讓我隱入塵煙。一年級開始使用電腦,六年級開始擁有智慧型手機,網路在成長中的影響隨著網路的發展同步增加。生活於核心家庭,父母生於七十年代初,教養方式不專制,也不算放任。他們作為金融從業的白領,享受了改革開放的紅利,是政治冷感的城市中產。在我的記憶中,幾乎從不在家庭談話中論及政治與社會新聞,也不會談論文學與藝術。我所在的小學與國中系本地一所的民辦學校,身邊的同學背景相仿,家庭大都重視教育,才藝興趣班與學科補習班流行。蘇南作為「寫規範字,講普通話」推廣與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作為母語的吳語,在校園中被大規模系統性滅絕,以至從幼兒園入園到高中畢業,在學校裡我沒有講過一句無錫話,多數同學不願說不會說,不少本地同學甚至聽不懂。在主流敘事中,優質教育雷聲大雨點小,難以掙脫以選拔為目的的應試體制,學校的價值在公眾認知中被窄化為提供升學服務的機構。從升學結果來看,除了少數同學選擇留學,大部分同學悉數透過高考進入了中國的精英大學。我一如擠在罐頭裡的沙丁魚,面目模糊。
關於童年的思想狀態,不妨講述至今留在記憶中的三件小事:一是外婆常常被老年保健品公司詐騙,那時我會怒不可遏,徹夜難眠,記得曾寫過長長的檄文抒憤,認為世風凋敝,說印刷店就不應該為騙子印刷宣傳品,酒店就不應租場給保健品公司開會等等;二是在網上沖浪時讀到一篇日記,寫的是“潤”美成功後來宣誓入籍的場面,語言洋溢著驕傲,我感到一陣強烈的噁心不適,隨之而來的是長期的困惑;三是初二的數學老師因家庭變故而消極怠工、性格暴戾,上課摳腳吃點心打瞌睡,在課堂上當眾扒下男女同學的褲子打屁股。我憤怒地給教育局寫信舉報,事情傳開引起了家長之間的小風波,父母為我承擔下了背後的閒言碎語。
如果一定要概括小學與國中時的我,那應該也可以用「有樸素的勇氣、正義感的小粉紅」來牽強赴會。但當時由於思想資源的匱乏、理解世界的能力不足。周圍的校園環境如果只提供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選項,儘管難以理解,但也沒有其他選擇。整體來說,可能只是缺乏主體性的表現。
幸運的是,這階段我的成長環境大致上穩定和諧。中國社會的問題在快速發展下被隱藏,惡性裂變被家庭與校園層層過濾,只留下純淨善良。這一方面讓我失去了觀察共情社會的身世浮沉,從而構建全面世界觀的窗口,一方面也使我不曾對命運發出無力與隱忍的嘆息,沒有形成“逆受不理想現實,尋求局部的有利處境」的簡單底層情感。相反地,我得到足夠多的關於愛,勇氣,人道主義的生命體驗,累積了足夠多「明天會更好」的自信。這在後來成為了我面對過載的資訊時價值評價的重要座標。從現在看來,就是一顆理想主義的種子。
2018年通過保送,我順利進入了本地一所寄宿制的公立高中。高一文科名列前茅,但最後分班時選修理科,有基於高考招生的功利的考量,也有當時覺得人文社科學習提升是終身的事情,不著急,但學了文科再想從零進入STEM的世界恐怕就不容易了的模糊思考。但無論選課如何,高中是我思想啟蒙的重要時期,我嚮往自由的理想主義形成與此階段接觸的許多思想資源息息相關。
從閱讀經驗來看,我的高中有一個很棒的實踐,將圖書館裡千餘本書搬進了每個教室後面的小教室,大大降低了借閱的成本。藉此機會,我相當廣泛地閱讀了各種各樣的書,其中與政治思想形成直接相關的有魯迅雜文和小說,王小波的雜文和小說,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非虛構作品,反烏托邦三部曲,更直接的是龍應台、劉瑜、熊培雲、梁文道、柴靜等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通俗啟蒙讀物,如《野火集》、《觀念的水位》、《重新發現社會》、 《常識》、《看見》等。
從媒體角度來看,給我帶來影響的主要有後來停刊的網媒《好奇心日報》,常被我從圖書館裡「竊」回教室的《三聯》《南周》《南風窗》,找遍方法試圖繞過付費牆的《財新》《端傳媒》等。高中時的這些市場化媒體,儘管能力遠不如黃金時代。但以其基本的新聞專業主義,有些有深度與廣度稿子還是好看的。與自媒體浮躁獵奇的文案或黨報上面目可憎的官樣文章相比,無疑還是它們更能擄獲我的心。值得一提的是,在19年的香港,20年的武漢,一些冷靜理性、富有社會責任的報道更是在媒介素養、媒體偏好養成上,給我帶來了直接且深遠的影響。從此我有自覺地從持不同立場的媒體中獲取信息,開始關注主流議題,嘗試在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全球化與不平等,民主退潮,女權主義、性少數平權等當代大問題上把中國放入亞洲、放入世界理解。
毋庸諱言,在網路時代,資訊素養在我的啟蒙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在高中時任校電視台台長,同時有一間教室學化學競賽,因此有更多機會在住校生活中接觸電腦,也掌握了穩定的翻牆方法。此時,由於意識到世界上主流網站多被審查封禁,在簡單比較了維基與百度百科詞條質量後,隱約意識到防火牆阻礙知識與思想交流,影響深遠,這與想像中“信息高速公路”聯通地球村的樂觀主義形成了鮮明的衝突。故此時,尋找自由新世界的渴望賦予了自己翻牆道德上的正義,反抗審查的英雄主義壓倒了翻牆違法的擔憂,禁果效應的竊喜超越了自我審查的桎梏。在探索自由網路的過程中,接觸到了以阿桑奇、史諾登、電子前哨基金會為代表的密碼龐克精神;以Zlibrary、Sci-Hub為代表的海盜黨;以自由軟體、開源運動社群為代表的社會治理聯想(或許就是現在流行的DAO?)。來自矽谷的無數宣言,代表了網路自由精神中最激進的,最近於安那其主義的理想。相比較簡中互聯網在監視資本主義和國家極權的夾擊下,“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而不自知的失魂落魄,這些可能屬於未來的理念不禁讓我夢入加利福尼亞,在遙望中認真地思考賽博烏托邦理想。
在此之外,儘管老師同學們都離不開應試體制,但還是盡可能地給了我一個相對於自由包容的環境。在江蘇的語文教育中,有良好的批判性思考訓練,這點在作文教學中尤其突出。鼓勵讀寫結合,鼓勵關心真實世界並勇敢發表觀點,老文青們面對千人一面的諂詞搖頭,選擇為真誠的文學理想,戴著鐐銬起舞的獨立思考打高分,因此我與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一起遵從內心的感召,在理想主義的道路上勇敢地越走越遠。
進入大學後,社群媒體的深度使用,使得社會與校園無縫對接。同時,新冠疫情過度防疫,壓抑的陰霾籠罩大學,時代感撲面而來。大學生作為社會心態的晴雨表,在2022年5月底與11月兩次學生抗議敏銳地捕捉並放大了時代症候。在暴風眼中,「我在」的感受強烈,這使我第一次將自我置於時代浪潮的參與者位置重新審視。對我而言,在現場的觀察與參與,如注射滅活疫苗,讓我一下子共情八九學潮中我們父輩的理想主義,卻沒有墮入電影《頤和園》中那種創傷後的虛無主義。隱約可以感受到當今中國畢竟不致於是鐵板一塊,儘管短期看不到重啟政體改革的希望,但專注發展自身與身邊社群,積極參與公共生活,推動重建公民社會,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2022年底聽了台大社會系一場講座,主講世紀學生運動與台灣民主化。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從白色恐怖到彩虹飄揚。他山之石不僅令人羨慕,其實也非常有啟發,尤其是青年身分下對於未來積極樂觀的想像力,以及捨我其誰的變革世界使命感。更讓我意識到自己過去在知識累積、解釋世界和感知經驗三個方面的嚴重不足與隱形割裂:沒有紮實理論基礎上的知識框架,無法建立解釋世界的獨立敘事,更沒有在現實實踐中的經驗。
當然,20歲,成長歷程未完待續。我感覺到自己對世界的感知正變得敏銳,似乎時時事事都與我相關,每天都會有新問題等待理論解答,新想法等待身體力行。我不知道廣泛的關注是否會失焦,從而使當下舒適圈中的生活失序。但貪婪的好奇心使我如海綿一樣去讀書、去體驗,試圖盡可能多地理解複雜性的每一面,與令人冷感、迷茫、孤獨、壓抑的時代力量拉扯,來眺望房間以外的不同可能。我知道,優秀的理想主義者是現實主義者,故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熱愛當下,熱愛真實的生活。無論是漸行漸遠的舊友,或是萍水相逢的新朋,我真誠地期待與所有人建立朝向理想主義的坦誠相見的新聯結。
Carpe Diem.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