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重男輕女”、“男尊女卑”這兩個詞都不敢提了!
刚刚在中国数字时代上读到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男孩偏好”社会中的女性:地域、身份、性别的三重贫困》,文章写得很好,但是我也注意到,对于父权制社会数千年来给女性带来巨大伤害与痛苦的重男轻女或男尊女卑思想,文章虽然持批评态度,却全程不提,只用一个轻描淡写因而完全没有丝毫贬义和道德谴责意味的”男孩偏好“取而代之。
然而,哪怕仅仅从词语本身的含义上说,“男孩偏好”也绝不等同于因此也绝不能取代“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就像你不能用“种族偏好”来取代“种族歧视”。充其量,“男孩偏好”仅仅是重男轻女或男尊女卑思想在生育过程中的体现,而在父权制社会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都存在于男女两性的整个人生中,甚至死亡之后——例如未婚男性死后要给他找个女尸或女性死者的骨灰来配阴婚,甚至有人不惜为此而杀人,其实也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这两个词所涵盖的范围,远比“男孩偏好”宽广得多。
就拿三联生活周刊这篇文章来说,文中提到的“父系制度意味着男性在财产继承、居住安排、家庭延续和权力结构上的主导地位”,就不属于“男孩偏好”,而是“重男轻女”或“男尊女卑”。后面提到的“‘妇女回家’数次引起过大规模的讨论”同样不属于“男孩偏好”,而属于“重男轻女”或“男尊女卑”,把这种现象说成“‘男孩偏好’迄今对社会生活有极大的影响”,是极不合适的。
作者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全程用“男孩偏好”一词取代“重男轻女”或“男尊女卑”有些别扭,因此在文章里的两个段落中,都在“男孩偏好”后加上“女性歧视”,来指代重男轻女或男尊女卑,说“男孩偏好和女性歧视没有因为经济发展、城市化而消失”,以及“男孩偏好和女性歧视也不仅是男性专属,在这个强大文化的覆盖下,很多女性也把它内化成价值判断”。
不幸的是,从作者千方百计都要避免使用“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这样的表述来看,她自己其实也在为父权制社会的这种吃人思想辩护与开脱。她或许没有完全将这种思想“内化成价值判断”,但她显然不认为这种思想是罪恶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父权制社会中,导致女性数千年来受尽迫害与压榨的罪魁祸首。
但记者杨璐可能并不是“男孩偏好”一词的始作俑者。据我观察,这个词是随着反节育派在中国的兴起而出现并普及的,应该来自中文对英文中“boy preferences”的直译。早在2010年代,我就在茅于轼等人的著述中见过这个词。而反节育派拥戴的造假大师易富贤,更是早在2007年的一篇将中国性别比失衡甩锅给计划生育的文章中,就用“男孩偏好”取代“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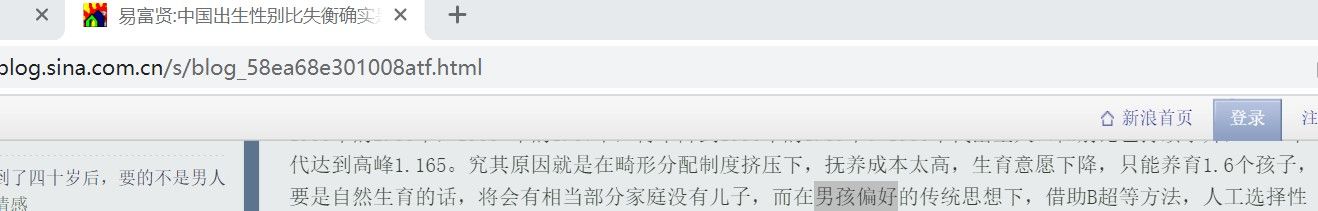
考虑到易富贤本身就热衷于父权制社会的宗族文化(参考《当吃人者摇身一变成妇女救星》),而宗族文化宗族势力又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他用这个轻描淡写的词取代明显带有贬义和谴责意味的“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为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宗族文化洗地,一点都不奇怪。
可是像杨璐这样的女性记者,为什么也会效仿易富贤之流的父权制社会宗族文化维护者用这个词?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已经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词汇?
我一度猜测,三联生活周刊那篇文章对“男孩偏好”一词的误用,以及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表述的避讳,说不定是主编给改的,毕竟他们的主编朱伟是男性。然而我在网上搜到三联生活周刊另一名记者黄子懿(疑似男性)的文章《留守女孩,被提前的成年:<不回家的孩子们>记者手记》,里面就直截了当地用了“重男轻女”一词:“关于留守的女孩们,我们零星知道的,只是她们的被动与弱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被忽视和欺辱,或者成为被熟人邻里拐骗侵害的猎物。”由此可见,避讳“重男轻女”与“男尊女卑”,并用轻描淡写、没有贬义的“男孩偏好”取而代之,并不是三联生活周刊的“潜规则”,而是女记者杨璐的个人选择。
在这个社会,最可悲的不是男性掌握话语权,而是部分能够发声的女性,也自觉不自觉地染上“男言之瘾”。
我不知道这个现象在传媒界是否普遍,背后是否有什么说法或讲究。请教一下马特市的媒体人和前媒体人们,@七月流火 、@甯卉 、@张德志 、@韓十洲 ,再斗胆@一下马特市老板@張潔平 ,请问各位了解“男孩偏好”一词在中文(尤其是简体中文)媒体圈流行的原因和过程吗?谢谢!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