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晶&艾晓明讲座音频及文字回顾:疫症之下,写作作为一种社会行动
郭晶:
《武汉封城日记》的写作的背景和初衷是比较简单的,一是重建日常生活,另外是作为行动者的社会责任。作为行动者,我非常明白发声的重要性,很多弱势群体的遭遇因此能够被看到,再开展去讨论,再进入政策议程。
封城中我的生活范围很狭窄,有一部分世界消失了,它停下来了,我的感官反而被打开了。我开始主动搜寻信息,本来普通的事情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人喜欢我的日记,也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人们在灾难中的抗争,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我在日记里写人们之间的连结,但同时我的日记让我自己成为一个连结点,再去跟更多人探索更多行动的可能性。
我的日记里做了很多自我暴露,自我暴露,必然会带来别人的评价和意见。说出自己的脆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去讲出自己小时候被家暴的经历。后来我开始理解自己的经历,理解我跟社会的关系,重新去看待自己被家暴的经历。人类的情感是有很大的共通性,很多人能够在我的写作里去找到同感,那是因为我们在经历同样的灾难。
封城日记的社会意义,一是多元的叙述方式,二是话语权的转换,三是广泛的社会连结。
参与社会行动是需要练习的。社会空间确实在不断缩小,但是我们可以去不断探索行动的方式可能性。我们也需要去了解每个人能够承受的张力在哪里?写作不是任何人的特权,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和行动,是可以通过练习去提升的。
艾晓明:(每一段都应该被传颂)
日记的深度在哪里?现在看到的这些日记还不够满足我们对日记这种文体的容量。日记这种内容的深度、丰富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对抗性,也许他还不能满足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幸存者的叙述是很宝贵的,但他们的经验还不能涵盖那些深渊里面的人的经验其万一,因为很多深渊里的人已经灭绝了,消失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我们能听到的就是幸存者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因为你活下来,没有经历死亡,你可能远远达不到那种痛苦的深度,远远没有到深渊的深处。但是尽管如此,这是一场浩劫留下来的证言,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叙述。如果我们说在一场大的疫情里,人民有那么大的付出,那么大的牺牲,还有那么多的苦难没有被表达出来,我们就知道,对于个人写作来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补。
我们要深深地认识到这是创伤下的写作,切割了很多东西,你看到的是一个很残缺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特别多的赞美,有一种不适感,我都觉得你们是不是把自己智商拉得那么低?比如有的人说我们要抢救方方,我觉得简直好笑,值得要抢救的太多了,有的人失踪了,我们多少年连他的名字都不敢说,你去抢救谁?有的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的,名字大家都不提,你要去抢救,方方在作家大院里呆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那么热衷于这么低端的,所谓正义的发泄,我觉得正义的目标太低了,我这样说话也很刻薄,怎么说?但我们得知道自己是在一种自残的状态下去做这个事儿,而不要把这事看做是完美的抗争,不要沉浸在自我美化里面。我们必须知道有限性,抗争者也要突破自己的有限性,你知道自己没有做到的是什么?想做而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的敬意要更多地给那些付出了更大的牺牲,更加直言不讳,更有勇气的人。
以日记的形式形成的一个个人叙事,是新冠疫情中出现的写作现象,它和主流媒体的情绪是拉开了距离的。我个人对所有冠之以日记的这种叙述,是抱着比较强烈的抵触情绪的。可能我这样说不对,但是我一个比较诚实的想法。我们用日记这种文体向公众公众传达信息,实际上它不是日记。那么明明不是写日记,我们为什么要叫他日记?
日记是作者跟自己的对话,我们从这个秘密里面得到一种书写的自由。同时可以在日记里做自我探索,其中包含多种自我,否定的自我,过去的自我、成长中的自我,我们所理想的未来的自我,然后这几种自我可以互相对话、互相质疑、互相砥砺、互相否定,然后我们从中间生长出一种作者的写作人的一个主体性。在这种主体性的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我们体会到了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日记不会是一种孤立的状态,它和社会一定是有关系的。不管作者是谁?是什么专业?日记的一个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提出怀疑、质疑主流的意识形态,质疑流行的观点,坚持不同的意见,而越是具有这种对抗性,他在后世可能就越有价值。所以我觉得这种写作其实是一种语言的抗争,它能够形成一种抗争性的叙事。
我们常常面对两件事情不可以公开谈: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因为这两件事都是有非常强烈的规范,强大到什么程度?强大到可以构成一个压迫性的力量,构成一个推翻性的力量,推翻我们的个人经验,推翻我们的个人感受。然后把我们置于被审查、被批判的中心。我们看到很多真实的日记,后来成为一种公共读本的时候,我们恰巧非常喜欢日记和公共论述里面对抗性的因素,是里面有意义的成分。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言论管制,不是说我们个人通过一本日记得到了发表,我们就真正能够把它看作一种话语权的转换成功,当我们看到这些日记能出版的时候,同时还要知道,这样的发声渠道其实是被狭窄化了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有很多声音是发不出来的,我想直率地说一些公众号能够幸存,不要把它看作言论自由的胜利。我希望幸存的人能够了解到牺牲的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和牺牲的人们连结?怎么连结?我不能回答,我把问题提出来。
再一个就是非专业作者和专业作者的困境。这两类作者得到的采访条件完全不一样。那些公民记者去了,消失了,这个是我们要去想,要去挂念的,要去放在心上的。我们怎么样去研究困境中的记者?专业记者和非专业记者之间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连结和互动,从而为公众争取到充分的信息自由,这也是一个挑战。
人民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其实我们对苦难的描述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抗争性的论述是非常必要,又非常稀少的,我们还远远没有抵达灾难,牺牲和痛苦的深度。因此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大的挑战——我们要怎样写作?我们要怎样承担写作的使命?怎样才能通过个人叙述建立起一个对抗性的文本,来实现一种语言的抗争,从而使文本将来能够成为公共记忆的一块基石。
部分问题:
1. 作为一个普通人,公共生活写作经常觉得疲惫无力,到底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在哪里?
2.国内现在做社会工作的环境跟氛围是什么样的?郭晶你有没有感到失望过?你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3.对于一个初想尝试公共写作的人,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到底怎么样判断自己写的东西会不会太私人,欠缺公共性?
4.怎么处理自我表达的充分性跟审查制度的关系?
5.会不会担心在写到弱势群体的时候,自己说的不完整或偏颇错误地代表了别人?会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建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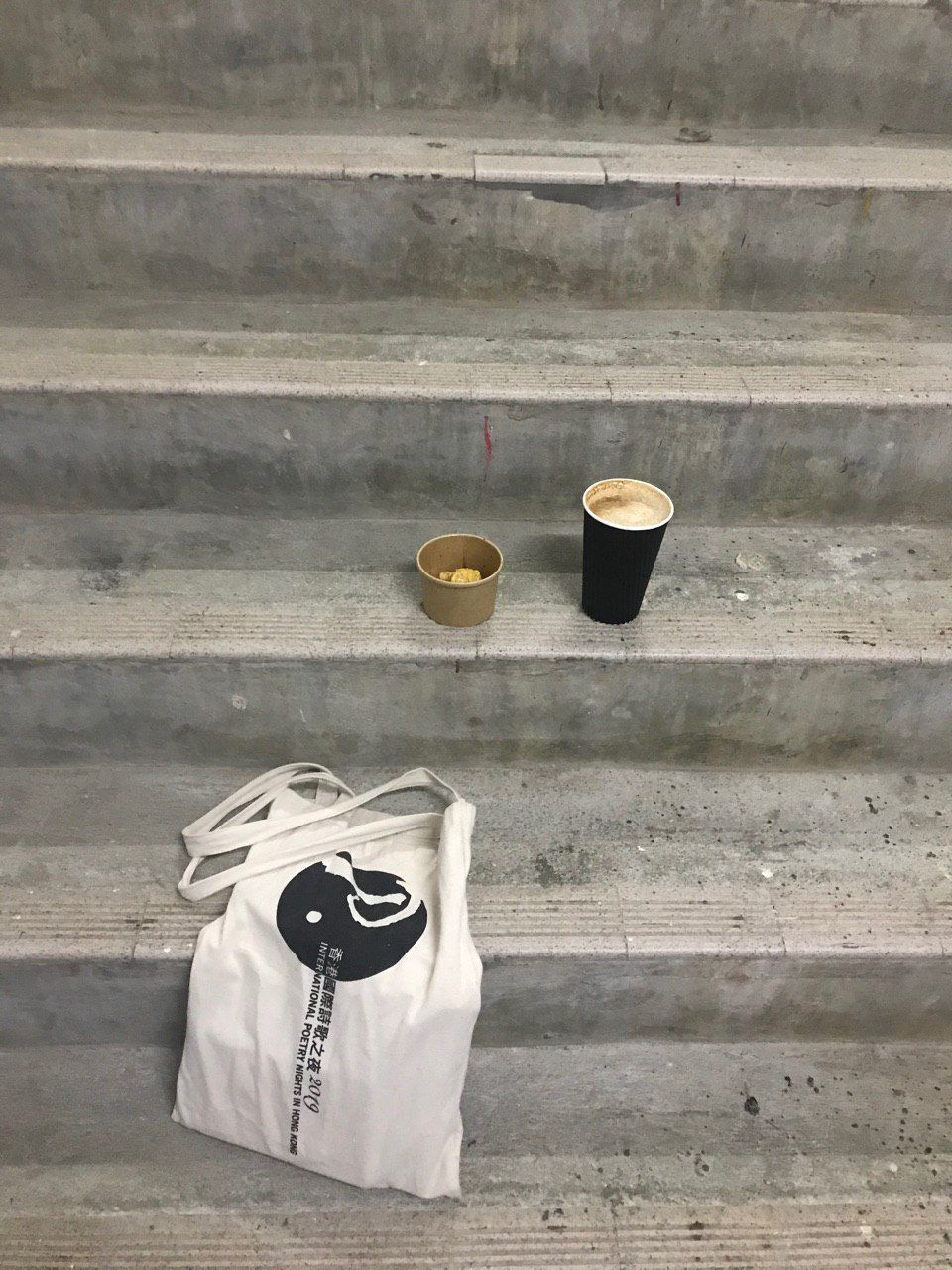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