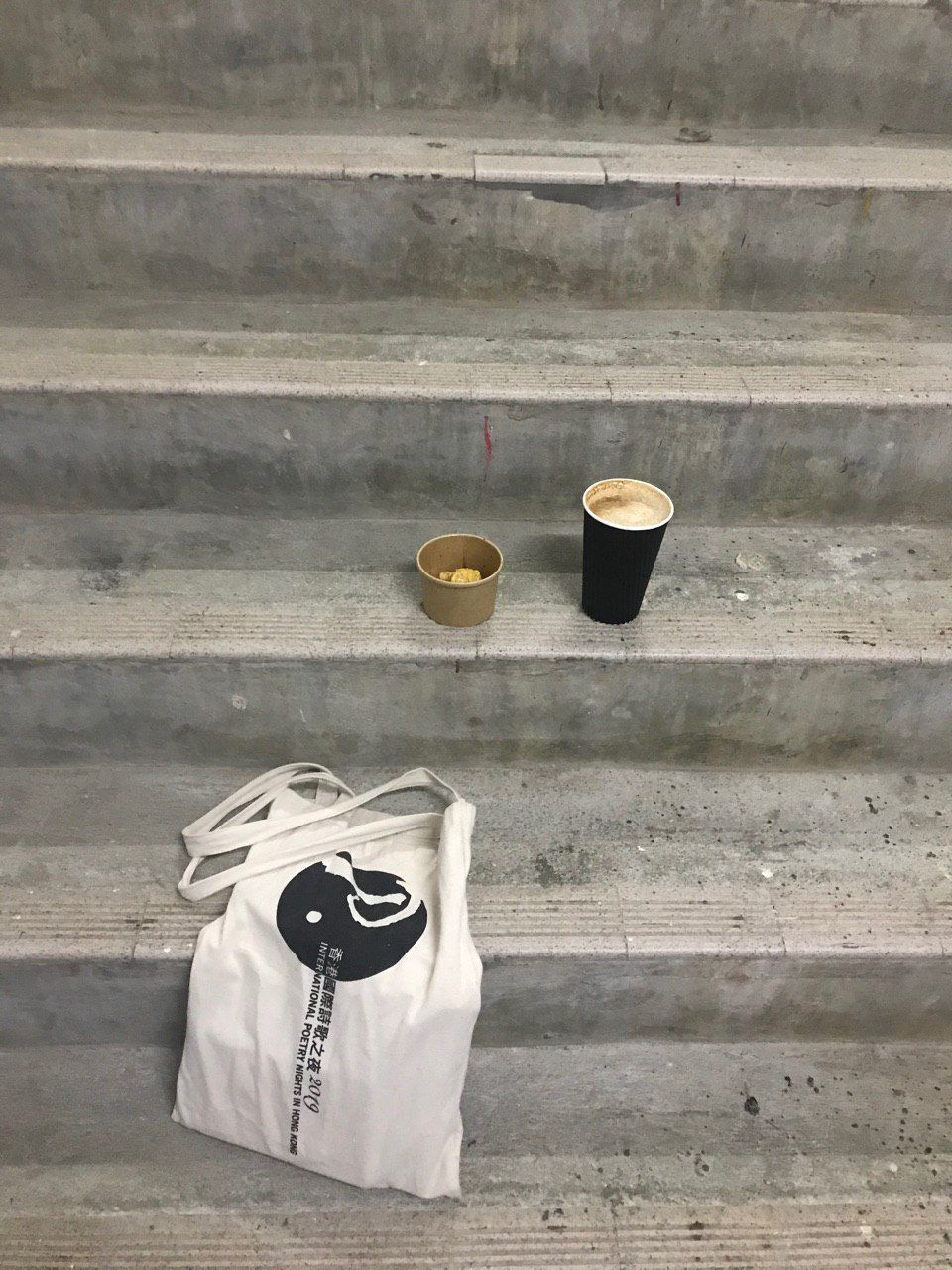郭晶&艾曉明講座音頻及文字回顧:疫症之下,寫作作為一種社會行動
郭晶:
《武漢封城日記》的寫作的背景和初衷是比較簡單的,一是重建日常生活,另外是作為行動者的社會責任。作為行動者,我非常明白發聲的重要性,很多弱勢群體的遭遇因此能夠被看到,再開展去討論,再進入政策議程。
封城中我的生活範圍很狹窄,有一部分世界消失了,它停下來了,我的感官反而被打開了。我開始主動搜尋信息,本來普通的事情就變得很重要,很多人喜歡我的日記,也是因為大家看到了人們在災難中的抗爭,我覺得這是非常珍貴的。我在日記裏寫人們之間的連結,但同時我的日記讓我自己成為一個連結點,再去跟更多人探索更多行動的可能性。
我的日記裏做了很多自我暴露,自我暴露,必然會帶來別人的評價和意見。說出自己的脆弱是非常需要勇氣的。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夠去講出自己小時候被家暴的經歷。後來我開始理解自己的經歷,理解我跟社會的關系,重新去看待自己被家暴的經歷。人類的情感是有很大的共通性,很多人能夠在我的寫作裏去找到同感,那是因為我們在經歷同樣的災難。
封城日記的社會意義,一是多元的敘述方式,二是話語權的轉換,三是廣泛的社會連結。
參與社會行動是需要練習的。社會空間確實在不斷縮小,但是我們可以去不斷探索行動的方式可能性。我們也需要去了解每個人能夠承受的張力在哪裏?寫作不是任何人的特權,每個人都可以表達和行動,是可以通過練習去提升的。
艾曉明:(每一段都應該被傳頌)
日記的深度在哪裏?現在看到的這些日記還不夠滿足我們對日記這種文體的容量。日記這種內容的深度、豐富性、多元性、差異性和對抗性,也許他還不能滿足我們對這些東西的追求。倖存者的敘述是很寶貴的,但他們的經驗還不能涵蓋那些深淵裏面的人的經驗其萬一,因為很多深淵裏的人已經滅絕了,消失了,我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我們能聽到的就是倖存者的聲音,這個聲音可能因為你活下來,沒有經歷死亡,你可能遠遠達不到那種痛苦的深度,遠遠沒有到深淵的深處。但是盡管如此,這是一場浩劫留下來的證言,是我們能夠得到的敘述。如果我們說在一場大的疫情裏,人民有那麽大的付出,那麽大的犧牲,還有那麽多的苦難沒有被表達出來,我們就知道,對於個人寫作來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補。
我們要深深地認識到這是創傷下的寫作,切割了很多東西,你看到的是一個很殘缺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看到特別多的贊美,有一種不適感,我都覺得你們是不是把自己智商拉得那麽低?比如有的人說我們要搶救方方,我覺得簡直好笑,值得要搶救的太多了,有的人失蹤了,我們多少年連他的名字都不敢說,你去搶救誰?有的人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消失的,名字大家都不提,你要去搶救,方方在作家大院裏呆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要那麽熱衷於這麽低端的,所謂正義的發泄,我覺得正義的目標太低了,我這樣說話也很刻薄,怎麽說?但我們得知道自己是在一種自殘的狀態下去做這個事兒,而不要把這事看做是完美的抗爭,不要沈浸在自我美化裏面。我們必須知道有限性,抗爭者也要突破自己的有限性,你知道自己沒有做到的是什麽?想做而不能做的是什麽?這個時候我們會知道我們的敬意要更多地給那些付出了更大的犧牲,更加直言不諱,更有勇氣的人。
以日記的形式形成的一個個人敘事,是新冠疫情中出現的寫作現象,它和主流媒體的情緒是拉開了距離的。我個人對所有冠之以日記的這種敘述,是抱著比較強烈的抵觸情緒的。可能我這樣說不對,但是我一個比較誠實的想法。我們用日記這種文體向公眾公眾傳達信息,實際上它不是日記。那麼明明不是寫日記,我們為什麽要叫他日記?
日記是作者跟自己的對話,我們從這個秘密裏面得到一種書寫的自由。同時可以在日記裏做自我探索,其中包含多種自我,否定的自我,過去的自我、成長中的自我,我們所理想的未來的自我,然後這幾種自我可以互相對話、互相質疑、互相砥礪、互相否定,然後我們從中間生長出一種作者的寫作人的一個主體性。在這種主體性的我們體會到了什麽?我們體會到了思想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日記不會是一種孤立的狀態,它和社會一定是有關係的。不管作者是誰?是什麽專業?日記的一個迷人之處就在於它提出懷疑、質疑主流的意識形態,質疑流行的觀點,堅持不同的意見,而越是具有這種對抗性,他在後世可能就越有價值。所以我覺得這種寫作其實是一種語言的抗爭,它能夠形成一種抗爭性的敘事。
我們常常面對兩件事情不可以公開談:一個是性,一個是政治。因為這兩件事都是有非常強烈的規範,強大到什麽程度?強大到可以構成一個壓迫性的力量,構成一個推翻性的力量,推翻我們的個人經驗,推翻我們的個人感受。然後把我們置於被審查、被批判的中心。我們看到很多真實的日記,後來成為一種公共讀本的時候,我們恰巧非常喜歡日記和公共論述裏面對抗性的因素,是裏面有意義的成分。
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社會問題——言論管制,不是說我們個人通過一本日記得到了發表,我們就真正能夠把它看作一種話語權的轉換成功,當我們看到這些日記能出版的時候,同時還要知道,這樣的發聲渠道其實是被狹窄化了的。我們必須要知道有很多聲音是發不出來的,我想直率地說一些公眾號能夠倖存,不要把它看作言論自由的勝利。我希望倖存的人能夠了解到犧牲的人,這裏就有一個問題——我們要不要和犧牲的人們連結?怎麽連結?我不能回答,我把問題提出來。
再一個就是非專業作者和專業作者的困境。這兩類作者得到的採訪條件完全不一樣。那些公民記者去了,消失了,這個是我們要去想,要去掛念的,要去放在心上的。我們怎麽樣去研究困境中的記者?專業記者和非專業記者之間怎麽樣能夠有更好的連結和互動,從而為公眾爭取到充分的信息自由,這也是一個挑戰。
人民承受了那麽多的苦難,其實我們對苦難的描述是遠遠不夠的,這種抗爭性的論述是非常必要,又非常稀少的,我們還遠遠沒有抵達災難,犧牲和痛苦的深度。因此對我們每一個個人來講,都是非常重大的挑戰——我們要怎樣寫作?我們要怎樣承擔寫作的使命?怎樣才能通過個人敘述建立起一個對抗性的文本,來實現一種語言的抗爭,從而使文本將來能夠成為公共記憶的一塊基石。
部分問題:
1. 作為一個普通人,公共生活寫作經常覺得疲憊無力,到底能夠堅持下去的動力是在哪裏?
2.國內現在做社會工作的環境跟氛圍是什麽樣的?郭晶你有沒有感到失望過?你有什麽樣的期望嗎?
3.對於一個初想嘗試公共寫作的人,想問一下兩位老師有什麽樣的建議?到底怎麽樣判斷自己寫的東西會不會太私人,欠缺公共性?
4.怎麽處理自我表達的充分性跟審查制度的關係?
5.會不會擔心在寫到弱勢群體的時候,自己說的不完整或偏頗錯誤地代表了別人?會有這樣的經驗或者建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