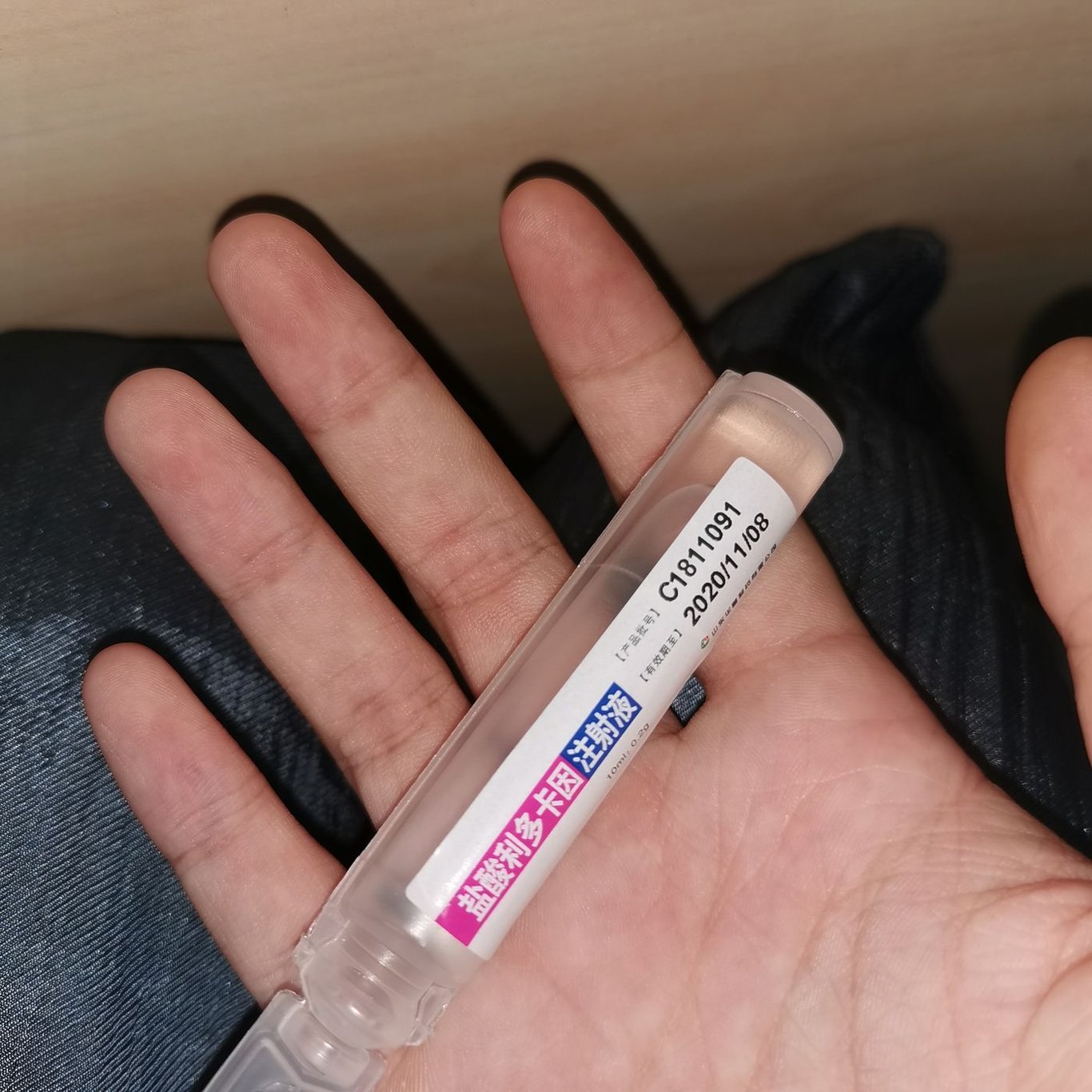
体认性别
城際交通抵達鬧市,我們會碰見流浪漢。
我曾坐過很多次開往莘莊的地鐵。因它是一個樞紐,且在城郊與中心的分界點,總會在不同站點匯集很多人。
大一的暑假,我每天晚上六點從十三號線轉二號線轉五號線回到學校,為了在另一個校區修電影課。有一天我回來時,在微博裡寫道“每天順著地鐵上下課,遊走在上班族之間,我們共同方向和去處,彷彿一具被搬運的屍體”(這句話,在今天跟你在樞紐站換乘時又突然想起);大二的寒假,我從莘莊去往寶山,為了修數據分析課;後來大三,我開始工作,定居市內而不再需要長時間的往返。我們也適應了快速的出租車和慢慢接受它昂貴的收費……
事情從哪裡開始變得不一樣的呢?從能夠忍受往返四小時的公共交通到不再能夠接受與上下班的人摩拳擦掌開始的嗎?我已經無法回顧那個變化的瞬間,甚至在對於記憶不再清晰的時刻,都羞於承認自己逐漸放大的鈍感。
曾幾何時,敏銳和效率是我生活的重心。我永遠需要理性至上的邏輯,也永遠服從冰冷有效的規則。但是當這些東西無法解決我源自自身的困境時,彷彿所有的信仰都被消解了,而無處可去。這是一種極端的痛苦和無助,也覺得無法呼救——因為長期堅忍和頑強。
那是一種無法與餐廳玻璃牆外的流浪漢對視的情緒。儘管直視他們的襤褸時,知曉自身必然會因此而產生負面的情緒,但是卻無可避免。我們無法與流浪漢對視,對視的瞬間似乎就是直視自己那個“道德的污點”,而必定要坦蕩地接受無視“弱小”和“底層”的自己,因為對他們的不信任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當他們乞討結束,會開著自己的轎車回家”、“有太多流浪漢,其實過著還不錯的生活”……這樣的說法甚至已經突破了地域、宗教甚至國家的邊界,成為一條現代人避而不談的公約。
我也無法回想,我童年時那些氾濫的同理心是如何逐漸消失的。在中學以前,小學時代,我對國家和社會沒有概念,我的夢想是能夠支持所有流浪漢的生活。當我學會思辨,通達事物存在正反之後,我則對此保持懷疑;當我聽到來自成年世界的聲音,教導我們不要過於相信人的面孔時,我的懷疑被逐漸支持……所以在廣義的道德和逐漸成長的、被建構起來的理性中間,好像什麼東西被天然地放棄,成為一種“成長”必須的代價。
以往我自豪於做一個“大人”,而今我卻越來越接受自己是“小孩”,這好像一種滑坡:忍耐和接納自己遲鈍與並不聰明的面孔,而放棄曾經的野心和故事。所以,當看向你時,我似乎恐懼你帶有能夠直視流浪漢的勇氣,但也驚訝於你並非如此;或者好像看到在地鐵裡侃侃而談的你,負載曾經我的諸多信仰和想像;又或者似乎你能夠忍耐長時的交通去奔赴和運動,而不需要買來的便利……
我無法自得地說這是一種成長,但是接受自己的平庸,彷彿也是與自己和解最重要的方式。或者當有一天我們發現,不再因為一首歌、一句詩、一張畫、一部電影感動時,也能容忍自己的平靜;或許不再運動時和保持active時,也並不是一種可悲和死去。
這是一種好事嗎?我不知道。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發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