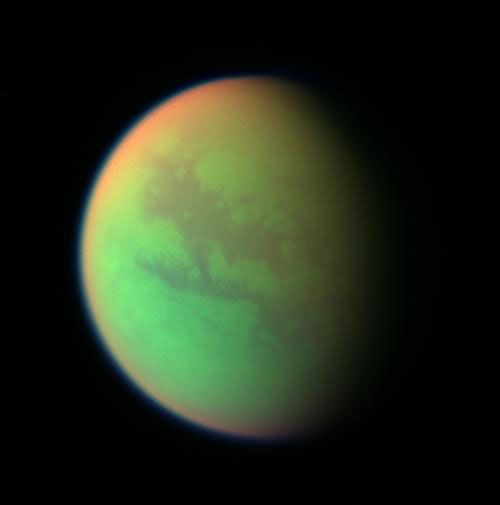
Volo ut sis.
边境
上车前,其中一名乘客问这位载我们下山的「司机」:「欸!你成年了吗?」这位脸色泛黄但是挂着笑容的藏民男孩表示肯定,尽管包含我在内的四位乘客都不相信他有驾照。 「出发啰!」男孩坐在这辆灰尘遍布的手动波箱汽车的驾驶座上,用手机播放起一些除了旋律之外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歌曲——除去那些藏文歌词,那些干瘪的摇滚旋律似乎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
在车里感受到的入夜后的原野和入夜前没有太大分别,路不会因为黑暗平等地覆盖大地而变得平整,更何况这里并没有路。乘客因为颠簸而剧烈摇晃。男孩也摇晃,但他播放的藏文摇滚乐又让我觉得他自己是故意在摇晃,毕竟他看起来像是将这块原野当成他的舞池。车的高灯(远光灯)照亮了前方枯死的树干,他猛打方向盘躲闪,大声唱着歌,但完全跟不上播放的音乐,好让各位体验他故意营造的刺激与混乱。 「哎呀!天黑啦!找不着路啦!」他故意吓唬我们,让大家更相信他未成年。坐在前座的我随口说了句:「那你按着那些轮胎印走就行。」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抵达了山下的营地,男孩的音乐声也随我离开他的车而中止。那位在此等候多时的司机,真正的司机,抽着烟看着我朝他的车走来,笑着问我:「怎样?你看那些藏民开车是不是不要命一样?要是这里发生交通事故了,警察过来,他们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我坐上了他宽敞整洁的车,他把车驶上刚好够宽的柏油路,路灯的光在黑夜把整条路投射到司机的视野中,提示他仅能以规定的轨迹行驶。道路两端像是边境,司机被禁止闯进边境之外的区域,那是光无法覆盖的地方,意味着泥泞、违法甚至是生命危险。
司机全神贯注,车里播放的是他选的「正常音乐」。即便有个别路段没有路灯,车灯所照亮的地面依然有交通标线;没有标线的地方,乘客至少知道那是条可以支撑汽车的稳固的路。无论如何,只要车在平稳行驶,只要窗外能看见任何人造物的迹象,乘客便可以沉浸在「实证主义的喜悦」中,尤其是那些刚从没路的地方回到柏油路上的乘客。
从塔迪姆餐厅享用完美味的牛肉汤后,我起身前往独立大街的尽头,也就是塔克西姆广场,路上经过了一个月前发生恐怖袭击的地方。广场中央是共和国纪念碑(Cumhuriyet Aniti),是随着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而被浇铸成实物的记忆。这个纪念碑上面有国父凯末尔、举着旗帜的士兵、抱着婴儿的妇女、马匹等,外围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都象征独立与胜利的拱门。 2022年末的这次旅行中我造访了不少纪念碑,这一个是雕刻得最复杂的。上面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官方、游客、学者等解读了成千上万次,例如凯末尔穿西装意味着土耳其要成为现代化的共和国。这么一看,土耳其语弃用阿拉伯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来拼写这类事件也能和凯末尔穿西装相关(修改拼写方案也的确是凯末尔的杰作)。

这又是另一种「实证主义的喜悦」。历史事件(记忆)被诸如凯末尔主义等意识形态统摄,然后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被输出到公众的意识中。这些记忆被仔细打磨,然后进入工业化流程,输出成游客可以拍摄甚至购买的产品:雕像、明信片、钥匙扣、书籍、电影⋯⋯这些记忆产品对来访者——不论她是当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 —发出警示:你只能以规定的方式记忆这些事件。凯末尔不会像末代苏丹一样再度穿上传统服饰。落日之下,共和国纪念碑的轮廓便是记忆的边境,任何超出边境的行为皆被视为违法。
数日后我到访的另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我多年前在书中读到过。它位于塞尔维亚第三大城市尼什(Niš)郊外的一座山丘上,名为布班(Bubanj)。形态上,它是三个拳头,分别代表二战时在此地被杀害的儿童、女性和男性,共有近一万名。相比伊斯坦堡的共和国纪念碑,布班要抽象得多,和南斯拉夫土地上所有纪念碑式建筑一样抽象。拳头没有清晰可见的手指,仅仅是几个方块和棱柱的拼接。站在这三个拳头所组成的空间中,我不能像一眼认出凯末尔一样认出哪个拳头代表的是哪一类受害者。在这里被呈现的二战记忆,比先前在伊斯坦堡所接过来的土耳其建国记忆要模棱两可数百倍。尽管在视觉上,布班的形状要硬朗得多,也十分直白地传达出战争的残酷性和对建立新政权的决心,但是它的边境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难以捉摸。

它不像南京大屠杀或是吐斯廉一般的博物馆,赤裸裸地将死难者骸骨置于访客眼前。了解布班所纪念的死者仅能依靠想像力。尽管我研究二战的历史,但我对塞尔维亚在二战中的具体情形,或是八十年前发生在布班的事情毫不知情。对于毫无历史知识的外国游客而言,他们更无法想像这些拳头的意味。因此,布班构建了相当虚弱的记忆边境:它无法向我传达记忆的细节,而仅能唤起我的想像力,促使我运用最低限度的道德自觉与死难者共情,而非在这阳光普照、青草遍地的公园里大声欢笑。但事实上,这个公园是尼什市民的郊游地之一,在此野餐、遛狗甚至举行音乐节都不会遭受任何谴责,毕竟模糊的记忆边境削弱了它对观者道德上的约束力。而在土耳其,侮辱国父可被检控,共和国纪念碑因而无法容忍在它面前所表现的任何不庄重。
然而,我并非要在凯末尔和布班两个纪念碑之间分出个好坏来——边境的强弱与纪念碑的好坏,与后世所呈现的记忆之公正性毫无关系。无论是被路灯在视觉上串起来的山间小道,还是完美雕琢的凯末尔雕像,它们都指代一种被规训的路径。正如我总是从我居住的地方下斜坡走到上环站,按灯箱上的箭头和文字安排自己的路径,被规定好方向的扶手电梯带到月台。陈如茵(Cheri Chan)的广东话和英文广播告诉我即将到站的列车终点站是柴湾(港岛最东端),所以我相信上车后绝对不可能坐到坚尼地城(港岛最西端)。站在月台上,面前隧道里的黑暗被屏蔽门隔绝。门是由玻璃做的,所以反射着月台充足的灯光,让人觉得面前的黑暗并不真实。广播结束,进站的列车随即把光灌进隧道里。屏蔽门和车门同时打开,如同边境长官查验护照结束的瞬间,我被允许继续剩余的路径。踏入列车,告别了稳固的混凝土月台,取而代之的是能将我送往既定目的地的大型现代工业产品。我如一颗滚动的磁铁,那些箭头、文字、轨迹、标线可供我吸附,又将我释放,好让我寻找下一个可以吸附的目标。
接过凯末尔相关的记忆后,我从塔克西姆广场出发向西北方走去,经过一些无人的破败街道,随后下坡,想找一个地图上标示的希腊正教会教堂。教堂在马路对面,但似乎没有地方能让我穿过马路,不要命的当地人趁着没车的间隙闯过去,我没有心思冒这样的险。彼时夜幕低垂,而路灯还没有开始工作,对面的教堂昏暗得像个废墟。因此,过马路的念头被打消,我决定按原路返回塔克西姆广场。我过于相信自己的方向感而没有使用地图,但明显无法在半黑又雷同的肮脏街道中找回我来时的路,便开始随心所欲地走。
清真寺门前的小广场上,有数个穆斯林男孩骑着滑板车,橘色的灯光仅能照到广场的一半。这一半和没有光的一半之间泾渭分明,就像那些纪念碑尝试通过规训记忆来划清的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生与死的界线。这个街区阴暗又污秽,路边烤肉店的店员一点都不像我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看到的那些烤肉店店员,后者恨不得要把我抬进他的店里。我抬头一看,是叙利亚菜。那个店员坐在钨丝灯下,面前是一些不知道有没有烤熟的但是发黑的肉。我继续走,蔬果店的老板准备打烊,他站在街边,一边收拾,一边转过头来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或者是不速之客脖子上挂的相机。野狗从我身边经过,似乎它们也有既定的目的地,不像我一样随便闯进他者的空间。
回到旅馆后,我上网查到这个空间名叫塔拉巴西(Tarlabaşı)——「伊斯坦堡最危险的地方」,「伊斯坦堡的贫民窟」,「抢劫、杀人、贩毒、纵火」,「五岁孩子能拿着刀到处跑」,「你进来了,你不舒服,住在这里的库尔德人也不舒服」。似乎我从塔克西姆广场往西北走便是非法越境——游客区和非游客区,安全区与非安全区之间的边境,跨越者后果自负。而我的确这么做了,那一个多小时里的我得以不受规训。
从伊斯坦堡往新德里的飞机上,我低头看书。飞机缓慢地靠近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边境的交点,舷窗外诡异的光线让人无法分清白天还是黑夜——分清了又何妨。我因此拒斥了一切可以提示我时间流逝之物,不再看手表、手机、翼尖规律闪烁的灯光,允许书里字词尝试建构的现象在脑海中成为真正的现象,纵使这些现象不合逻辑,不按时间排列,甚至不合道德。
那本书是鄂兰写的,但我没有读进去。她试图让我和我的同代人知道,人类处在困境中。她没有提供任何的工具好让我面对困境,而仅仅是描述了那个困境的轮廓。这个轮廓的内容很清晰,稍微了解过历史的人就会知道她想说的是二战、现代性和道德虚无主义。但她所构建的空间就像布班一样,鲜明的形状下潜藏着模糊的边境,没有提供实证主义喜悦的光明,也不知道边境之外有什么具体的危险。
我站在布班的三个拳头下做了什么?我直面他们,也仅能直面他们。我尝试寻找这些在布班终止存在的个体的蛛丝马迹,但是只有三个拳头,三个被笨拙的混凝土块代表的群体。他们是谁?她和他是谁?我在寻找的同时,也是在记忆;我在记忆的同时,也是在遗忘,毕竟记忆永远伴随着遗忘。所以,当人说「我是我所记得的」(I am what I remember)时,人也是其所遗忘的。
时隔半年,我在2023年11月21日再次开始写作,完成了上面的这些内容。我已经快走到了这一岁的边境。走过这条边境之后,我会不会还是走过这条边境之前的自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必须走过去。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