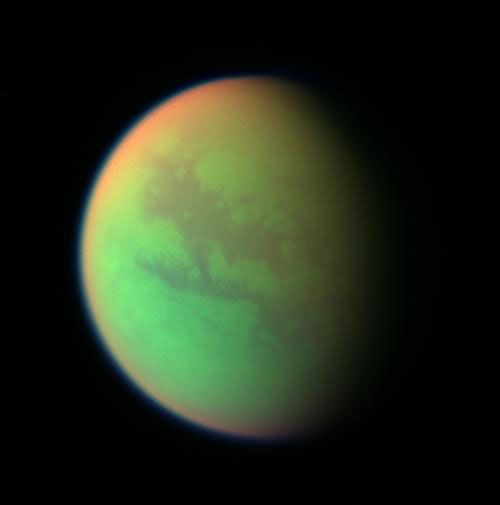
Volo ut sis.
在海上
12月22日早上9点10分,我登上尼什快运公司的巴士,由尼什前往贝尔格勒。这一段250公里的路程需要3小时。巴士驶出那个看起来如同城乡结合部的塞尔维亚第三大城市,苍白的阳光与尚未消散的雾气加上路边栽种的叶子掉光的树,毫无看点的窗外景象孵化着车厢内乘客的睡意——所有人都无意识地把命运交给那个清醒的戴着墨镜的司机。我从未乘坐过如此安静的巴士。在通过几个路口和回旋处后,巴士驶上了高速公路。坐在走道对面的男士穿着臃肿的黑色羽绒服,金色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睡眼。
窗外是毫无变化的南斯拉夫土色原野,偶尔冒出来一些英语和塞语的旅馆广告牌或者被拆除掉一半的平房废墟。在这样的移动过程里,我与现实的接触似乎只有那条轮胎与地面之间无限延长的切线,我不在尼什,也还没在贝尔格勒,我处于一个不处于任何地方的地方。车厢一如既往地安静,尽管巴士已经驶离高速,准备停靠在第一个中途站。我无法控制车辆的方向,无法阻止景色的划过,也无法忽略这些景色与经验在我的记忆里迟早会分崩离析的这一事实——所有的事物都被迫向前。早晨,我去巴士站前获知一位朋友的死讯;彼时,巴士暂时停在一个名为阿莱克西纳茨的城镇边缘的车站,我倚靠着车窗泣不成声。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于30分钟后抵达伊斯坦堡的萨比哈·格克琴机场,天气良好……」把我吵醒的不是机长广播,是和我隔座的女士以及走道对面第一个座位的男士之间的聊天声。廉价航空的座椅没有枕头,无法为我患有颈椎病的脖子提供足够的支撑,被吵醒的我发现自己在保加利亚上空睡到落枕。虽然我坐在第一排的靠窗座位,活动空间充足,但不可避免地夹在他们的对话中间。我完全无法理解漂浮在机舱里的那些词句,两位乘务员随后也加入了他们的闲谈,并免费送给两人其他人需要付费的三明治——我大概知晓这位女士和男士是休班的乘务员。
我从贝尔格勒回到了伊斯坦堡,准备次日经新德里前往曼谷。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堡的小亚细亚。我乘坐地铁前往小亚细亚的最西端,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于斯屈达尔(Üsküdar)。这里的海边能看见被围蔽施工的少女塔和欧洲部分的清真寺——要么是一整个的建筑,要么就是若干尖塔。城市史的教授曾说过城市内部的塔和权力息息相关。在酒店放好行李后,我在菜市场附近的食堂用餐,点了番茄沙拉、羊肉汤、土豆炖牛肉和米饭。吃完出来,太阳还没落下,我走到码头,买了一瓶4里拉的水,靠在栏杆上一口气喝完。挂着俄罗斯国旗的货轮自由地穿越海峡,海风把我的啜泣声和面包圈小贩的叫卖声一并淹没。
一周前的某日早晨,我坐地铁来到了同样位于小亚细亚的卡德柯伊(Kadıköy),准备乘船到伊斯坦堡王子群岛中的最大岛,比于卡达岛(Büyükada)。这里分布着几家不同的客轮公司,招牌上把「比于卡达」写得最大的公司今天不营业,门卫指着让乘客到远处的大码头乘船。我在大码头门口,问一位戴着耳机的女孩这里是否能乘船到比于卡达,她回答说是,但会在王子群岛中的其它岛屿处短暂停靠,比于卡达则是终点站。入闸后,我面前坐着一位比我稍年轻些的男孩,手里捧着一本土耳其的《孤独星球》。我仅能从他的肤色和眉眼判断他来自此地的更西边,也就是欧洲,而不可能是其他方向。上船的人很多,但只有少数观光客会到上层甲板去,本地人往往选择温暖的船舱内部。船往东南方驶去,兜售面包圈的小贩也来到了上层甲板,乘客购买面包圈来喂那些追逐着船的海鸥。
在伊斯坦堡第二次乘船是观光式的「90分钟环游博斯普鲁斯」。船从欧洲部分的艾米诺努(Eminönü)离开金角湾,沿着海峡行驶到7月15日烈士大桥(旧称博斯普鲁斯大桥),然后原路折返。那天天气并不好,雨在海风的干扰下落得歪歪斜斜,然后如一个个白点撞入我的瞳孔,眼前的景象泛起涟漪。海浪声、发动机声和乘客的谈话声顺势冲洗掉这片海上发生的事情。
那艘前往比于卡达的船离小亚细亚越来越远。我放下了相机,看着远方逐渐萎缩成一个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往下看,则是被螺旋桨搅成白色的海水,泛着油斑。只有远离陆地的细节的干扰之后,我才得以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在船或飞机上写东西。人被迫陷入一种自找的乏味里,要么是海水一成不变的蓝色,要么是黑白相间的雪原——细节无法辨认,思绪便被迫暴露无遗。我倚靠在机舱壁,耳塞顽强抵御着前来侵犯我耳膜的声波。看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架飞机的目的地不是机腹之下的西伯利亚。机舱的灯光被调暗,所有的乘客不得不屈服于睡意,他们仅在乎时间过去了多少,而无意了解现在几点。只有飞机翼尖有规律闪烁着的灯提醒着他们并未摆脱时间的控制,一切都在有规律地流逝,每个人都会在降落的时候年长一点点。
从比于卡达回到艾米诺努后的那个晚上下起小雨,我随便找了一家餐厅。用餐完毕,餐厅经理拉法埃尔招呼我到室外吸食水烟。水烟只能在室外吸。烟雾从我的鼻子和嘴里喷出,但它没有模糊我的意识。尼古丁反而让一些意识更加清晰可辨。拉法埃尔一边招徕路过的行人,一边问我「还好吗,我的朋友」。我一手托着腮,一手握着烟管,看着被拉法埃尔招揽失败的路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的眼神里或许带有一些惊奇——那是个第一次吸食水烟的东亚人,他快不行了。这些人在移动。我想起来我这些天在伊斯坦堡每日行走20公里,和他们一样也是在移动。在陆地上移动,万物于我而言只有移动,因为我总能找到参照物;而脱离了陆地移动,我能感受到自己的静止,意识安静地在脑脊液中流淌,并最终付诸笔端。
前段时间,奶奶因为掉进河里而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但好在没几天就回到了普通病房。她患老年痴呆,不能认出我来,但语言和行动能力并未受损。简而言之,用父亲的话讲,「她像个孩子」:总是充满了行动欲,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认识周围的人。父亲无奈地和她说:「那么多家里人来看你,你怎么总是说没人和你聊天呢?」
拉法埃尔带着账单来和我道谢;我也与那个在码头的戴耳机的姑娘道谢;我与奶奶握手,再次让她记住我的名字;我与那位看《孤独星球》的年轻男子挥手,彼此的眼神里似乎透露出了某种共识:「都是来独自旅行的吧」。我又来到了伊斯坦堡新机场,往登机口的方向远眺,能看见黑海,但看不见黑海另一端发生的战事。海水把两端陆地上人民的命运抚平,如同高空看见的那些单一的陆地纹理。我只是在他们有限的时间里很短暂地出现了一会儿,随后便要回归他处。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