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無中誕生︰探索文學邊界。香港文學館經營網上發表平台「虛詞」、實體紙本月刊《無形》。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由一群香港作家及學者組成,並設立香港文學生活館。常與大學、藝術單位合作,策劃各種文藝活動及展覽。 linktr.ee/houseofhklit
【无形.像西西这样的一个女子】怎么可以这样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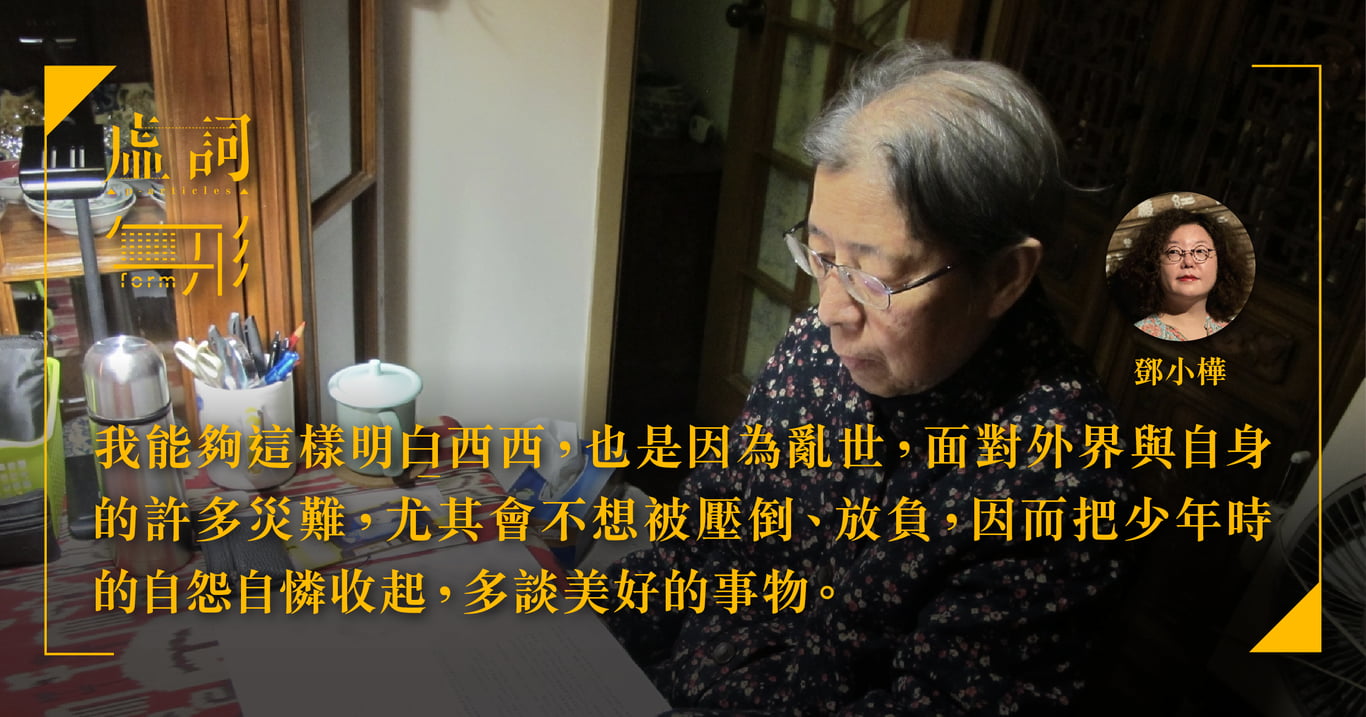
文| 邓小桦
对于西西的作品阅读,有些部分是需要时间的展开才能深入理解——不是指花在阅读时间上的,而是指需要读者自己生命的进程走到某处,才能真正理解到其中的价值。换一个说法是,事非经过不知难。而西西那么随和亲切贴近我们,让我们有时忘了她其实是在引领我们超升。
我没有送过西西玩具,我已经缺乏玩乐好多年了,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以看《我的玩具》来代替玩乐——如果这全然只是一篇西西《我的玩具》的书评,我会大讲西西有多么好玩,那些玩具显得她多么富于童真、多么博学而又秉持万物平等的眼光,正如此书的所有评论者一样。但这是一篇悼文,某些西西文中本来隐晦的地方会此而特别显现。 《我的玩具》固然是妙趣横生天真可爱的一本书。但它有些轻描淡写的地方一直让我怵然而惊——那便是年老与病患、身体的障碍——这些在书中的比例非常低,只有几处淡然提起。首次是〈散步〉,写自己在公园晨运练云手觉得天旋地转,晕倒在石凳上,不知过了多久醒来,人来人往没人理她,她自行勉力回家,此后不敢去晨运;再后来右手失去知觉再也抬不起来。读到这处霍然而惊,这样的「街外经验」,对一个老人家而言多么惊险,颇可唤起许多惨情与怜悯;但西西笔锋一转,又乐滋滋去写她的玩具。
读西西,看她写出来的知识与门道已经丰富到消化不来,但还要看到她没有写出来的。散文一般被认为与作者真实个人非常接近的文类,但西西在她的散文里常常是相当隐身的,隐于她所陈述的现实细节与知识背后,负面情绪很少,永远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童,只是非常偶然地流露出一点半点的惊心动魄。 〈阿福〉中写她有一年夏天去日本旅行闲逛电器店:
「我一时顽皮,伸手去试血压机。一次,没有数目字出现,再试,仍是空白。连试几部,都失败了。售货员帮我量,然后脸色一沉,说,See a doctor。以为我不明白,再说一遍,See a doctor。我马上乖乖回到饭店,对大堂坐在旁边独立桌椅的经理说要看医生。原来这位经理会说普通话,懂中文,姓有马。他立刻陪我到几幢酒店外的公立医院就诊,并且做起翻译。量血压时又爆灯了。我带了药回酒店,翌日连忙购买机票提早回港。几年后,我再到日本看毛熊展,仍选新宿那酒店。」
引述原文,是想展示这个惊心动魄的血压暴走情节中,唯一涉及内心的形容是「顽皮」、「乖乖」,最多加上「连忙」,当是一个小孩顽皮闯祸受教训般的事来写,仿佛一切还是自己的责任。每当遇险,西西总是这样带过去,没有怨天尤人,半分不自怜,别说没有夸饰简直是摒绝内心化,背后是顺受天命之意——看来没有经营,实则是节制到成为自然流露。
西西深谙言简意骸,又常以孩童口气说出普世真理,诗文中具宗教高度的启示性笔法更是常见;但写及自己现实中「遇险」时,则极度节制,留在现实的层面中,节制了象征和推衍。像〈陀螺〉中写自己在桌上玩陀螺,「多年来我已成为左撇子,左手没有什么能量,陀螺总是转几圈,意思意思,然后倒下,然后静止。桌上陀螺,只能这样了。」这明明是右手残疾的后遗所致;倒下、静止,当可指涉死亡;陀螺更可以象征不由自主的生命。但西西把一切隐喻象征之流截断,回到最平实最基本的,「桌上陀螺,只能这样」。
这在文学手法大概没什么好分析的,但当一个人面对衰老病残,又有多少人能如此豁达?老去原是一个剥夺的过程,将你的形貌、身体、行动自由、能力一一拿走,一切是绝对的无可奈何。近年右手也不大举得起来,久治不愈,遂有明白。当面对这一切受限,你还是否能忍得住,不把自己比喻为一枚不由自主旋转且伤痕满身的陀螺?很多人都知道,西西是反浪漫主义的,她不感伤,连自己的遭遇她都不感伤。是我觉得自己做不到西西这样,才知道这有多么难。
《史记.留侯论》中论勇气:「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经过2019,我大概可以接近「卒然临之而不惊」,但「无故加之而不怒」还是经常做不到。但想想,「卒然临之」、「无故加之」,不也就是命运的挑战与灾难来临时的状态吗?西西的豁达其实是面对命运的大勇,置生死于度外。但因不想亲友担心,活着又有好玩的事,于是又好好活下去。
《我的玩具》中唯一一次比较强烈的负面情绪是〈熊出没〉中西西发现熊玩偶打理不善而吽出虫来,「都怪自己愚蠢,明知香港气候潮湿,又无能力维持一天廿四小时空调侍候,缝什么熊呀。」西西把万物当生物,又把自己置于万物之下。又有一篇写她坐着的温莎椅散架,让她整个人跌到地上:「我居然亳发无损。于是也原谅了椅子,应该是,彼此彼此,因为之前对它的形容失敬。」这里的拟人,是将物与自我齐平对待,寛容平等,当是自己得罪了椅子。 「拟人」这种修辞手法,原来还可以帮人消化自己遭遇的意外和危险。
「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因是已。[⋯⋯]
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
——《庄子.齐物论》
关于身体衰病之事,《花木栏》后记有流露病弱时的低沉,集中全面开展的有《哀悼乳房》,收在《白发阿娥的故事》中的〈解体〉更以前卫文体极写身体内部的争战与崩坏;其后,西西倒只写外在的、趣味的、善良的那些玩艺。我从小「老积」,偏好结构性强或沉重高远的文字,喜欢看死亡和疾病的书写,连童真都要进行分析,自然也有觉得西西作品太过轻快的时候。西西过世后我和洛枫小姐做过一个LIVE,她提到一直有人嫌西西作品太轻,到西西过世了之后还在嫌。的确我有见过,我以前也一度有微言。是到自己老了限制多,才知道西西如何举重若轻——她一直坚持着卡尔维诺的信条,继续往「轻」的高处提炼,同时举起了更多更多个人命运的重负。如果你觉得那轻是不合情理,其实要想到她举起的那重也是极致。
特别要提醒的是,西西的「轻」并非浮浅,相反是承载愈来愈多的知识内容。大概也有人要抱怨西西是太正面、正能量了。我是在与洛枫做LIVE时,突然明白这种正面倾向是一种知识份子及教育工作者的取向。西西博学读书多是众所周知,但知识份子不止是多读了书而已。吴念真常提起他童年时村口代写信的「条春伯」,觉得条春伯才是知识份子的代表。村子里的大老粗请条春伯代写信叫在外的大儿寄钱回家,本来是满口粗言的训骂,条春伯则将之改写温暖婉转关怀有礼之语,并向大老粗复述一次,问「是不是这样?」大老粗喜笑道:「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啦!」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要把人间的粗暴情绪与纷乱辗压,转换成能够普遍明白与接受的言语,勾现底层的善良,让世间往好的方向发展。愈是面对丛林般粗砺凶险的现实,愈要这样。至于教育者,则是面对比你更弱势更年轻的人,负起教育者的责任去为他们服务,那自身的EGO也自然缩小,好把自己放低一点。
我记得《字花》第一期,有西西的一篇短文〈熊艺〉(不知算是散文还是小说),前段写西西初学做熊的手艺细节,大概如日后多篇文章所见;特殊的是文末写一个与西西一起学做熊的女孩,一边用木棒塞棉花入毛熊肚子一边喃喃道「死了吧,死了吧」。文章就在这里结束,不吝可以发展成一部惊悚小说,又或用来抒发「世风日下现在的小孩好可怕」之类的老式言论;但西西没有这样做,这个短篇没有收在任何集子中;当时间和体力都有限,西西选择去做《缝熊志》,那么多个精致到超越想像的毛熊,细节承载着大量的历史考察知识与创意。举重若轻,是想把力气花在美好的地方,把美好给予更多的人,让世界再好一点。
我能够这样明白西西,也是因为乱世,面对外界与自身的许多灾难,尤其会不想被压倒、放负,因而把少年时的自怨自怜收起,多谈美好的事物。吴霭仪说过,希望是一种责任。如果是太平盛世,西西的游艺手作、晚年小说可能只是一些美好的消闲,储藏给人间日后细味;但当世界日日出现坏事、连自己身体都是灾难现场,我于焉明白了西西的美好之难、及难得。那不是压抑,不是隐埋,不是为了呃LIKE而只呈现美好一面,而是真正消化命运的巨大挑战,以自己快乐的方式超越其上,同时俯身亲近万物﹐所谓举重若轻。
鄧小樺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文學放得開》主持。著有詩集、散文集、訪問集。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