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廣播人,寫作者。
自由工作者的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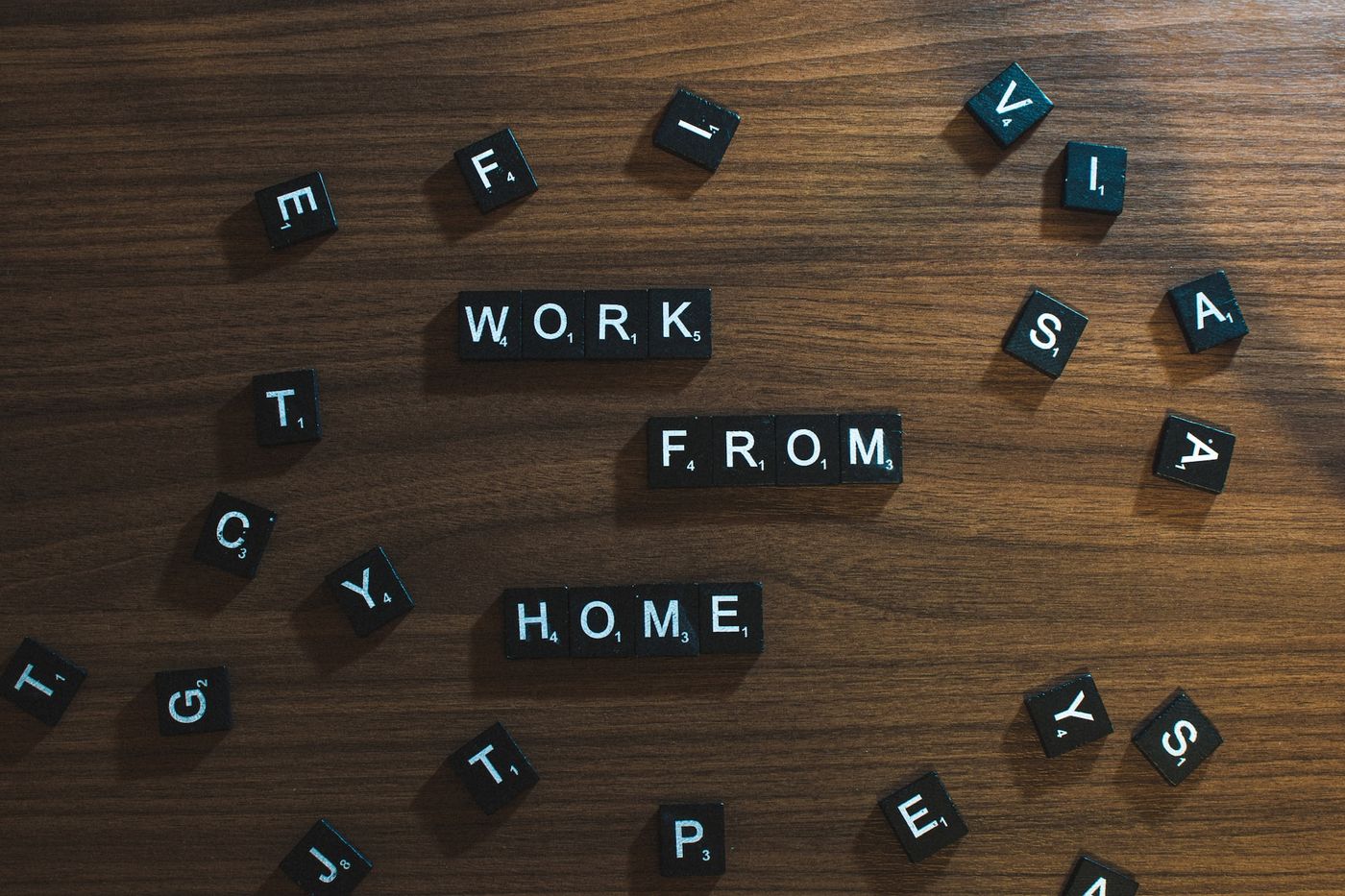
所谓自由工作者,简单讲,就是「不用上班」。不用上班,当然不表示不用工作。每天尖峰时段骑摩托车吸废气、挤公车捷运的上班族嫉妒地看着这些人,羡慕的是「自由」两个字。这些人自己呢,看到的永远是「工作」──有活可干,就是「自由工作者」。没活可干,就是无业游民了。
你若经历过长期的失业,尝过焦虑茫然的滋味,就知道无业游民一点都不浪漫。所谓「自由」是必须不为生计所苦,才有资格享用的。 「心无罣礙地浪掷时间」是天底下最最奢侈的事。其人若无雄厚俗世基础,便是已然得道开悟,我们多半都构不上边。
真正自由的「自由工作者」,几希。
自由工作者常常挣了这一顿,下一顿还没有着落。没有劳保,没有退休金,自然也没有组织赏赐的年休和奖金。想让日子滋润一点,就得多多接案接活。活接得多了,生活是一连串不断逼近的「死线」。人家上班出门、下班回家,你整天关在房间对着电脑拼命,晨昏颠倒,不辨历日。周末于我何有哉?
我的「自由工作者」人生,一眨眼快二十年了。我素来不是一个有纪律的人,偏偏一个专业自由工作者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纪律──若不能按表操课跟上进度,生活势必阵脚大乱,一塌糊涂。幸好我有个纪律严明的太太,无法忍受我的拖延症,时不时踹两脚,我「自由工作者」的事业才能勉强支持下来。
婚前,我经常半夜三四点上床,睡到中午。婚后,太太一早就要上班,我也跟着早睡早起,煮咖啡做早餐,总算每天都能见到早晨的阳光。 2020年疫情初起,太太的外商公司命令部门所有员工改成远距上班。她在书房摆起电脑桌,我们从此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她挂着耳机轮流和全世界不同时区的同事开会,我挂着耳机听音乐写稿。她若久没听到键盘喀喳喀喳的声音,就知道我又在上网胡混,因为这样,我似乎又变得更有纪律了一点。
我的工作,大抵可以分成「在家」和「出门」两种型态:在家写稿、审稿、审案、录音,出门开会、上课、讲演座谈,啊,还有看演出──是的,这也是我的工作。
讲演、座谈、表演,通常都安排在周末,我的周末也就经常是工作日。 「生意好」的时候,连续几个周末上工干活,常常还得跑外县市,根本没时间和太太一起过。若要争取两人相处的quality time,我们得找出周间她不用开会的空档,若是时间有限,就一起出门散散步,到外面吃一顿。若有大半天的时间,还可以去美术馆看个什么展,或者看一场电影。那样的时刻,大概就是我们的「周末」了。 「周间约会」好处很多:避开假日人潮,上馆子不用排队,路上不会塞车,到处都有停车位。
不过,我们两个都有空的时候,也常常待在家里哪里都不去,慢慢弄几个菜,一道一道吃。一面开一瓶酒,一面挑张我们都喜欢的唱片。酒足饭饱,懒在沙发上双双昏睡片刻,就是千金不换的太平日子了。
若是有朝一日真能心无罣礙地浪掷时间,我仍哪里都不想去。首先拔掉网路,搬出早该看完的那些书和早该听完的唱片,一本一本读,一张一张听。然后慢慢把房间收拾清爽,物件归置齐整。再接着重读以前读过的书、重听以前听过的唱片,只要食物和电力不虞匮乏,我可以几个月不出门......。
写到这里,你应该也发现了:我现在就可以实现那样的「自由梦」,只要把每天滑手机、上网瞎逛的时间匀出一些,工作状态更有纪律一点,我大可以化整为零,每天创造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刻」。所谓自由,其实触手可及。说穿了,都是意志力的问题。
(写给《小日子》)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