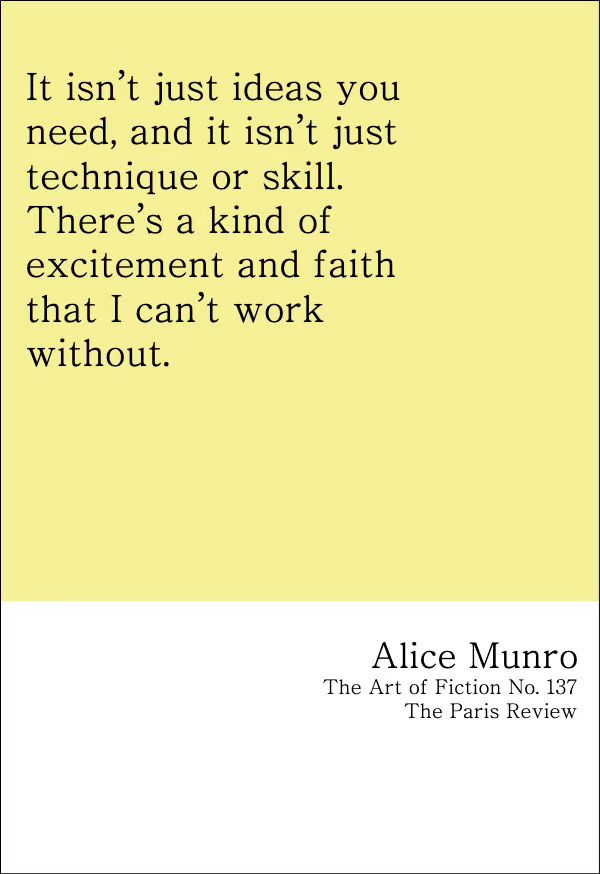我为什么要写作-1
工作上遇到的前辈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想做内容这个事情的?
我也很难答上来。我知道自己一直喜欢写作,但把本像浮萍一样轻飘飘的业余爱好摆放到“为生命创造价值”的位置,似乎是在来到三明治以后。
三明治成立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并接着度过了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初高中时代。生活在所谓的下沉市场,乡镇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QQ空间以外的博客和软件。到了2020年,它也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从一开始聚焦于30代中国青年人生活状态的非虚构写作媒体发展到现在,有了“短故事学院”“每日书”两个固定产品,发展各类写作、阅读、艺术课程和周边产品,也积累了一群固定且忠实的写作者。
非虚构的概念其实是个舶来品,和上世纪中国的“报告文学”相比,除了服务目标和调性的不同,也存在注重细节、写实等共同点。在21世纪初,纸媒仍然火热,记者仍是收入蛮高的体面职业,《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南方周末》也曾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记者,他们成为了现在大批非虚构写作者的前辈。
前《南方周末》记者、知名特稿作者叶伟民在采访里说过,他在南方周末时,仅一个特稿版面的差旅费和稿费总和,就接近2万元,而一个特稿记者的长成(平均以5年计),背后机构所支付的成本将是百万元级别。
曾经报社的光辉岁月不复,纸媒的衰弱是令所有传统媒体人嗟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些记者选择去高校读书,另一些则出走传统报社,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或新媒体。这就有了前《时尚先生》总编李海鹏带队的“ONE实验室”、界面旗下的正午故事、魔笛、真实故事计划,隶属大媒体的《GQ》和《人物》也紧随其上。
非虚构写作的热度由ONE实验室《太平洋逃杀》百万高价的版权出售开始,最擅长追逐风口的资本热钱纷纷涌入。但随着类似咪蒙这样篇篇百万加的营销文热起,资本们嗅到了更香的饽饽,才发现一只专业(且相对更昂贵)的特稿团队虽能产出优质内容,却不带来流量,而《太平洋逃杀》似乎更像是一个偶然,无法批量化复制。
除了背拥时尚资源的《GQ》或聚焦自带流量的娱乐圈的团队,其他非虚构写作团队则需要通过媒体广告和活动营销解渴。比如前《冰点》团队张伟创办的新世相,以爆款活动出圈,以知识付费和品牌合作变现。还有一系列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大公司子团队,如网易的人间工作室、搜狐的极昼工作室、更偏公益性质的腾讯的谷雨实验室及故事硬核,它们更像是非虚构编辑部,而并没有精干稳定的记者团队。
始终有一批人在坚持写好东西,无论环境多么困顿。在图像和视频泛滥的时代,他们珍视文字和故事的价值,重视文字架构的叙事空间和张力、逻辑清晰讲究节奏的纯文本,在意信息的质量和导致的后果。乱七八糟的商业电影环境中,总有导演在坚持着做好作品; 那些好故事也像伟大的电影一般,告诉人们在荒唐的价值观体系里,如何体面地活着。
我们反复询问着,反复思考着: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能这同一时空下不同的生存状态,被更多人看见?如何能让这些截然不同的人性互相映衬,为这世界的合订本增添一页?
没有一个严肃的媒体或平台会声称:我们没有价值观,如果有的话,那它一定是在企图用“没有”掩盖其价值观的丑恶。数字、代码本身是中立的,但背后的逻辑和目的却是人所控制的。我们生活在充斥着碎片化信息的时代,视频、短文本、广告,它们被包装成与每个人相关,而真实目的只是娱乐。娱乐是顺应人类天性的,在基于点赞、转发、竞价排名的竞争机制中,它对人类时间的侵蚀被进一步放大,把任何具有反思、逻辑、说理的内容狠狠踩在脚下。(教育娱乐化,大多只是给娱乐戴上“教育”的帽子,让它更好听)
而对文本的坚持,是对连贯信息的坚持,是对阐释、讨论、说理、思考的坚持。认可花大量时间去做的事情,读书、写字、运动、思考,我们都可以对自己有一些更高的要求。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边娱乐一边收获的。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把写作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回复到嘈杂的尘世生活中,我仍然需要去处理和面对各种各样我“不得不”做的事情:上讨厌的课、聚令人不自在的餐、做无意义的工作。这或许是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中不得不面对现实:每天的生活就是如汪洋一般的各种要求,所有人都教育我们去遵从时间规范,我们每天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却可以花上三个小时刷手机。
所以能在周五上午开完无聊的会议后,花上一点时间整理读书笔记,并在这里写下点什么,或许已经是我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联结与共鸣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