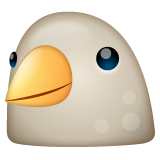身体的夺还——《死亡诗社》影评
夺还,一个和制汉语, 【奪還する.奪い返す】【彼は他人に奪われた物を奪い返した】 其意为 “把东西从一个人(非那东西本来的持有者)的手里夺回来后还给那东西的本来持有者”。我认为这句话可以非常精准概括影片的核心冲突与主旨。即作为干预实验存在的,Kenting所做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围绕着把激情和冲动这一被唯一的绝对社会结构所压制的身体个性的夺回。
相对很多短评所强调的无限制的自由或者其他,我认为是不那么准确的,最近正好在读Beck的《个体化》,个因为我们可以明显从Neil以及Todd等人或刚性或柔性的对抗或抵抗中感受到,与其说是反抗一种制度化的暴政,他们反抗的是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心智,这种社会期望压制他们寻求自己声音和灵感的可能性,并以一种威权体制(当时的美国确实如此)和父权家庭的方式压制子辈的成长——他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本身被当成了生产资料并被导向了家庭再生产的路径,这也和当时美国梦息息相关——一个反映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与社会期望的模范人生。因此,Beck提到的individualization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解释路径(虽然这是被称为制度化的个体化,当时的时代是个体化前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要更晚一些,或许用个性化更为合适,但不管怎样,就如同Beck在文章中所述的与主观个体化、市场个体以及心理学家的个性化间难分难舍的关系,在描述50年代的情况时总会遇到难以那么准确的问题)。
影片在开头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情境,1959年的美国,悠久历史成果丰硕的私立男子封闭式预科。与父辈们一同出席的学生,排排聆听委员讲述这所学院的成绩——极高的藤校录取率,它意味着他们即将也必须成为其中优秀的一员和社会的栋梁,这是来自家庭的期许和学校的使命:学校是家庭期望的承担者并负责把学生教育成家长们所期待的那种栋梁之材。在这里学生作为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被隐形了,他们被期望成为他们的前辈一样的优秀人才,而不是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或者说这种健全的评价体系是他们能否被藤校录取并在进入社会后取得一样的声望,在这里评价体系被交给了权威,这个权威来自于公权力、市场和社会,而不是个体和家庭(因为家庭也只是一个细胞而已)。非常简单的例子,Todd在和教委握手的时,教委对他的期许不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像你的兄长一样优秀的人,优秀在这里以一个单一且权威的标准出现。而之后寝室里Neil与其父亲的对话则更为明显,他只需要把时间花费在那些卓有成效的事情上——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那代表他站在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高点,并即将在经济资本上也占有优势地位,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从他父亲所说的家庭厚望中可得知,Neil被视为稳固甚至是升格的重要一环——他是这个家庭的生产力而在这个小生产组织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他的父亲,因为所有的对话都掌握在其手中;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意到这场对话发生的场所,寝室,这是一个共有空间,而他的父亲依旧要宣誓他对Neil的支配地位;同时,Neil对其时间、空间的支配不被允许有自主的成分——因为被限定在模范生活的内容之内,而且他也没有认识到自发和自觉的区别,编辑校志只是对模式生活的一种逃离而非是抵抗——后者涉及一种参杂情绪的主观选择。至于Todd的僵尸形容,则是一种去意识化的身体的戏谑形容——了无生气,这种生气的消失尤其体现在他缺乏情感与情感的表达,后者则言及他语言功能的丧失——他不擅长或者说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内容,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身体意识分裂的回击,因为意识的表达需要借助身体,用手去写用嘴去说;同时这种失语也代表着他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他不需要表达或者不能表达,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他的话语没有或缺少反馈,以及没有表达的权利或者是总是被拒绝的情境下。至于这所学校,它体现的是一种客制化的产物, customization ,学校根据家长/家庭的需求对学生进行改造,生产出符合交纳高昂学费的人力资源商品;它代表的不是一种个性化定制,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需求,它对应的是一种生产行为,因为它不追求学生自我的发展,而是用一定的教学方法批量打造优秀学生,以藤校为目的而不考虑更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对学生不构成消费,但对家长来说,它确实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它代表的不是一种教学体制,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制度化的产物,而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反映的是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互动,所以将矛头指向教育体制是不准确的,而是投入与产出的机械功用主义,追求效率与再生产。
Kenting老师所做的就是对这样一种追求效益的僵化观念的回击,他撕去以效率和量化的机械方式评判诗歌的前言,略过追求真实与摹仿的现实主义诗歌(当然,只是跳过而不是撕去说明了这是Kenting有意识的选择而不能推断出他对现实主义手法的批判),选择了最能激发情感与冲动的浪漫主义与战后文学,前者涉及对启蒙运动的反应,而后者则涉及对机械理性和权威的批评,前者把神圣和世俗区分、把人拉回到目的,而后者则从切身感受出发感受世界,驱逐机械理性和均质这一对启蒙的误读,驱逐对普世价值的一元论解读并呼唤多元主义。Kenting老师的意旨与其说是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倒不如说是让他们以人的姿态生存,因为全片的几处冲突并不完全只涉及到他们对某些事件的批判——一种思考方式的重建,恰恰相反,里面的所有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想法,虽然很朴素,但这种想法始终没有得到表达或者说在他们心里泛起涟漪——生成情感与冲动,而这正是身体的能力。为了让一具僵尸起死回生,Kenting老师所做的一切,包括缅怀前人、写诗、站上讲台、步伐节奏、足球赛与诗篇赏析等,都是试图还原学生们麻木的各个器官:跳动的心、言说的嘴、灵动的脑、直视的眼。
在前人照片前,Kenting老师先教会学生全片的经典名言“seize the moment”,与其说是存在主义,倒不如说先带领学生认识死亡,只有正确认识死亡,人们才能更好生存,而不是成为模糊的生产的人或者是永生的神圣的人,人们首先是要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他人以及神圣信仰,而那些照片里的人曾经也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成为校园品牌资产的一部分。这种还原是Kenting老师的第一课,也是全片的第一课。在之后的诗歌课程里,他教导学生不能仅以权威话语评价诗歌,而是要融合自己的切身感受,他不断用大喊、野外观察、户外运动等调动学生的感官,其中激发Todd创作灵感的片段最为动人:Todd在Kenting的激励下,从小声嘟囔一直到大声地叫喊出来,他在Kenting的引导下从眼前现象的描述一直延伸到内心感受的表达,同学们都为原本如僵尸一般唯唯诺诺不善言辞的他喝彩。叫喊,是唤回身体的表达与冲动——身体除了能够表达之外,它本身也是一种表达;而遮上眼睛,则是从现象到感觉。我们可以想象Todd的言语功能是如何“被设限”的,他的哥哥一直是他不得不学习的榜样,在这之前的任何表达都是被“取消”的;而在这所校园里,Kenting和他的伙伴们给了他准许表达与获得反馈的可能。站上讲台则有双重意味,视角的转换除了拓展,更有替换——来自地位,因为讲台与课桌往往是一个单向的传递过程,它除了物理的高度,还有一个权力的高度——取消权威。至于步伐节奏,除了不要盲从之外,还有保持自我的节奏。这一系列最终促成了最后一幕煽情意图最强的画面:最怯弱的Todd看着离去的Kenting老师发出了最热诚的呐喊,并且站上了自己的课桌——一如之前所述,它在纪念的同时,也是以身体发出学生个体的声音。
本片其实是非常成功的群像作品,它以死亡诗社为线索,但并不着重描绘“死亡诗社”本身——死亡诗社从复建伊始就和Kenting的“死亡诗社”有显著不同,它们只在冰山之下拥有相似的精神内核,复刻流程但拥有崭新的滚烫内容,因为成员都是崭新的,他们拥有崭新的个性内容,在爱、性、烟草和酒精等越轨元素的冲击下,他们也进入了一个失范但有可能的世界,当然这也和他们之后的成长轨迹相同。影片着重描绘了四位人物的成长,打破门户及伦理限制、勇敢求爱的Knox,重情重义反抗权威与主流文化的Charlie,夺回言语和表达能力的Todd,以及作为带来全片最强戏剧冲突、努力追寻内心真实想法并付诸行动的Neil。他们四个人都从不同的方面夺回了身体,这种个体化或者说个性化是以情感与欲望的滋生与表达为基础,因为这些在所有者看来是多余而无谓的,且影响到了他们以高效的机械精神投入到生产/学习活动之中。这一矛盾就在于,让身体焕发生机的意识对个体的家长们是无关痛痒甚至是有害无益的,而其核心就在于身体,不仅是因为机能,更是因为他们置身在这个场域里,他们的身体被视为家长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而Kenting的所做就是焕发其精神,逐渐夺回其身体——身体应当与其意识同行。在这场夺还战中,最激烈最彻底就非Neil莫属。
有一种争论在于Neil的自杀是否是有必要的,有些人认为是盲目自由的后果,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批驳;有些人认为是剧情需求,这一点不完全是,因为它过分强调编剧意志和观众面向,但实际上究其行事逻辑,Neil的自杀恰好是其人物主动所为,并且是其成为独立个体的标志——他选择饮弹自尽恰好是在完全意识到身体的无力的基础上为夺回身体做出的最后也最彻底的抵抗。Neil的自我觉知其实最为深刻,因为他的冲突在于生涯的分歧——中产期待下的哈佛商学院与自我觉知的艺术人生,这点深刻体现了作为再生产的身体与个体选择下的职业道路之间的冲突。Neil的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从最开始懵懵中接受父亲的安排,到接受Kenting的教导后出于逆反心理自发组织重建“死亡诗社”,再到逐渐发现自己的特长与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自觉报名参加剧团选拔,甚至在Kenting的支持下主动和父亲进行公开交流——试图在嵌于国家的家庭中和父权沟通以争取未来的自主选择,但最后我们都知道他的沟通失败了,他的自主道路被无情扼杀,甚至被父辈计划送入完全消灭个体的军事学校以实现生产机器。此时,他的家庭中只有生产/支配者(父亲),以及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再生产的母亲(为家庭牺牲)和儿子(满足家庭期许),三口之家只有一种性别、一个大脑和一个声音。
Neil选择自杀的场所也极具代表性,他选择的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在雪地中死去,而是把代表他自由意志的精灵草帽放在卧室的窗前,来到在代表中产阶级家庭理想与父权意识形态的空间“书房”用父亲的手枪饮弹自尽。虽然很多人讨论这部片里没有女性,但这并不代表影片放弃对父权制的批判,Neil的自杀是五十年代威权体制和父权制鼎盛的年代下,个体挣扎寻求出路的缩影,女性被隐形、被牺牲、被扁平化,子辈被当成再生产的工具,而在书房里的一颗子弹——这里我可能要再多分析一下,因为书房本身不作为生产力的空间,它的存在更多是象征一个家庭有条件可以设置一个用于脑力劳动、展现文化资本、接待社会资本或者什么都不做的炫耀性消费的场所,而这种场所往往是男性、父辈主导的,因为它涉及到当时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群体以及家庭中的当权者;因而这颗子弹射入的不仅是Neil的身体,也是对父权制的一枪。Neil借由这颗子弹,也完成了对身体的完全支配,这种支配是建立在柔性抵抗、公开协商均无所作为的基础上,弱者所能做出的最后的消极的“积极”抵抗——你不可能指望他弑父,因为弑父并不意味着他夺回自己的身体相反这具身体又要以另一种形式为国家和社会所支配,他也没有因前路无光丧失理智从而失去对身体的控制。相反,Neil的自杀是完全个人意志下的支配身体的行为,他支配了自己最为根本的生命并选择放弃以生产资料的物化方式生存,从而在失去生命的那一刻起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的有血有肉的自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