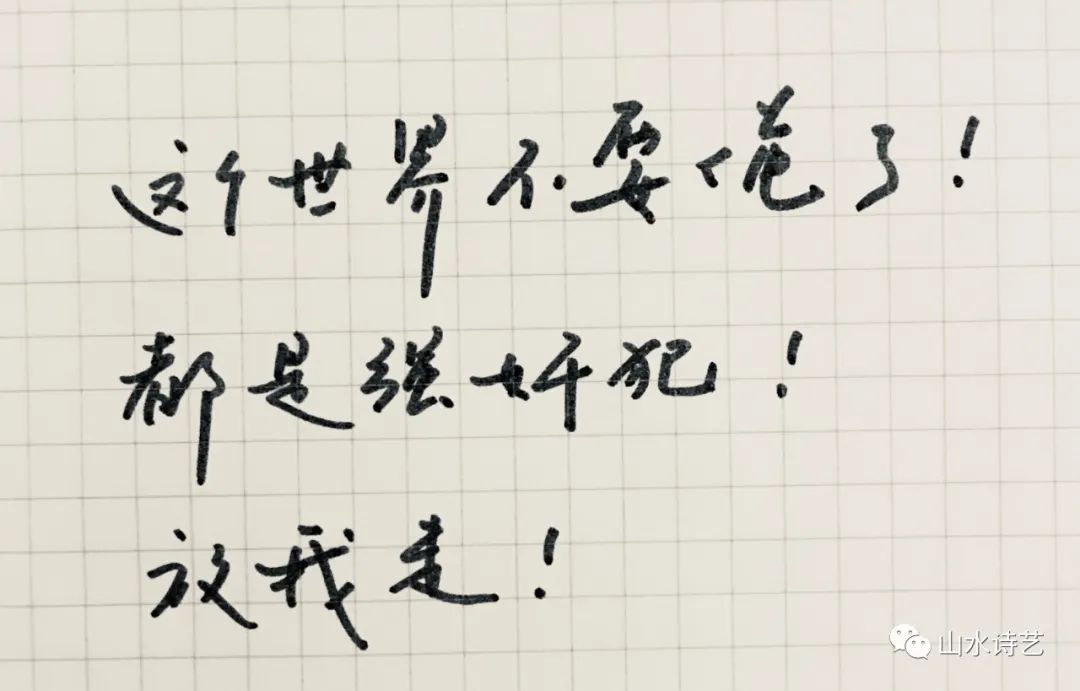与安妮∙厄诺(Annie Ernaux)诺贝尔文学奖讲座的共鸣
周琰
大概十多年前,我读过安妮∙厄诺(Annie Ernaux)的三本小说,当时我觉得她写得好,标记了最高分,而后我忘了她。前一段时间在《巴黎评论》上又读了一点她,还是觉得特别好。昨晚和今天起来,我读了她的诺贝尔文学奖讲座: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2/ernaux/lecture/
这篇讲座中文已有翻译,就像一个朋友说的,觉得翻译的标题是不恰当的,‘I will write to avenge my people, j’écrirai pour venger ma race’,不是“报仇”,而是“为我的族类复仇”,在字字句句中为我的族类寻求正义。
刚好昨天做饭时还听了一个播客,邀请了两位嘉宾谈论安妮∙厄诺。其中一位批评了国内媒体报道渲染安妮∙厄诺工人阶级的出生,是小镇做题家发迹正能量心理的体现,指出安妮∙厄诺父母开咖啡馆,而她一路上的好学校,实际上不是国内想象中的劳动阶级,而是小资阶级,安妮∙厄诺坚持的劳动阶层和我的族类的叙述更多是文化上的阶层不平等感。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却弱化了文化阶层不平等带给安妮∙厄诺和她的族类巨大的痛楚和义愤。这一点,也正是布迪厄一生所坚持言说的。
安妮∙厄诺感受的她与她的族类因为语言和文化而形成的巨大区隔,也是我的。她因此而确立的终生的研究和写作的信仰,也是我的。在阅读她的演讲的时候,我的家庭我的族类也在她的文字中浮现出来,带着痛带着眼泪,但全然在他们自身的沉默中,却在安妮∙厄诺和其他同类的文字中默默出声。
我父母两边的家庭自19世纪以来,四代人,是文化和生命无法安居的人。我父亲家族是南方的书香世家,但是在历史的动荡中,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文化的从容,那种真正的文化特权。父亲一代人,从少年起,无论文化和生命的立身,都是脆弱、破碎的,虽然内里沿袭了一些深深根植的文化和道德信仰。他们在社会中曾被连根拔起,从小我就能感觉到他们一代那种岌岌可危的不安全、无依无靠的感觉。在文化上,他们也变得无产,失去了可以思考、愉悦和保存自我的整体文化,人当然也是破碎不堪的。
我母亲那边的家庭,一半也是读书人世家,但是早已随着20世纪衰败,到苟活亦不能够的地步。我的姥姥是个牧羊人的女儿。只在解放后学文化的识字班学习过,同样的情况还有我的婆婆——我爱人的母亲,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母亲和弟妹们,年轻时没有机会按照他们的梦想学习读书,他们以其他的方式填补这永远的剥夺。
还有我的朋友、邻居、街坊,许许多多和我性命相关的人,他们就和安妮∙厄诺的父母,和她的族类一样,被语言和文化剥夺、侵犯、欺骗。我所有的爱和痛,我所有的力量和获得,最初和首先,最核心和最强大也是最柔软的部分,都是来自于他们。这其中没有丝毫的自我欺骗、浪漫,而是我之为人的根本。
安妮∙厄诺说她的写作位于社会和女权主义的范畴内——YES!如果不是从这样的一个范畴出发,她的族类、我的族类就找不到痛点和反抗的支点。安妮∙厄诺说她的写作中的 “我” 和那种自恋的我没有丝毫关系,而是一种彻底透明的、中性的,我与我的族类与共的、读者和他者可以取用的 “我” ——YES!这也就是我自己。长期以来,我常常看到一些我觉得非常做作的、文青的、小资的姿态: “我很私密”、 “我很隐私”、 “我要善于不显露自己而彰显自己” ——我觉得这其中是赤裸裸的虚伪和自恋。任何一个我,本来就是赤裸裸的平凡,微不足道而意义非凡。每个人的私密的尊严都是不可穿透的。而每个人的真性、真情和创造性的奉献,并非都是我的私产,而是本来就属于世界,属于我的族类的,有何遮掩、修饰、伪装之必要?我觉得这是智慧和伦理上的不诚实或者不彻底。
与安妮∙厄诺的共鸣带给我巨大的欣慰感。道不孤是巨大的力场。
2022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