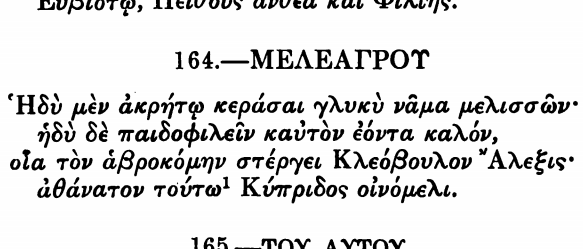一些非虛構&半虛構隨筆片段

人們總是很難在人生被徹底改變的當時,意識到自己已經永遠不會踏上某條道路。
三島由紀夫還是初中生的時候,憧憬著等到從有不能留長髮的機掰校則的學校畢業之後,就要留一頭長髮。後來情況一年年坏下去,法西斯自取滅亡,三島成了名滿天下的作家,又戲劇性地自殺身亡,只是後來他再沒有以板寸之外的髮型示人。
我來到這所學校后,感到最驚詫的一點,還是穆斯林,即舊稱的回教徒,以及回教相關人士中,喜歡三島的比例實在是高。
我和一位姓上田的穆斯林女生熟悉。上田本名當然不是如此,稱其上田是因爲其人曾經指責借新型冠狀病毒之機會跟風辱駡不宅家人士的學生只知尋安全時機人云亦云,奴性未除。我高中溫習古文時讀過上田秋成筆下的人物執意治療疫病之人,曰不該死之人自不會染病,便認爲這位同學有上田的氣質,如此稱呼。
有一次去教室去得早了,上田和另外一個女生去得更早。我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一邊放書包掏出書和筆記本一邊聽她們聊天。上田說學生運動時,學校一個自殺的學生的遺詩集終於出版了,打算買來讀。我有點在意,但不太好意思搭話問名字。如果我自殺了大概不會有人記得我,雖然我也是現代詩人。校園一隅有一座小小的墳墓,説是爲了紀念在這讀書時被軍國主義政府殺害的年輕詩人,或許人只有運氣好,或是殺害其的事物數年後運氣不佳變爲千夫所指,才會成爲某種程度上“英年早逝的詩人“吧。
一個已經絕交的朋友有次晚上忽然發來消息問我人是爲了什麽而活著,我回覆她說爲了神的正義。她加入了批鬥方方大軍之後我就刪除拉黑了此人,雖然主要原因是發現她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交際圈互不干涉,一個伴侶膩了換新的的速度比換乘地鐵還快且每一個都對她死心塌地,感到有點可怕。想起斯特林堡小説中的女人。我有時確實會發表性別歧視言論,這很不好。
我害怕我的祖國有一天變成一個侵略成性,瘋狂邪惡的國家。依稀記得芥川龍之介的隨筆寫,靖國神社展覽武器的地方使他感到不安,第一次讀的時候我才十二歲,現在或許更能讀懂吧。無論怎麽説,芥川都是幸運的,他在1927年自殺,1927年的日本還沒有坏到一定地步。三島由紀夫也很幸運,日本最瘋狂的年代他還太小,等他剛剛成人,那個邪惡帝國就永遠覆滅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意識到再也不會有人譴責長髮男生,他才再也沒有留起長髮。
我和上田的交往也沒有那麽多,我們除了都討厭日本政府和美國,對伊朗,伊斯蘭教和三島由紀夫感興趣之外共同點似乎不多。三島在有機會目睹伊斯蘭革命和共和國成立之前自殺了,很可惜。我寫小説寫累了就停下來,用電子琴彈那首Ey Iran,這首歌從旋律到歌詞我都很喜歡,甚至還能唱一小半。對文學來説,某種程度上愛國的熱情本身應該是一種剛需。不是愛某特定國家,而是“我愛著一個國家“本身吧,就像對特定人的愛情和“愛情本身”的關係。所以,現代社會應該也有失去了愛國的權利這一説的。
“敵人若是磐石,我們就是鋼鐵荊棘。
犧牲性命為土壤純潔是我所願
因您的愛成為我義務
我的思念從未遠離您
為您理想,我們的生命何足牽掛?
願我們伊朗的土地萬歲。”
我有幾次想在個人SNS寫,如果“武統“也就是侵略台灣的話,就成爲我自殺的契機好了。可是比起自殺,我可能還真的更在乎説這種話會被人嘲笑吧。況且我始終是一個懦弱的人。我在乎神的正義,但是我又以怎樣的努力(Jihad)來探求神國的大道了呢。阿舒拉日,人們用鞭子將自己抽打到渾身鮮血,女孩子們成群披著黑袍頭上繫著綠金色的帶子,確實,鮮血和悲傷是凡人最容易觸到的事物,而不義的痛苦勝過鐵刃百倍。
“但神使他所意願的人清白。“
上田有一次很嚴肅地突然找我,說
“自殺是不可以的,自殺是犯罪。會受到神的譴怒”
我説知道,不會自殺的啦。
但倘若不是畏懼成爲不義和受譴怒的人,爲何要自殺呢?
那樣的話讓別人殺掉自己比較好吧,不過殺人觸犯了人間的法律。
中學生時代不懂事,寫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文章,把金暴性和極道脅迫當成什麽很好玩的東西,現在翻出來看,真是丟人,丟人到快不好意思和別人談寫過什麽。哪有名作家會覺得這種東西好玩啊。不過想起來那時候誇張的言辭和中學生小混混們,還是覺得好好笑。
偉大的定義是什麽,或者説怎樣的人才能稱之爲偉大?人,是因爲天賦,勇敢還是某種虔敬而偉大的。過去我以爲是前者,但其實只取決於某個時代大多數庸人沒有的能力吧。寫下“我的悲哀不爲人所容(わが悲しみは人に許さじ)”的詩人若山牧水,那些關於戰爭和天皇的作協式作品,讀來一種“哈哈哈哈你也有今天”式的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