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原)當“人”變成“分子”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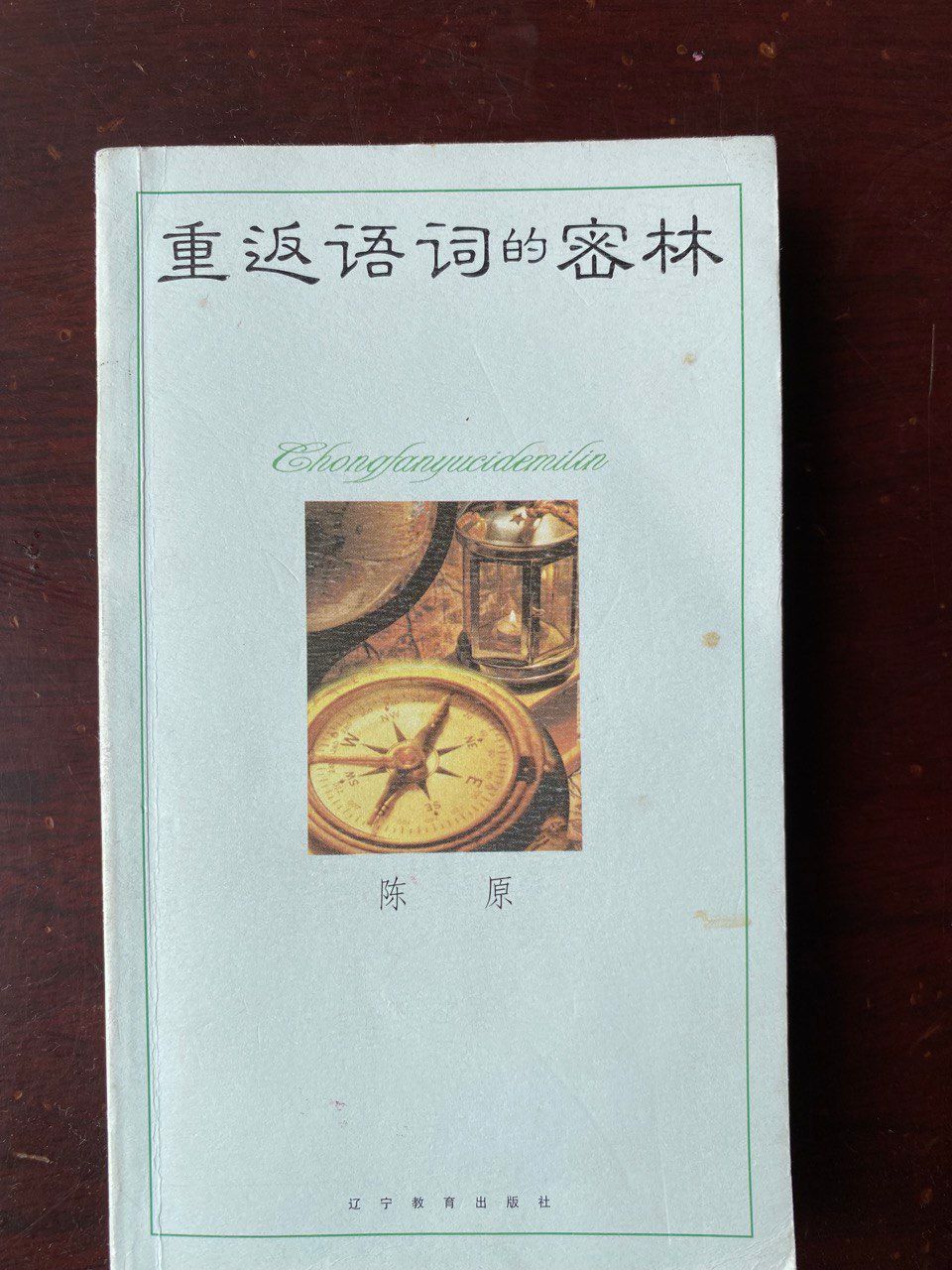
分子
“分子”原來只是一個科學名詞,所以舊版《詞源》“分子”一條的義中云:
“凡物皆由分子構成”——“物體可分為最細之微粒,不失原物之性”,這種東西就叫做分子。還附了英文原名molecule,可見“分子”是意譯過來的借詞(外來詞)。
值得注意的是,舊版添了個引申義:
“喻構成一體之各個體也。”舉例說,“如言國民為國家之分子,家人一家之分子。”
例子是很可笑的,誰說過“我是一家的分子”這樣的話呢?
舊時編辭書的人,往往自己造出一些實際生活著不曾用過的例句,來證明他的釋義正確——近年來國際辭書界已經不提倡自造例句,而求助於語詞庫:庫中收集了從書面語和口頭語來的活生生的大量例句。這且不去說它。只是這兩個釋義,一直沿用至今。
銷行超過三億冊的《新華字典》初版本(距今46年,即1953年面世)即沿此說,引申義云:“構成整體的個體”就是“分子”,例如“積極分子”,“進步分子”。所舉兩例的“分子”都是好人。可見解放初即五十年代初,分子變成人的時候,都還是好人。
從六十年代開始,這個簡單的釋義“政治化”了,說“分子”是“屬於一定階級,階層,集團或具有某種特徵的人”了。分子成了某種可爭議的人!分子是人呀。這本字典其後各版都如是說,例子卻只剩下一個“積極分子”,原來的“進步分子”不見了,儘管如此,分子還是好人。積極分子不就是好人麼?
同樣銷行甚廣的《現代漢語詞典》亦沿此說,但它一直保留了三個例子:資產階級分子,知識分子,積極分子。
當一個人變成這三個分子時,他是不是好人,就有點迷惑了。幸好還有一個“積極分子”,是好人無疑。
當人變成分子的時候
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是“分子”的。當人變成分子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凄苦的過程。讀懂“人”變“分子”的過程,就會很容易讀懂中國現代社會史。
試從一部大書抄下幾個分子來觀察觀察:
反對分子
動搖分子
最積極瘋狂分子
右派分子(大書中有說明云: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對派。)
“起義分子”(注意,加了引號,實指動搖分子)
中左分子
中間分子(另一處作“中間群眾”)
知識分子
頭五個分子變成人的時候,可憐都成了壞人。在這一串分子出現之前或之後,即在連綿不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不時出現了種種色色人變的分子或分子變的人,比如:
貪污分子
壞分子
地主分子
富農分子
破壞分子
反革命分子
地富反壞右分子
胡風分子
反黨分子
階級異己分子
托派分子
右傾分子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三反分子
黑幫分子
修正主義分子(又稱: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哎喲,分子分子,此時人們看到,當分子變成人的時候,多半成了壞人。好人不大變分子,比方五十年代初“三反分子”,是反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反對的是這三種人,可是只有貪污者變為“貪污分子”,後兩者沒聽說叫“浪費分子”和“官僚分子”(偶爾也見過“官僚主義分子”)。叫“分子”的顯然是壞人了。
再如有“右派分子”,卻沒有“左派分子”(“左派分子”不叫分子,只稱“左派”);有“富農分子”而不見“貧農分子”或“下中農分子”;有被整的“胡風分子”,而那些積極把人整成胡風分子的人卻從不叫“反胡風分子”。
由此可知,五百年後的古語文學家推斷,二十世紀下半期的分子變人的時候,十之八九成了壞人,於是“分子”一詞的引申義在五百年後的詞典中,可能注上“貶義詞”。
印貼利根追亞
“五四”前後,曾經大規模地輸入外來詞,而且很多是音譯的,例如:普羅列塔利亞,布爾喬亞,狄克推多,德謨克拉西,英特耐雄那,煙土披里純,還有印貼利根追亞。
印貼利根追亞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知識分子。
對當代中國文化教育有過重大影響的兩部大辭書《辭源》(初版於1915年)和《辭海》(初版於1936年),舊版(即1949年前初版的)都收有“知識分子”一條,卻沒有收錄那拗口的“印貼利根追亞”。
非常有趣的是,在“知識分子”詞目下,這兩部辭書都注上了用拉丁字母拼寫的語源:intelligentsia。一看,這個貌似英文的語詞,是從俄語轉寫的。據西方辭典學家的考證,它是1907年才進入英語詞庫的,語義則從專指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喚醒民眾的那一群可愛的智者,引申爲泛指覺悟了的或者說有教養且對平民百姓富有同情心的那一群讀書人。
舊版《辭海》云:知識分子有廣狹兩義,廣義指一般受教育者,狹義指受有高等教育,以知識為生活手段之人,“即勞心之勞動階級”。令人吃驚的是,釋義的後半竟然有點超前意識:
“因其不能自存,須依資產階級及勞動階級為生,故為非基本階級,亦非支配階級。”
妙哉!這裡闡明了知識分子不是“基本階級”,亦非支配階級(統治階級),是一種可憐的依人而生的人,幾乎有點像寄生分子了。
不過,直到本世紀下半期開始前,知識分子還可以歸入好人一類,雖然不是凌駕在萬般皆下品之上,卻也悠然自得,清高得很啊。
那時的人變成“分子”不覺得怎麼樣,只是有些智者卻不喜歡這“分子”,筆下不寫“知識分子”,卻寫“知識者”。有書為證:
1932年10月商務印書館復刊《東方雜誌》,主編胡愈之在復刊詞《本刊的新生》中寫道:
拿筆桿的知識者,如果能夠用著拿槍桿的精神,捨身到現實中間去,時刻不離現實,⋯⋯決沒有自悲“沒落”的理由。
總之,知識分子也好,知識者也好,這兩個語詞在本世紀上半期的語感還是積極的,正面的,多少還保持著一點人的尊嚴。到了世紀的下半期,知識者的“分子”氣越來越重,“文革”十年,則降到最低點,成了“臭老九”。為什麼是老九?因為在那史無前例的十年中,該打翻在地的排行榜第九才是知識分子,前面八個順次是: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
一根毛或一撮毛
知識分子是什麼?過去幾十年間有熟知的權威答案:
知識分子只不過是一根毛,一撮毛,只不過是附在某種皮上的一根毛,或一撮毛。這皮,不是人皮,不是獸皮,而是階級的皮。據說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是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因此通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麼沒有附在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的皮上?不知道。或者無產階級本身就沒有皮也說不定。於是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說。難道資產階級也沒有了皮麼?不解。到了此時,作為一種“分子”的知識分子,真是無皮可附,無處安身,確實變成了化學元素的“分子”了。
當人變成分子的時候,就意味著有一頂相應的帽子給他戴上。分子同帽子是孿生的兄弟。戴上帽子的分子,幾乎是永世不得翻身——除非有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給他摘掉帽子。例如現在六十萬頂右派分子的帽子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搞掉了,據說還有百分之零點零幾頂帽子還在某某的頭上戴著,不知是真是假。但願是假的罷。
幸乎不幸乎,知識分子這頂帽子卻還不怎樣臭,有時還可以遮遮太陽,擋擋雨水。不過若提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樣一頂大帽子,則又當別論了。“文革”前三四年,有過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帽子的集會,鞠躬,演說,鼓掌。誰知好景不常,一下子換了一頂臭老九的帽子,比原來的帽子更破。
歷史老人總是嘲弄世人,他從不走直路,他也要人們走彎彎曲曲的小路。現在,世紀末,我們的知識分子雖說還是分子,不過這分子已變成人了。不再是人變成分子了。善哉善哉!
高爾基
不知附在哪張皮上的高爾基,對知識分子卻有另外一種定義——那是根據世界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亞賓轉述的——,他說的文縐縐,也許是譯得文縐縐:
(知識分子)是在每一分鐘都在準備挺身而出的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捍衛真理的人。
高爾基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原來是非常之好的人,好到不得了的人,是捍衛真理,時刻準備為真理而犧牲的人。
五百年後的考古學家挖掘出一具知識分子木乃伊時,不知他用什麼儀器去推斷:這木乃伊是好人,是壞人,是好到不得了的人,還是無皮可附的不可救藥的人。那具木乃伊不知還戴著帽子不。
(完)
陳原(1918-2004)廣東新會人,中國語言學家,編輯出版家,世界語專家。建國後,歷任中國國際書店副經理、三聯書店編輯室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後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兼總經理、顧問,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
1979年,陳原主事商務印書館後,這里成為他撥亂反正,開啟民智,重塑中華民族人格的“理想試驗場”,他主持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意在把“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階級,一種思潮的先驅者、代表者”所積累的時代文明的精華,“留給後人去涉獵,去檢驗,去審查,去汲取營養”。
另外,陳原先生20世紀80年代在北京《讀書》雜志開了一個專欄,名叫《在語詞的密林里》,簡約、精彩、諧趣,可讀性極高。後來他把專欄文章編成書,讀書界幾乎人手一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