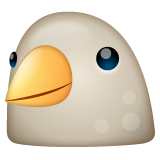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7日星期日。1916年《民报》在东京召开创刊周年纪念会;1926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起义;1949年重庆1127大屠杀发生;1980年印尼三宝珑、中爪哇省等城市发生排华骚乱……上海今日多云转阴,气温20到16摄氏度。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今天都是平常且普通的周六,人们日常地睁开惺忪的睡眼,日常地接受扑面而来的悲恸事件,又日常地走出家门休闲。作为上海指定的六十四条永不拓宽马路,安福路和乌中路街边的小店也日常地开着门,日常地迎接打工人们日常的光临。
如果说有些什么的不同,或许是寒潮将要到来的前奏,阵阵寒风把道路两旁梧桐树尚未转黄的叶子一把把地薅走,可能一如去年的冬天,老街在变得金黄之前就会被寒风薅秃。日常生活的节奏也有些不同,亦或是过载的26日让中国人民度过了2022年又或者说是2020年1月以来最烦躁的一个周五,借用些有点机械主义的比喻——拥有最宽裕的存储空间的中国人民,其情绪容量也达到了阈值。因而,不论让乌鲁木齐的子弹飞多久,不论全球最安全的中国大陆有多少境外势力潜伏,也不论到底是要躺平还是要放开这种二极管问题,再或者是沿着陇海线从乌鲁木齐到连云港感受中西部的“静默”,再沿着京沪广走遍大城市的“常态化”,所有支持或者不支持现有公共卫生事件解决方案的人们想必都有一个念头:撑不住了。
在朴素的政治光谱中,不论是左是右,总会在极化的尖端相遇,而在当下情境里,在尊重科学这一点上我们终究是可以达成共识。
这也是为什么在桥事件发生过后,各类抗议发声事件层出不穷,这也是为什么在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之后,上海的人们自发地聚集起来,让出这些原本节奏化的休闲时间,为远方那些与我们无关却又紧紧相连的人们祈祷凭吊。
我想这也是人们聚集在乌中的原因。在经历了26日晚五原路乌中路交叉口的清场之后,27日下午的主阵地似乎转移到了安福路乌中路口。在我刚想要去五原路口的场地吊唁时,安福路口聚集的人群吸引了我的注意,之后,我经过并参与了一系列群众聚集的点,包括五原路口、长乐路口,以及五原路与常熟路交叉口(之后简称常熟路口)。而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说明我参与的时间和地点都恰到好处,本文并不是对事件的忠实纪录,夹杂了现场的描述、我个人对活动和现实的一些反思。
我不愿意把它和那些更为久远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政治事件做类比,尽管我们都知道某些人心里早就把这些事件划了等号,但某种意义上它们确实共有同一内核,即我们对共和国,以及这片土地和其上的所有人们,所抱有的深挚热情与关切——我们担忧我们的人们,我们担忧我们的城市,我们担忧我们的共和国,我们担忧花朵的成长,我们担忧脚下土地的未来。
焦点:15时的安福路口
14-16时的安福路口是当日斗争的焦点和高潮。
最先引发人群骚动的是警察对一位黑衣大哥的逮捕,也是我所目击的第一幕。大哥位于安福路与乌中路交叉口东南侧的电线杆处,狭窄的路口和较密的人群让人很难从远处直接辨识出他,但依旧可以清楚听见他喊出的内容「不要核酸,要自由」。他的口号博得了群众的喝彩与掌声,叫好声与回应的口号此起彼伏。两辆警车,二十余位警察分布在这一路口,以维持交通秩序为主,同时密切关注现场的动向。虽然偶尔也有一些意料之内的激进话语出现,但场面仍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突然原本稳定的人群里爆发了一阵骚动,数位警察深入到人堆里试图将那位大哥逮捕,但大哥的挣扎和周围的群众的阻拦迟滞了警察的行动,“放人”“凭什么抓人”的呼声从中心爆发并向四周扩散……
和边缘零散的正在向路口聚集的人一起,我们迅速冲了向前,但只看到了大哥被制服在地,随机被扭送上警车的场景。群众和警方的冲突一触即发,群众大喊“凭什么抓人”“他犯了什么罪”“放人”,而警察则将冲上路面的群众向后推以维持现场的“秩序”。 警察将人群从路面推离,时不时有群众站出来为那位大哥打抱不平,“放人”的喊声汇聚成为声浪,群众们的呐喊一声比一声强烈,不禁让人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但警察们并不直接回应,大多数以平和近似于恳请的语气劝说人们配合工作,回到道路两侧的台阶上。在大哥原先待着的地方,有一位似乎是他的同伴的人拎着一手提袋饮品,希望能交给被带上警车的他,但警察好像拒绝了那个人的请求,于是他黯然回到了马路边上。旁边有一位爷叔询问民警那个人被带走的缘由,我试图听懂他们的上海话,不过也只能捕捉到一些碎片信息,似乎是那位大哥中午是喝了酒的,因而有些情绪激动,而带走他的理由好像是影响社会运行秩序,但也只是好像。
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明显过分的暴力行为,道路北面和南面均有人和警察产生口角和肢体摩擦,警察用力推搡人群,而群众则抓住执法力度以言语回击,若干群众站出来指责警察的行为要求放人,但效果并不理想,有一位甚至遭受了警察强烈的推搡行为。随后站出来的一位蓝衣大哥,仅是高喊了一句口号要求公正执法,尚未在路口泛起涟漪,随即被警察反扣手臂制服,迫靠于电线杆,而后被警车带走。
虽然连续两位站出来的大哥被警方逮捕,人们退至路口的四个角落,但群众的情绪不仅没有就此被压制,准确来说,是达到了一个小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路口四角聚集的群众从未停止过“放人”的高呼,而且始终克制自身的位置与行为,没有任何把柄留与政府一方。甚至,群众们体谅配合警方对秩序的维持,理解执勤民警因自身所处位置的难处,也配合他们的工作,在聚集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公共交通的影响。讲到这里,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一场活动以年轻学生为主体,但事实上我们都清楚的是,上海的大学仍处于名义上的“封控管理”中,出校需要严格的审批;而只要睁大双眼,环顾你所处的四周,竖起耳朵,倾听身边群众的呼声,就能够了解,各行各业各年龄都有人参与:有年纪大的人在询问聚集群众和警察目前的事态后,表示理解并加入到了站立的群众中;有年纪小的在父母的陪伴下站在街角一旁。
下午约莫三点钟左右,安福路口的聚集活动在一位身穿棕色外套、手捧橙色雏菊花束的年轻男子的行动影响下,达到了最高潮。我想用一些比较零散的话语来形容这一场面,那短短五分钟给我带来的冲击,不论是过去半天,亦或半年半个十年,我想我都会清楚记得。我钦佩他的勇敢,感动于他的勇气,赞叹他的行动,他的口语表达的不多,肢体语言也很少,但仅仅是他的在场就足够有力,我想这也是我以及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们心中所想,站立也是一种战斗:
他手里握着一束雏菊,
经斑马线走向路中央,
警察想要拦下他,
他说——
你有什么理由阻止我为远方的人们哀悼,
在昨天或是前天,
不久前或是更久以前,
火灾或是更多的事件,
乌鲁木齐或是更多的地点,
十个以及更多的同胞,
业已正在或者将要逝去。
中国人需要多一点勇气,
中国人是否真的缺那一点勇气?
拒绝核酸与隔离封控的勇气,
选择做核酸、不隔离与自由的权利……
话音未落之时,
手中的花束就已落地,
连带着和人一起,
被推搡扭打制服在地。
周围的人们呐喊——
你们凭什么抓人。
周围的人们集聚——
你们为什么打人。
周围的人们高呼——
放人……
可他们不听,
回应群众的就只有警车门关闭的声音。
人们像潮水一样,
又被推回到了原地。
……
那位小哥的壮举——虽然在一些人看来他的结论,例如对乌鲁木齐火灾的归因,以及一些或许有些过激的话语,例如是被CCP杀死的,有点煽动性或者是以卵击石,但是我仍想将其称之为壮举,五分钟,是他被扭打并送上警车的时间,很短,按照这个效率一小时就可以把安福路口的人们全部抓完;也很长,人们似乎还有一线期望能将他从公权力的大手中拿下。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轻松地得出一些结论,譬如,聚集活动仍在公权力的容忍范围之内,但只要是有公开发表言论,即涉及到示威、游行、集会等性质的活动,则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扑灭。我想,这也是和某两年发生的某两起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相关。毕竟,以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崛起的政权,对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研读颇深的政权,是不可能没认识到群众的力量的,我们总开玩笑他们一点不重视群众,但事实上是他们非常重视群众,只不过这种重视并不是同一的认识,而是对立的认识。
在这之后,人们也认识到,在当下的情况下,站立,在当下的中国大陆环境里,似乎成了最好的抵制活动。毕竟,在传统的游行活动里,游行代表着公民权力的流动性,但我们都清楚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抱残守缺。因此,在作为公共空间的街道里,以移动性为尺度的场域里,对静止/站立的坚持,就是对公权力所期望的流动、解散、清场和逮捕的对抗,是一种弱势群体对强者的实践的艺术。毕竟,如果我们仔细去回顾民警对聚集群众的劝说话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那些最常用的句子“动起来动起来啊”“没事儿就别在这儿看热闹了”“要过马路赶紧过啊”,蕴含着从上级传递到基层民警的命令和指示——避免聚集(相对静止),因而从这个层面上讲,站立是目前我们能选择的最合适的斗争方式,这既是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权力场域内同属弱势的基层民警留下缓冲的空间。毕竟,下午在安福路口大多数的民警都有一种强行营业的倦怠感,面对着民众的讥讽,他们也只能苦笑说“政治是最肮脏的东西”“希望你们也能体谅体谅我们,你不往机动车道上站我们也不赶你们”。
这期间,有一位操北京口音的男士和民警在辩论,究竟为什么抓他?他犯了什么错?他犯的错严重到要抓他吗?抓他的时候有必要采取暴力的形式吗?执法没有度吗?抓了他之后你们又要做些什么呢?什么时候放人呢?你们抓得完吗?你们对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你们没什么感觉吗……这一连串发问基本上可以概括所有聚集的民众对警方的发问,而我们也清楚其后续:他们很难给出我们希望的回复,甚至他们连回答本身都是困难的。
在这三次行动期间,我观察到有三位着便装的男士在人群之间来回穿梭,其中两位手持旁边咖啡厅买的咖啡——安福路是上海最有名也最具有下所谓小资情调的特色街区之一——用沪语在交谈,我听懂了一些关键词,包括对人们反对核酸、在此聚集的不屑和不解;在警察抓捕站出来发言的人、情绪高昂的民众走上街道时,那两位就混入人群中同民警一起劝阻人群、迟滞人流、分割人潮;而另一位身着摇粒绒稍显年轻的便装男士则直接参与到了对那位捧花小哥的抓捕——在小哥发言时,民警并没有行动迹象,而在一辆警车行至路中央,即将和小哥的行动轨迹有重合时,便装人士和民警一同发难,将小哥制服并扭送上车。我还听到那两位咖啡便装人奉劝民众的话:这有什么好聚集的,没事儿的人就散了吧。
在小哥被抓走半个小时后,路口的人群也渐渐安静下来,大家只是安静地站立着。有一位老人经过,看着四周密集的人墙有点不知所措,于是问民警道,“这马路我能过吗?”。民警回说,“大爷,能走,快点过去吧。”大爷虽然没有搞清楚状态,但还是推着自行车过马路先,在临过去的时候,他转头问民警,“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了?”
“与你无关就走。”民警对他摆了摆手。
中场休息:交通管制的前奏
在站了快两个钟头之后,安福路口的人群虽然没有想要散去的意思,但也没有什么大的波浪发生。在我旁边,有一位小哥和一位大哥就行动策略上进行了随口一说式的讨论,小哥认为我们应该逼得更紧,增强我们的威势迫使警察放人或者在下次发生局部冲突时放弃抓捕的念头;而大哥则认为要避免冲突,尤其是在一方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这点我也表示赞同,在中国未经备案的游行均是违“法”行为,而在法律范围之内的聚集是在这一场域内弱者所能展示的最大程度的抵抗艺术,我们在主导者所规定的范围内坚守自己的位置,故而让其丧失制裁所需的名分——我们是在其规则内行事。
口感舌燥的我希望能找到一家便利店——这一需求因为之前一系列行动暂时被搁置——既是想多站斗一会儿也是因为退到后面实在困难,而最近的在马路对面的好德便利店,不知道是因为周六晚的活动与管制加上今天的人群聚集还是其他,并没有开门。在紧张感稍褪去一些后,我也退出了站斗,过马路向五原路口走去——那边有家全家和一间还不错的茶餐厅供歇脚。
从安福路口到五原路口段的乌中路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行人,不禁让人好奇怎么一辆车都没有——我走过去才发现是北向行驶的路口拉起了警戒线。站在五原路口北侧等红绿灯时,我望向对面——称得上是乌中业态最兴盛一段——行人从五原路走进又走出乌中的一家又一家店铺,一些人会好奇地向安福路望过去几眼,但随即又走进商铺或是走向常熟路地铁站。总之,这两百米像是隔开了两个世界——一边流动性极强,一边静止不动。
而在一小时前刚刚听过、喊过“不要核酸”口号的我们的身后,排起长队的,就是一个核酸亭,同样也用喇叭播着些什么:请扫场所码,保持一米间距,有序排队。
延续:五原路口的花束
年纪大了,只是站了两个小时腰就痛得厉害,在我坐定之后,原本过了饭点儿空荡荡的茶餐厅也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除了日常聊天,大家的话题都和安福路口的聚集活动相关——不论他们本身所处的位置如何,但是在执法的力度、民众的声音以及公共卫生政策的科学性这三方面上,似乎都很容易达成共识。
走出茶餐厅的时候,已是将近五点,最近上海的天光暝得很早,已是日薄西山。夕阳很好看,只是前景从车流变成了人流——五原路口也聚集了起来;人们多到站在路面上——原来是五原路口整个拉起警戒线,似乎是已经开始戒严;人墙里三层外三层,由于围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只能勉强看到里面有三名警察——但我们都知道人们闲着没事儿不会围警察,而且警察也不会束手让人们把他们围起来。借由前面人的手机,我看到了在内圈里,三名民警同样围着一些东西——地上摆着民众献上的几束花,而人们聚集一圈,似乎在缅怀的同时防止警察将花束撤走。
不知道是谁带头,人群中传来了一句“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陆陆续续集结,人们齐声唱起了国歌——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随着天渐黑,来吃饭或者吃完饭的人也多了起来,国歌断断续续唱了几遍,也有人喊核酸与自由的口号。
也有些突然,本来在内圈观望形势的民警把地上的花束捡了起来,并试图穿越人海向道路北侧——戒严的方向走去。本来稍显安静的人群也随之爆发了一阵骚动,人们一边拿出手机拍摄一边怒吼着质问着——
“连死人的花你也要拿吗?”
清场:长乐路口
由于五原路口已然没有进入的可能性,我便试图从常熟路绕回到安福路上,但不意外,安福路同常熟路的交叉口不仅封路,甚至加上了路障。起初,我自作聪明认为他们必有一疏,没有封闭长乐路与安福路之间的写字楼,于是我穿过树林,发现出现在眼前的还是铁栅栏。没有办法,不想再退回去的我,抄小路拐到了北边的长乐路上——回到了我今天最开始的路线——想要去碰碰运气。
长乐路与乌中路的交叉口同样拉起了警戒线,但不同于五原路同乌中,警戒线除了人造纤维,还有用民警的“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路口的四个角同样站满了人,但囿于台阶面积实在有限,人群的分布有一种夷陵之战里刘备八百里连营的阵势。我站在道路西南侧的街角,观察着路口的形势,此时约莫是将近六点,人群还在不断聚集,特别是道路的东北角,本就逼仄的路面已经是挤到水泄不通。
环视四周的过程中,我看到旁边站了个外国人,他在和旁边的一位女生了解今天下午的情况,听起来那位女生大致也同我保持了一样的行动轨迹。他俩旁边站的另一位小哥也加入了聊天,三个人除了分享今天的见闻,还就中国公共卫生事件交换了看法,具体的谈话内容囿于隐私并不展开。那位老外来自英国,据他所说,在他的圈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来到了现场;我们问他将会如何报道这一事件,他表示对身处遥远海外的人来说,中国发生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相信中国发生了这样的可能威胁到人权的事件,而是他们无法想象此时身处中国的人们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之中——北京、上海都是如此,那中西部又是如何呢?那位女生问他,为什么BBC没有来到现场,他略微耸肩苦笑,并对我们讲述了BBC在中国的污名化:在英国,媒体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而好话当然没有必要反复吟唱,因而你也能感受到诸如BBC一样的媒体发布的报道、评论大多是对政府的质疑——自然也可以理解延伸到海外版它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虽然BBC对中国有质疑,这种质疑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政府执政和治理水平的鞭策,但这种鞭策在中国的语境里,往往被曲解成为一种攻击和对内政的批评——它的好话好像说得太少了些,但他说即使是在英国,BBC也是质疑远远大于完完全全的恭维——这也是媒体扮演的角色不同。
在我们聊得火热、谈到今天具体的活动时,身边另一位大哥也加入了我们的聊天局,他认为今天活动是非常克制和审慎的——这也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人组织,我们一致认为这种克制要延续下去——避免真正的有心之人浑水摸鱼和公权力内部强硬派的抬头——他们都在等待一个苗头好让态势升级,如果希望表示抗议,最重要的是维持我们——真正且具体的人民——始终在场,从而向遥远的朝堂之上传递声音和威压,因而避免和公权力产生冲突就是重中之重——否则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由头以驱逐我们。在他看来,为了避免重现学潮事件的悲剧,尤其是在公权力的实力空前强大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和希望;而这次纪念活动选择的位置也是有考虑的,乌中路很长,但纪念活动位置选择五原路和安福路口,其实也是考虑靠近使馆区的原因——虽然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他们不能也不愿在这个话题上有更多的行动。
在我们聊着的时候,身后的路口突然开来了一辆货车——车上装满了路障,民工们把路障搬到路口,摆成一排,而警察则分成两排,站在路障前,并拉起了两道警戒线。在这期间,路口的形势非常稳定,交通警察并不试图驱散群众,而是语气平和地规劝围观群众在驻足时远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要站就站在台阶上。大家都非常配合彼此的工作,交警需要完成维持交通秩序的工作,而民众则以折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突然,东北角爆发了一阵骚动,警察似乎在驱赶什么人。担心事态升级,我和大哥立马冲了过去,试图了解具体内容。原来是警察试图驱赶坐在花坛边沿的几个人——以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名义,他们并不想离开,口角也因此爆发,而在警察借助推搡驱使他们离开的过程中,肢体冲突的苗头也埋下了。特别是在外围看热闹的一些群众,因为站在位置接近车道或是那几个被重点关注的人,也遭了殃,被警察用力推开,其中有两位小哥因为警察动作力度过大,外加受了无妄之灾,一下被点燃了怒火,以硬气的话语质问了警察,但警察根本没有服软的意思,反而是又推了一把,并以“走不走”的话语更恶狠地回击。眼看冲突就要爆发,我和大哥连忙把他们两方分开——首先维持态势的稳定,尔后东北角的冲突以台阶上腾出了一条可供担任通过的道路告终,花坛边沿站了几位交警,东北角的人群更分散了。
回到了西南角后又过了一会儿,感觉可能没什么别的事态发生,小哥和大哥都各自离开。我询问了一下那位女生,在我去茶餐厅歇脚的时间安福路口有没有发生些什么,她给我的回答还是那位捧花小哥,那在我不在的时间,安福路口似乎一直保持平稳。
不断有行人因对聚集的人群和管控的道路感到好奇而驻足,也有原本计划去乌中路吃饭的人在被告知不管如何都是“只进不出”后被迫放弃去乌中路吃饭的计划;而对这一区域的住户而言,进出变成了极为困难的一件事,如果是步行,则被告知进去了就先别再外出,如果是驾车,则需要绕行到未上路障的路段方可进入这一片封闭区域——五原路、长乐路、永福路等交叉口都已进入特别状态。对这些人而言,民众的柔性对抗所引起的公权力的敏感反应确实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放弃自己周末的休闲生活,而这里同样也有一些高端住宅小区。
也有不少过路的行人在驻足后,加入了聚集的群众,他们虽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有人在问我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但依旧选择站在这里,不管是抱着站斗还是围观的心态。在我看来这也是当天很多聚集群众的行为——无计划、混沌的动机、随机但自愿的停留,他们可能不能做些什么也难以做些什么但大多都期待发生些什么——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们都期待或多或少能有改变发生;在这个过程中,自己都期待能成为或参与或在场的见证者。常被当作是境外势力干预的铁证的记者之在场,譬如那位刚刚与我们交谈的英国某家媒体的记者,在和旁边其他几位围观的外国人聊天——那个区域由于自身区位的特殊性本就有很多外国人居住,他们几乎和身边的中国人没有交流——如果有也是如同大多数中国路人在目击到这一聚集现象后脑子的茫然和对热闹的天然好奇一样,向身边的人询问目前状况为何。再譬如,在见到警察组成人墙并布置路障后,一位日本小哥举起手机,用前置摄像头自拍了一段vlog——“日本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现在是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话音未落东北角就发生了那起骚动,他也飞快地跑过去围观和纪录——就如同中国人也会录街上看到的中国人打架一样。
东北角在稍作清场后,又聚起了人群,并且似乎在四个街角中显得最为激进——其余三个角大多是围观的人群,在东南角的台阶上放着的钢材堆上站着许多占据最佳视角的人,而我所在西南角,大多是不明所以驻足的人,询问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上至爷奶叔婶,下至中青少年,居住在这里面的人搞不清楚状况,而途径的人短暂停留后又走向地铁站。
东北角由于劝离引发的骚动仍未完全平息,俄而,又爆发了一阵喝彩与叫好声,囿于西南角视线有限,我转移到了更接近的东南角,但还是搞不清楚具体情况——东北角的人群太集中了。和西南角的结构相仿,我的旁边又站了一位正在和身边女生了解情况的外国男子,以及两位围观并评论的小哥。那位小哥同样好奇对面发生了什么,我扼要地向其说明了这是一系列想要驻足与想要流动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争执;他若有所思,拿出手机用文字群聊和拍摄视频记录当下的情况。
时不时,交警过来劝说群众不要站在车道上,偶尔有人不听劝,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交警就会半揶揄半无奈地说,“我们不为难你们,你们也别为难我们好吧,机动车道晓得吧,你行人能上吗?总得配合我们的工作吧?”;也有不明所以的行人问能不能过马路,交警也随之回答,“当然可以的啊”。其实封路对外卖小哥的压力很大,因为送不进去要等顾客过来交接,他们总是被交警规劝推开电动车;有准备长线作战的群众把外卖点到了路口,外卖小哥也不得不把手高高举起以便利游客辨认。在设置了路障之后,有个路过的外卖小哥专门停下车,激动地掏出手机录起视频,我从他的嘴里听到了他对朋友描述和定义的这场活动:暴动。虽然聚集在路口的人群只有约莫二百人左右,也有部分群众分布在延伸更远的道路上,但我们可以说,这完完全全是一场群众自发聚集、从心发声、自主决策的纪念活动,而不是一场有境外势力煽动、徒有满腔热血的、有任何预期目的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暴动”。
那时对面偶尔有人唱起国歌,或者喊一些口号,旁边的外国男子抬起头和我搭话,“今天的警察都很克制啊”。我笑着回复,“因为在中国,没有经过备案的游行和示威都是犯法的,大家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大家也都保持克制,不给公权力留下让事态升级的借口,standing still is the greatest defense ”。听了之后,他也笑了。我也听到旁边两位小哥在交谈,其中一位担心秋后算账的问题,担心在场的人会不会在明天被一个个找上门;另一位就宽慰他,如果真的要算账,直接让这里出现一个阳性,那所有人都是时空伴随者,都变成红码了,高效制裁。我对此深表赞同,各方都有自己的尺度。
后来,对面突然又爆发了一阵听起来不小的骚动,外国男子立马冲了过去,而因为对面人多无从落脚,我就留在了原地。有一位过路的婶婶问我对面发生了什么,我说可能是因为有争执,她又问是和外国人吗,我回答不清楚。骚动很快就平息了,我一扭头,看到了之前在西南角聊天的大哥,笑着问他怎么还没走,他说走到一半,听见声音以为出事了马上就又折返回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说,现在看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他这次也是真的要走了。我们俩互相道别,在回答了几个路人的问题后,看着局势平息,我也沿着长乐路向东前往地铁站。
尾声暨前奏:常熟路口的人墙
决心前往地铁站的原因很多,最关键的是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民众们除了聚集也无法再做出其他更多的行动了——警力的威慑和民众的魄力不相上下,另一方面也是小道消息总是传言说有武警在路上,总之,处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我踏上了归途。
常熟路上,安福路的路口依旧封得严严实实,只进不出,但没想到在进地铁站的最后一百米,我又被五原路口聚集的人群吸引驻足。五原路口当时约莫聚集了有五十余人,虽然不清楚他们聚集的动机和目的,但我决定还是先稍作停留,一是当作见证,二是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做的事情。
和其他时段的其他路口相比,五原路与常熟路口的活动并不显得十分突出,但由于独特的地形和区位,这里明显有不同的可能性:靠近地铁站与单行道路口。前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围观者和路见不平的生力军,有疲惫的人离去,同时有好奇的人驻足并加入;后者则体现在,这个丁字路口是单行道与常熟路南向汇聚的点,不似被分割在四个大陆的其余路口,在这里,聚集的群众和集结的警力隔着斑马线背靠红绿灯面对面对峙。就年龄结构而言,常熟路口聚集的群众也显得更年轻,同时就成分来说也更复杂(有很多潮人在),但能感觉,这里的聚集活动确实是有一些相对而言更激进的民众在的。
在我刚到的时候,站在最前面和实行交通管制的警察们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群众的,是一位高壮老哥和一位女生。在两位身旁和后侧,有许多群众大声地为他和她声援,或者更确切地,是凝聚成为一个群体对警方施压——民众的呐喊此起彼伏:有一位年轻的摇粒绒小哥,同样在和他面前的警察对话,希望秉公执法,释放被捕群众;我身边一位黑衣小哥则声嘶力竭地控诉言论管制和暴力执法……在民众试图向前施压时,交通警察依旧维持着自己的防线,避免被抓捕的人有机会和民众接触——被民众释放是不可能的。
看到被捕者即将被转运,人们汇聚而成的人流加强了冲击的力度,喊着“放人”和“人民警察为人民”向前涌去;相对的,作为反馈,警察也开始向外推搡,一齐将民众向五原路外推去,那位在最前的大哥受到了最为严重的推搡行为。
受到冲击后,民众和警察保持了一定距离,以免再次遭到冲击。在人潮退后之后,不知怎么,我被留在了第一排,和警察面对面;而现在还在站在最前的,换成了那位女生和摇粒绒小哥,在他和她的表率下,以及后面传来的带头的喊声,“放人”“放人”的呼声再次无数遍重复播放在我的耳畔,某种程度上,这两个词成了当天出场率最高的呼声:只因一句“不要核酸”民众就可以轻易成为被抓捕的对象,而民众的“放人”重播多少遍都无法撼动公权力的心,对抗这一师出无名的抓捕。“你们难道没有家人吗?你们难道没有朋友吗?你们难道也想让自己妻子朋友过眼下这样的生活吗……”,冲在最前的那位女生声色俱下地说着; “你们是公务员,是拿着纳税人的钱来办事”“人民警察为人民”,那位黑衣小哥叫喊到喉咙沙哑;“让民众说话天不会踏”,不断有青年站出来和警察同志们交涉;在人群的最后有许许多多的人举起了白纸……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一句“起来”,随后整个路口聚集的民众都唱起了国歌;我甚至能听到有维族同胞用没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坚定地一字一句地唱着,之后我听到她在给朋友发语音,大致意思是新疆如此政策如此,怎么能不发声?
但面前组成的,依旧是两列警察组成的血肉长城。在这堵高墙背后,装载着被捕者的警车也放弃从五原路驶入常熟路,而是选择掉头。空留群众在不断地唱响国歌,不断地和警察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交涉,而随着警车驶去越来越远,我也愈发觉得虚无。
虽然常熟路口的行动在我看来一定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但若是把它打成“境外势力”,我更愿意把“把它打成”的那个人打成“有心之人”,双方的克制有目共睹。在冲击的势头被阻止之后,警力在路口排成两排,有着便装的上级过来视察,把他们的布局调成得更“合理”。民众的情绪也缓和了些许,和他们保持了更远的距离——往前稍进一步就会被警察喝止。
不断有人在这个路口停下:人群原本只是将将能够封闭上这个路口,而现在已经延伸到几乎可以对常熟路的交通造成影响,两侧的行人区域也挤满了人以至于更多的警力被派来维持两翼的秩序,不过这也给原本住在这一区域的居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尤其是在出行方面。当然,造成这种不便的主要责任人是封锁这一区域的警方:这一区域在管制之后变得只出不进。对机动车而言,因为五原路到常熟路是单行道,所以只有单方向驶出而没有驶入的车辆,我想这一定程度上也助力了人群在此处聚集;当有车辆驶出时,警察和民众都非常默契地让出一条道路来,还能听到旁边的老哥和身边人对驶出的豪车一顿点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高端住宅小区)。而对于这一街区并不限制非机动车出行,只是出去还好说,而想要回去的住户就有点倒霉,被警察拦在了外面;我看着立于警察和人群之间的一人一车,心里也有点同情;也不时有人开玩笑,既然进不去就加入我们;而最终,他们也只得把车推到两侧的台阶上和人群一起等待,或者是绕行至更远的路口碰碰运气。看热闹的群众大抵也是有的,因为有一个大哥不知道从哪里挤了进来,还踩了我一脚(当然,没有说抱歉),站到了我前面,掏出手机开始录小视频发朋友圈,我看清楚了配文,内容是说乌中纪念活动现场直播。他扭过头问旁边的人今天被抓了几个人,和之前退下来的大哥站在一起的一位女生回答说可能有两三个吧——起初我以为要求释放是泛指,包括今天下午被抓捕的群众,但听起来这个路口在这之前好像也被抓捕了两三个人;他又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她开玩笑说,“你自己留下来看不就好了”,于是大哥又拍了几个小视频,接着挤出人群走了。
在局势平稳之后,我的乐趣,就是之前带头的大哥和旁边的一位中年老哥,以及那个女生聊天。那位大哥说自己也没什么能做的,不能做得太过,也过了带头的年纪,没能做得更多,但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可能;旁边的老哥也同意,毕竟没有什么人组织,自发聚集过来是这样的,而且这一次的规模也很小,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人左右,连淮海中路都站不满。在人群反复播放好几遍国歌后,那位老哥再次锐评,昨天是唱国际歌,今天改唱国歌,为什么不唱明明更合适的国际歌了,因为在这种老小区,唱国歌肯定比唱国际歌更能引起人们的共情与支持;我对此深表赞同。
当然,一如其他路口,常熟路口看似稳定的局势其实也只是如履薄冰。在中间几次喊口号的过程中,不乏有一些在国外习以为常,但在国内仍有些敏感的行动。譬如,有一位女士对警察狠狠地竖了个中指,虽然我觉得警察可能也不太能领会个中意涵;后排也有人愤怒地大喊“帮凶”,在前排的我开始还觉得后面的人出于距离的原因需要更有力更方便传播的词句,但是等喊到“败类”“走狗”的时候我就有点慌了,虽然不反对大家表达意见,但是终归还是不能延伸到人身攻击,况且,站在第一排的是更克制的我们。我有时候也在想,会不会是人群中所处位置、在对抗关系中的位置关系影响了具体战略的选择。除此之外,晚上还多了一个浑水摸鱼的人,也搞不清有些人是坏还是真的蠢,竟然对着警察大喊“你在狗叫什么”,甚至在人群没有遮挡的声音之后,那个男人还连着呐喊了好几遍,听得我头皮发麻,他前面的民警更是已经按捺不住开始逼近人群了。好在人群中保持理性的是绝大多数,一句“你是不是有病”直接将酝酿的风波化为无形。当然,一些更过激的话语其他路口也不是没有,中午安福路口就有人大喊下台和推翻这类我听了都要苦笑的话,但那毕竟不涉及具体的人身攻击——我们也要顾及警察自己的难处,同时考虑不同路口的空间布局,常熟路口直接对峙的特性就导致采取的战略必须更柔性。
在那之后,常熟路口一直是双方礼貌对峙的状态。唯一的一次交涉的尝试,是摇粒绒小哥发表的一次演说,但一如其他路口,警方的缄默直接让群众的努力转化为一种无计可施的挫败感——又能怎样呢?小哥丧气地点了一根烟坐到了马路牙子上,随后又走到右翼,和末端的民警交谈。站了大半天的我腰痛难忍,注意力也开始分散,“他们肯定是想着,等人散了就好了,毕竟明天就周一了,打工人都要去上班了……”,我又听到旁边的老哥在说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聚在这儿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是在等待做什么事情,还是等待什么事情发生……”
确实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而我们的期待又是什么,如果不解决这些的话,那我们的聚集确实显得有些虚无,但这种虚无是源自因为像无头苍蝇一样的我们吗?我记得今天中午我刚刚站在人堆里的时候,看着被制服在地上的大哥,被反扣在电线杆旁的大哥,被扭送上警车的小哥以及和警察据理力争的老哥……心中百味杂陈,我打开手机检索,“在一场游行/示威活动中,一个普通人能做些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更准确的说,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或者说该在目前的情境下,怎样才能在自己合法权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开展一些表达意见的行动。我思来想去,好像也只能和大家站在一起,站在路口,站在街道,以固定的位置对抗流动性。我们可以搬出法律中关于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条文,但也无法忽视更关键的,“集会、游行、示威应向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提出申请”。所以,回到开头,没有人想要成为无头苍蝇,而是所有的苍蝇早就被掐去了头,一如曾经的自组织被细胞化一样,在政治的场域内我们也被细胞化了——中午安福路口的一位交警曾无奈地对回复民众的询问“最肮脏的就是政治”,一句有些朴素但确实无奈的话。于是,腰疼的我,看着继续站斗的大家,和身边的人说句先走一步后,转身前往地铁站。
期间,我听说有一起去吃饭的人在门口看到有逡巡的着便衣的男子,也听说了地铁上有警察查手机——这个第二天影响更大,但我好像都没遇到——即使流传广泛的视频显示好像是我常搭的八号线。不过不管怎么说,在我回到寝室,睡一觉醒来后,这半天好像从中国大陆抽去一般,没有半点痕迹留存。
之后的事:一点声音
那也是我写作本文的出发点之一。在当晚,有一张内容是关于乌中路牌被卸下的图片,在简中互联网广为流传,于是我本着验证的想法——同时也是缅怀,缅怀远方逝去的人们,同样也是缅怀这场行动,计划找机会重返现场。在一周后,我终于成行,再次前往了乌中。这一周里我断断续续回忆那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断将已完成的部分和朋友们分享,但分享的过程,不论是以Word还是PDF的形式,除了第一次发送的文件可能幸存,绝大多数的消息都被微信屏蔽;这一周里也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敬爱的江爷爷离世,但影响更大的,可能是从中央到地方(广州),各层级对解封的造势,曾经被妖魔化的奥密克隆一下子被拉回到了流感的评级,广州地铁通道里到处张贴的场所二维码也都被逐一撕掉,人们拿出手机拍摄海报被撕除的画面分享到各类社交平台,甚至可以据理反驳那些扫场所码的要求——在几周前这还被认为是大不韪的行为,一些城市的常态化核酸点已经撤除,进出具有中央意味的场所譬如车站也无需查验48小时核酸,朋友圈满是欢欣鼓舞的词句,开始有人思考要去哪里旅游,甚至一些平台开始卖起了一年期的旅行套票……种种光影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既视感极强的画面:“如此工作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放到这里可能是如此核酸三年,直到二维码崩塌——这不仅让人想到昔日一夜之间的自由化政策,只不过我们都知道在那些快速的闯关背后潜藏的是怎样的风险。
我在这里想重点强调其中潜藏的一种可能被我们忽视的风险。它或许和被我们遗忘的那些抗争有关但又不直接相关,因为可能在如此庞大的欣喜面前,那些沉重的伤疤并不会想被人们反复揭开;我也不想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种风凉话,它只会在人们内部造成更多本不应该存在的裂痕,以及一种俯视的高傲态度。我所要的强调的风险,是这种巨大且迅速的转向本身。这种转向在没有经过任何“试点”,没错是“试点”,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所谓不得不封城的“感染”,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次打着其他名义的封控或静默,社会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在其中也有各种各样关于“放开”与其他保守思路之间的争辩与呼声,但事实上,对于“放开”,我们好像并没有积极主动在中国大陆对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开展公共卫生政策调整的实验与总结。如果还能总结高中政治生活里提到的“枫桥经验”的内容,或者是《我爱我家》里傅明老爷子里对家庭事务的经典段子“搞一个试点,总结总结经验,然后在推广嘛”,我们好像感觉这一转变似乎来的太快了些:不仅是出人意料地推翻了原本保守、严格且坚固的政策高墙——这一高墙背后还有不计其数的利益群体和迷信群众为之叫好,而且其崩塌的速度之快只能用一夜之间来形容——没有任何的缓冲期或者是逐步适应的过程。
这时我们再审视,这一行动就耐人寻味了,或许会有一些人为国家叫屈——“你们这些人想要放开,那给了你们还不好吗”,或许会有人对政府恢复了些许信心——“它还是会听人话的呀”,或许开始有人对未来充满了信息——“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明天会更好”……这些印象可能会指向“科学”“群众路线”“预期”“确定性”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词语概念,但事实上这一巨大转变本身带来的风险指向的完全是这些褒义词的反面,延续了三年的被称为“防疫”的公共卫生政策其运行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被成为“人民”的合法性,以国家意志持预防保健之名,人们被迫出让自身的数据和身体以及预期,即使是在最受非议的2022年后半,依旧有一种呼声称其高感染率仍对儿童和老年人存有较大风险、中国现今的疫苗接种率不能够支撑其实行如同新加坡一样的政策以及为延续现有政策站台,并驳斥各类存有放开倾向的声音,“放开”被污名化为“躺平”,“民众上街聚集”被污名化为“境外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这种二分完全忽视了中间逐渐过渡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多种呼声与需求,而就在其中一极在击碎了十一月底的各种抗议呼声并沾沾自喜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撞倒的不周山是自家房子,他们自家的头也没了。
不周山倒塌的是如此迅速,以至于连十一月底最激进要求取缔核酸的声音也会觉得吃惊,他们可能也想掐掐自己的手臂看看自己是否活在梦里,但对更多受够的民众来说,这一步迈得过大过决绝,在三年的公共卫生事件中都没能完成的上下统一这次反而执行得干脆利落,以至于相对于中央的地方在苦行了三年之后究竟能有何种程度应对未来的流感也成了一种风险,人们一下子好像回到了80年代末的下岗潮,一夜之间人们被推到了市场化的浪潮面前,而今天则是不得已要面对国家在公共卫生角色的大退步所带来的种种风险,而这种风险现在不得不为他们自己个体承担——所谓所有人是第一责任人。当然,我并不是呼吁再把这一责任交还给国家,相反,身体应当且仅应该由个体所支配,但我们也都注意到了这种身体成为国家玩物的风险:它确实抬起了科学,它确实听到了声音,所以它把身体和自由交还给了民众自己,但是以玩儿腻了、大发慈悲同时又表现出依依不舍的心态。
我想这是没人能感觉到开心的,它从头到尾没有想要积极接受人民的质询,以至于当谈到它决策所依据的人民的呼声究竟是来自于哪一种人民我们也只能挠头,如果是听证会那我们怎么没有听说?如果是我们自己聚集在公共场所所发出的声音,那那些发声的人为什么要逮捕呢,不应该大家和和气气在信访部门唠嗑 ?或者是通过专业的调研机构,但是又是怎么来的呢?在2022年年底回望过去的三年,有一种错觉,就是简中互联网中的讨论变成了一种时风飘絮的现象,能存活下来的只有与政治和政府无关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反对才被404,有时候质疑也是,这种质疑很多时候也在政府辟谣过后被打成了“有心之人”,以至于在面对社会事件的时候,如果不想犯错那就闭嘴——与其说是一种自我保护我更愿意称之为一种疲惫,这种疲惫最终导致了舆论全面的去政治化。但这种去政治化并不完全指政府放弃政治宣传,相反,不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亦或是经济层面都要求加强政治站位,那为什么说去政治化?是因为我们在各种程度上,都失去了与公权力对话的可能,在场域里面处于绝对的弱势,在互联网上讨论相关话题面临着各种监管风险,但互联网的以至于在简中网络传播信息需要经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我们发推发电报然后把截图转回来,然后再等着404;所有的不利发言可以被删除,互联网可以没有记忆,网友们可以没有记忆,但是所有的痕迹都在真正的有心之人手里,作为复数的民众有更多的生存命题等着解决,而真正记仇的反而的强者。我们这里不讨论公信力和反攻倒算的问题,我们只讨论一点,那就是我们在这三年里似乎所有的施压都是通过互联网这一非正式渠道,然后现在这一非正式渠道也和刀尖上跳舞没什么两样;我们上街去,突然就有一种梦回八十年代的感觉,再配合上今天突然的转变,我们甚至可以再次思考互联网究竟给我们的言论自由带来多少进步,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是不是应该抬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我们可能也需要更多根治在地社区和地域的自组织出现,以对抗这种话语上的无名化和细胞化。总之,我们要警惕自己变成符号的一部分被模糊掉,同时也要警惕麻木的丧气心态,由于层级所带来信息损失和噪声,可以通过反复播放和提高分贝来弥补,但如果因为担心和觉得无用而放弃发声,那不论如何转变都不会到来。
至于科学,我们也都知道,今天最新发现的科学好像在去年发表的科学里早已发现,换言之,科学也是和人民的声音一样是可以被筛选的,昨天我们还在依靠渲染国外的血雨腥风和国内弱势群体的同理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出最新的统计数码说毒性如同流感然后在新闻发布会集体摘下口罩。我们总习惯吐槽日本人讲话的方式忸忸怩怩,但中国大陆何尝不是呢?所有人盯着国家释放出的信息,从信息的平台、推出的时间节点、撰稿人等方方面面展开一如剧本杀的实景信息推理,政治具体到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一场文字冒险游戏。中庸之道连同辩证法在实践过程中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我们所有的辞令(尤其体现在外交和行政上),吸收了所有长篇大论的糟粕——言之无物,这甚至被当成一种弹性而饱受赞扬,但这种弹性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总没有弹在个体的头上,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它秉持的精神是一种毫无信念的实用主义,科学和理想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以至于病毒成为了中国大陆舞台上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打开今天的热搜,看到一女子八日自愈说病毒不如流感;广州专家说90%以上可自愈……我们像是在排练一出超长篇幅的舞台剧,觉得这里不够魔幻现实主义,那就打乱它的章节,加一点蒙太奇,但最后我们要落到一个结局,升华一个主题,那些篇章的小核心都只是为了烘托最后的理想信念:一切为了人民,相信科学,以及更多它想要说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人民的声音缺少一个听取的环节,而科学又变成了一种贴金道具。如果说这还只能说明国家自有打算,社会稳定才是第一要义,那这种稳定以及其带来的政治价值,它们背后的成本是不是太过高昂,在公权力面前不论是支持它所有决断的人还是持有疑虑的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它抛弃掉,就如同当年K12行业的雪崩也只是一纸条文的事情——那我们的未来还有什么确定性呢?尤其是建立在一个自视甚高,把自己架在神坛之上的角色,我们能说它真正从人民的实际出发吗?在一夜之间,它把它的公共卫生政策的基石从一端移到了另一端,同时在互联网目所能及的信息全表达了对这一决策的欢欣鼓舞,社会各界就差齐奏好运来,但相对的,三年以来的那些问题和成本,用这些没有感情色彩的词好像不好,就如同我们走一些弯路一样,我们改成“那些本不应该的失去的”,好像完全被按下不谈了,如同日历翻过新的一页一样,直接翻篇了。眼下的中国大陆,连“反思”这个词也被污名化了,这一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传统连带启蒙一起被打倒了,并连同反西方主义一起上了绞刑架,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谈反思,若是你真的要,那等待你的会是一句有完没完,永无止境地从当下开的大陆特色历史唯物主义成了相对主义最大的保护伞,也成了群众路线的最大阻碍。“我们反对的是核酸吗?我们反对的是口罩吗?我们反对的是志愿者们吗?我们反对的是那些可能受到影响的弱势群体们吗?不,当然不是,我们反对的是那些不由分说的隔离,一刀切的政策,污名化的导向,毫无同理心的执行者与高屋建瓴的……”这是我上周没有写完的一句话,如今我也不想继续再写下去了,因为还有一大堆烂摊子等着我被完成。
我们特色的制度习惯大包大揽,但在大包大揽之后呢?国家有难大家帮,我不下岗谁下岗,今天我稍微续一句,“我不阳谁阳”。一如八十年代突然的国企改革使得原本生活于单位系统的个人被推向了一个叫社会和市场的存在,它是洪水猛兽吗?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地说它就是,思想和观念需要一个转变的阶段,就如同大洋彼岸的台湾骤然放弃把大陆视作敌人一样,你可以树立起一个虚妄的敌人并将其污名化,但在迫使大众在耳濡目染接受这一概念之后,你不可以在不做任何思想建设的基础上,把大众推向另一个极端,往轻了说,我们说这是政治欺诈,往严重了说,这是把转型的所有成本,在不讨论正义的情况下,移交给了民众。一时间甚至还有一点点双轨制的痕迹,部分城市的常态化核酸点纷纷收起,取消了区域间流通的限制,而以上海为首的诸多城市还非常保守;出入一些公共场所已经不需要核酸,而学生还被管在学校里,一些服务业场所还需要48小时核酸;核酸点取消了,可一些行业还需要核酸,以至于人们在一窝蜂挤向医院和仍开放的核酸点;更不必说去药店抢购治疗发热药物的人们……而我们之前还在宣传“防疫”背后的政治账,今天就可以让民众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佐以一幅悲伤退场的漫画,充满了对民众的深深嘲讽,说句难听的,甚至让我感觉有一种调教的意味在。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内容是97年香港回归后,末代港督乘船离开香港时,他看着逐渐远去的香港,同样留下了热泪;而从联合公报到香港回归之间有13年,大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花了四个五年,而放开只用了一天,或者说一夜。
最后,让我来为大家汇报一下关于乌中的情况吧:或许是寒潮来临的原因,梧桐叶子落了大半,离秃头不远。各个路口的路障早已撤去,甚至只是存在那一夜而已;我如同那个下午一样依次走过四个路口,乌中路口的牌子也都还在,可能只是不存在于那一夜,甚至不到一夜;路口零零散散有几名交警,但也都只是站着看,工作日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安福路段和长乐路到安福路的乌中路,道路两边立起了铁皮,但大抵是用来便利路面整修,并不是用来阻止群众聚集。餐馆和商店们正常营业,一如往常,甚至有不少店铺已经开始为圣诞做准备;常熟路口的圣诞饰品店甚至有不少情侣在拍照,一切都很平静。
这就是在一周之后关于乌中的全部。
我踩上单车,去镇坪路取眼镜,之后顺便去定西路吃饭,顺着光复路沿苏州河西南行至定西路,在武夷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余光瞄到旁边正在更新的街道外墙挂的大海报: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习总书记当年考察上海时提出的重要理念,它旨在回答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我之所以印象这么深刻,也是因为去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时,它和“15分钟生活圈”一起成为多次被提及的概念,那个秋天我伴着落叶穿行在普陀、长宁、徐汇、黄浦……而谁又能想到,我再次回到上海已是一年后了呢?
我低头看了眼微信消息——我把之前完成的小样发给了我的朋友看。
“加油啊!人民的力量!”
红灯转绿,我继续前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