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過寒冬的方式是合作行為而非進化論(下)
一年多過去了,下篇還沒寫,疫情卻也依然持續,近期甚至在臺灣加劇。然而,這段時間我們也更清楚的看到世界的連動,即使隔離仍如此的緊密而難以分拆,當然也包含人性善惡的互動。上篇提及合作行為並非如進化論預設的果,而是存活的因,此篇延續 Survival of the Friendliest 的內容和討論並以張君玫的軌道政治:我們會在中途相遇嗎?作延伸和補充,希望在批判四起的輿論中探究多元的互動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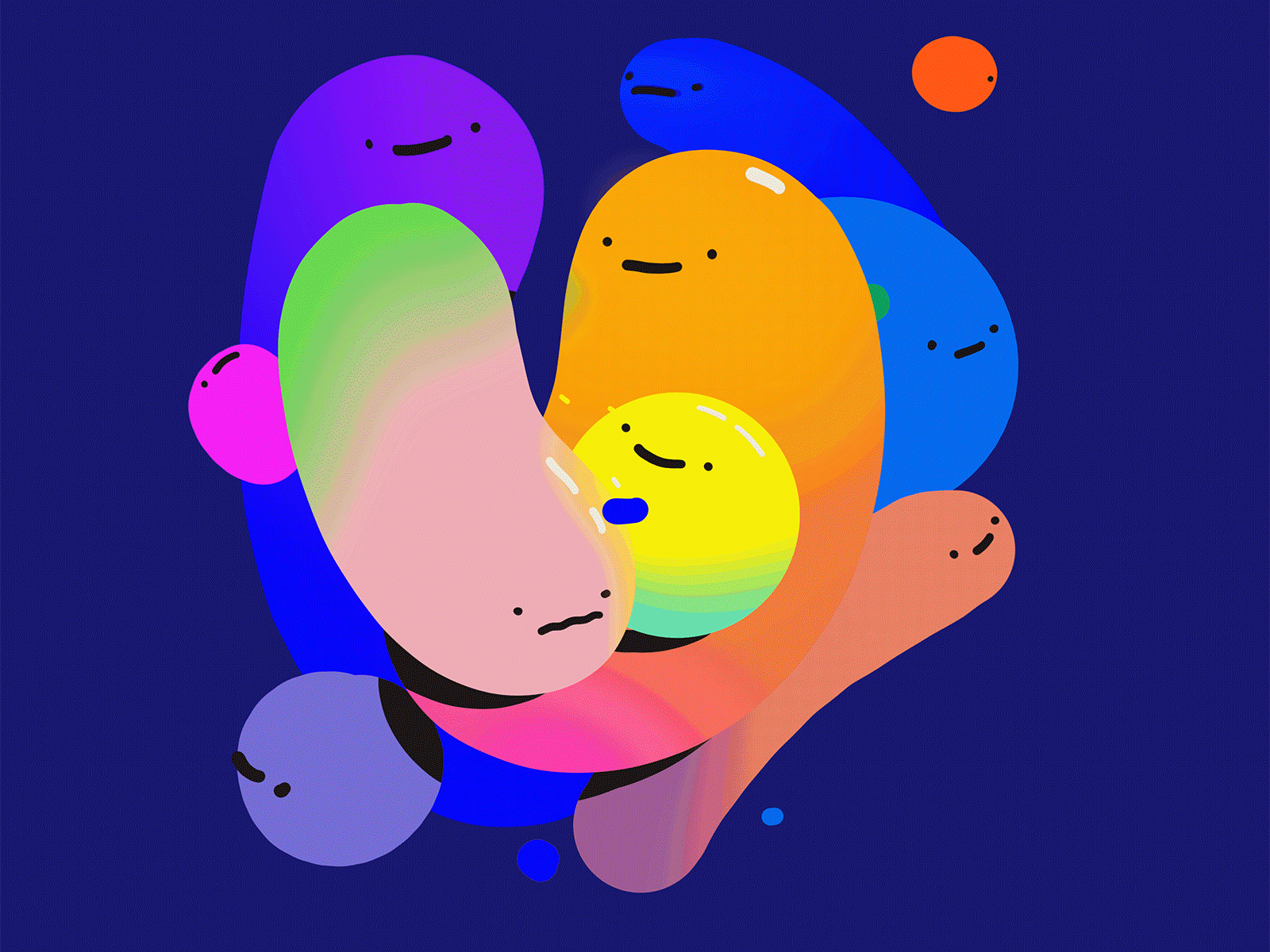
從疫情甚至疫苗施打在各地發展的差異,便能看出環境的影響力。對於多數動物而言,可能是溫度、濕度或其他環境參數,對人類來說甚至有更加複雜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等等。然而,正如 Clancy 所述,環境以至於生態猶如一個網,也包含在同一個地方共同存活的其他物種。以珊瑚為例,他們會形成保護自我的礁岩,減慢海流對自身的侵蝕,同時也成為許多生物的棲息地,當中更有許多物種演化出保護珊瑚的行為。因此,若一物種得已改變和其他物種的關係,那將有機會為後代創造更適合生存的環境。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則是微生物之間神秘的關係,簡單來說就是在培養細菌時,不同菌株得以在共同的環境下生長,不過一但將不同的菌株分離,僅有一小部分能獨自存活。目前甚至估計有98%的細菌是無法在實驗室中單獨培養,雖然說這樣的現象有諸多原因,但也不得不承認細菌無法獨自生存,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共同演化出對彼此的依賴性。對進化論來說,這想必不太明智,不過這樣相互依賴勢必有其優勢,而黑皇后假說正是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
黑皇后假說提出生物因為共同環境中其他物種所提供的相同功能,而退去自己重複的機能,換句話說就是耍廢來節省多餘的能量使用。黑皇后假說對立於更廣為人知的紅皇后假說,也就是因為需要面對演化的軍備競賽,不停地適應新的武器和防禦來避免滅絕。然而,有別於大家常認為演化是朝著日趨複雜的方向前進,生物減少自身非必要的基因和其所帶來的能量消耗其實相當常見。
黑皇后的名稱正是源於傷心小棧 (Hearts) 類似的機制,在分數越低越好的此遊戲中,獲得黑桃Q是最高分也象徵著高持有成本,但若同時取得其他分數卡卻能增加其他人的分數或減少自己的分數。因此,黑皇后假說中持有如黑桃Q功能的生物便成了關鍵物種 (keystone species),提供許多物種好處的同時,也可能間接避免和依賴自己的他們競爭,猶如先前提及的珊瑚一般;依賴他人的物種則得以減少能量消耗,回歸上篇創造緩和環境以加速演化的可能,說明了生存並非一場零和遊戲。

數億年前,古老的藍綠菌 (cyanobacteria) 被植物的祖先吞沒,他退去了獨自存活的機能成為了大家知道的葉綠體,為那些提供自身緩和環境的宿主們實行光合作用,形成了遍佈世界各地新的生命形式。在這樣的脈絡下,長期和諧共處可能才是創造真正共生關係的演化先決條件,也就是說:
演化並非一場軍備競賽,而是相互依存的各國之間的和平條約。
Evolution is not a weapons race, but a peace treaty among interdependent nations.
說到葉綠體,張君玫從古生物學家 Brasier 以奴役 (enslavement) 形容這樣的吞沒行為,來探究這種敘事所反映的資本主義軍事殖民意識形態,並以 Margulis 爭議性主張的包含葉綠體、粒線體和鞭毛體皆原是獨立的個體,和蓋婭假說來論述我們經由環繞和包裹以建立新的生命形式,而人類也早已是跨物種的雜揉體 (trans-species hybrids)。延伸到整個宇宙,所有的天體形成複雜的相互牽引,所謂總質量核心的質心 (barycenter) 也非固定不變,而是取決於系統中無數天體的運行和狀態。因此,在這樣的環繞、包覆、折疊、展開和纏繞中,張君玫道出:「地球生命的巴洛克形構早已經是一種藝術創作,但同時也是無法漠視的界線政治。」
回到當前的疫情,張君玫以能動實在主義 (Agential Realism) 的形象,也就是事物並無獨立存在且利基於非二元的全體,來形容病毒造成分裂的同時卻又形成溝通。另外,病毒甚至帶出了跨物種生命政治 (trans-species zoopolitics),不停地在物種間互動輪迴,寄生與共生早已是在大大小小的尺度上交織難解的複雜關係,兩者之間的界線也從未分明,換句話說:「各種生命形式,包括以往不被視為生命或被視為缺乏獨立性的形式,都在不同尺度的演化事件中形成共生、寄生、合生的反饋迴圈,以及訊息共享的延伸系統。」
延續此觀點,不管是病毒、人類或天體之間皆是存在於既危險又能動 (agential) 的動態互動,但即使科學使我們深入微觀世界又望出星系宇宙,在這些微小和廣闊的尺度間,張君玫點出:「對人類來說,中間總是太平庸,而日常過於繁瑣,此時此地則是所有迷惘的質心。」或更直白的說:「我們可以計算出一個行星相對於地球的軌道傾角,卻完全不了解我們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軌道有多偏差。」

回到 Clancy 較正面的結論,人類正是在全球利基上建立了緩和環境,像是農業減少挨餓、促進和睦的文化和避免疾病的醫療,即使當前受到了挑戰,我們仍不停創造緩和淘汰的適應性,只因這些抱團取暖或是使用工具的行為遠遠比基因變化要來得容易傳播,我們的基因反而也受到文化和行為影響。全球化的當下,我們的合作行為加速了科技的進步,技藝和創新也得以有空間發展,迅速的疫苗研發亦是近期最好的例子。即使仍能看見許多粗暴的惡意,長時間下來人類已經成為更溫和、更合作的物種,睪固酮濃度也顯示較祖先低,可以說是複雜文化行為的出現讓我們馴化了自己。所以,對於那些執念達爾文進化論觀點的適者生存和暴力美德,就請他們放輕鬆吧~
與此同時,在疫情前我們可以很輕鬆的批判如瑞典以一命換取61個工作的放任,但封城後卻又各自在個人和群體利益間獵巫。疫情雖然模糊了善惡也凸顯了不平等與隔閡,但當中複雜的互動,像是政府的措施、國家文化背景和人民的選擇拉鋸,不正是讓人好奇、值得探究和深入了解張君玫所說,社會、政治與文化軌道偏差的好機會嗎?
*同時發佈於 Medium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