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李峻嶸:如何顛覆群眾的常識?——左翼組織斷裂的困境
本文爲「低語與行動:反送中/大運動中的左翼聲影」專題訪談之五,點此閱讀專題序言
訪談日期|6月28日
訪談地點|尖沙咀
受訪者|李峻嶸,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前「左翼21」召集人,現為網媒「夜貓」媒體的核心成員。醉心足球,積極考慮將花在社運的時間,轉投在一年看二百場足球賽的目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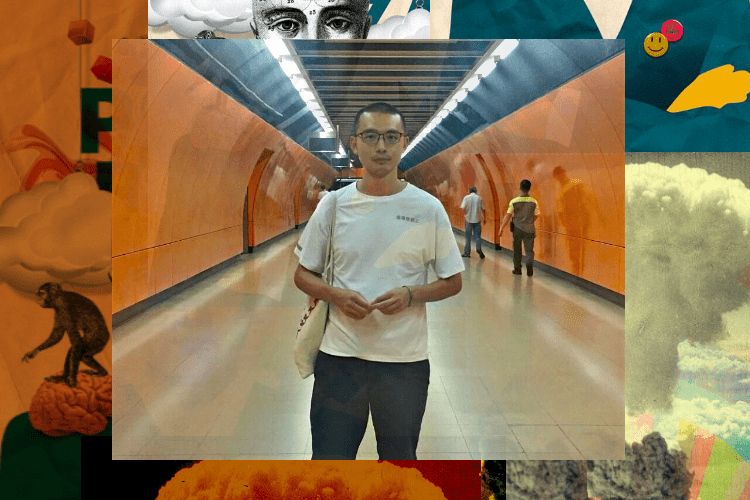
1. 與群眾常識的距離
懷火:今次的大型運動中,你覺得是什麼「基本常識」支持人們走出來?
李峻嶸:恐共呀,對自由的執著呀,這是主流香港民眾的常識。為什麼這件事會變得那麼大,甚至一些既得利益者都會出來,這是因為整個修例可能令到大陸的司法制度在香港的影響力會愈來愈大,侵犯在香港的人的自由,所以有這麼大的反彈。
我早前有一次,有同事說有很多同學去完6月9日遊行與12日行動以後,有很多運動創傷,當時林鄭還未讓步。他們做了一個分享會,我問一個同學為什麼你不開心?他們說的我完全不能明白:「原來警察不是保護人民的!」喂,你讀過社會學入門,馬克思的分析告訴了你,警察是統治階級的工具,為什麼你會幻想它保護人民呢?他說:「為什麼我上街佔領一下,都要這樣趕走我?」這個過程就令到他很創傷,很憤怒。
你見到的是,原先的常識,比我想像中更要根深蒂固得多,那我就明白為什麼自己沒有行動力了。因為我沒有幻想過它會好,它那麼壞是正常的。所以我也開始明白,為什麼有人覺得那麼少福利不合理,但他們還不鬥爭,人們覺得是正常的。反而他們覺得警察打人是不正常。
懷火:我自己覺得,這是因為人們無法看見那些太過滲透日常、令人習以為常到從來都看不見的社會運作原則。你有一篇文章【註1】提到遊行示威的自由,去中信大廈外面的集會,有警方不反對通信書,你用催淚彈掟我?你會覺得那些自由,都是中學有教過的常識呀,我也覺得我自己的常識被撼動了。
李峻嶸:問題就是這個嘛。北京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動搖你原有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在經濟上面就被人奴役到習慣了啦。那是「守」與「攻」的問題,「守」就容易動員到人,「攻」你就難了呀。
懷火:你提到對於運動中一些群眾訴求的批判,你覺得那是一種「失語」的狀態嗎?
李峻嶸:我想,我們不要常常爭拗「失語不失語」的問題吧,我不是「夜貓」〈左翼的失語〉一文【註2】的作者,但我理解所謂失語的意思,可能是你很難可以令到一場運動可以推進到一個方向,或很難在這場運動上滲透一些你想說的東西。又或者,講到想講的東西,但做的事不能改變到運動一些不良的方向。例如,當有人用「自由市場」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時候,平時我可能可以很明目張膽地去批判這些想法,但是到了現在這個位置,你批判它,就會讓人覺得你是在分裂這場運動,不識時務。
我自己就算反G20都要很大勇氣,那篇反G20和講居權的文章【註3】早在6月26日前已寫好,但我不敢在集會前發布。因為這些就是我罵群眾愚眛、自絕於群眾的表現。這些位置要如何拿捏,這就是所謂失語的位置。
過去整個星期,民眾運動導向就是祈求國際—在香港的語境脈絡之下就是西方—支持,這是自從2014年爭取真普選失敗以後的傾向。在你很迷失的時候,G20好像一個契機,但我不是對G20有任何期望的人。策略上,我並不反對國際聲援,香港之所以沒有如拉薩、新疆一樣的更大武力鎮壓,其國際性是其中一個原因吧。但是我反對「G20 Free Hong Kong」這句話隱含的含意:香港市民的自由需要西方列強去解放。這個口號假設了G20是個正義的集團,這跟事實是完全違背的。同時,這也不是為我們自己民眾充權或為自己奮鬥,而是祈求別人去解放你。
我見到有朋友提到阿桑奇被美國緝捕的事件、去小額錢債審裁處受訪時,又會揭露香港本身法制的不足,那些是很值得說的東西,但真的不會扭轉到運動的方向嘛。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師奶反送中」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在這些位置上我就看見我和群眾的距離。有人發起師奶反送中聯署時,我自己真的想像不到這會被人說成開玩笑。原來這是一件新奇的事,那麼多主流媒體都會訪問她的呀。
懷火:對於運動中釋放出來的政治化群眾,你的反應好像沒有其他行動者一樣熱烈,而是比較有距離。你認為他們有被組織的可能嗎?
李峻嶸:運動中釋放出來的力量,組織的可能是有的,但前提是容得下他們。你有沒有足夠的組織者去組織他們,有沒有那麼多的事情去給他們做?組織不是說要有就有,你要有資源、計劃、人,才做得到。
學究一點說,那些好像很隨機自發的組織爆發力很高,可以做到以前很難想像的事情,可以organise和coordinate到很多事情,可是它始終不是organisation。世界不會永遠都是革命高潮的,有高低起伏。你去到低潮期時,大家的分歧很容易浮現,做長期組織的話,這些都是要處理的。這跟左、右沒有很大關係。
我理解過去十年的趨勢,自從天星、皇后的鬥爭,社民連冒起時已激化了很多年輕人。但問題是,原有的組織沒有足夠的容量去組織這班人,因為出來的人太多。這班人被政治化以後,市面上出現比較右的言論,而那是更加容易吸收時,他們就會被這些意識形態、語言與修辭吸納。到現在這個現象也沒有解決。
早幾天我說不如搞組織,但讀書組可以留得幾多人,還是去搞選舉呢?如果真的以勝選為目標,那就會陷入選舉的邏輯,可以講得有多「左」呢,輸了又如何?組織到他們,又不一定可以在意識形態上,感召他相信偏左立場。我七、八年前認識過的年輕人,最後部分是會走去右邊,因為對家的行動比你激烈。那我們要同他們去鬥行動激烈嗎?我又覺得不是。
我想反問的是,你想爭取的群眾到底是哪些。群眾很多,所有人都「離地」的啦,因為「地」有很多。你在前排衝的是一班群眾,後排支援的是一班群眾,每人的目標與客觀環境都不一樣。你在家裡不出來的也是群眾,政治冷感的也是群眾,保守的也是群眾。社會有很多不同的「地」,那些才是你的群眾呢?這我就不知道了。感覺上,左翼常常「群眾」前「群眾」後,那你會覺得行得最前的是你天然的盟友。每人的目標與客觀環境都不一樣,組織沒有出來前線的人,又會不會是脫離群眾呢?
當然我自己連那些組織都沒有做,但我知道有認識的人有這樣的抱怨。
2. 經濟鬱悶轉化為「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激情
懷火: 我記得你有提過,要在經濟緊縮或有切實個人生活影響下,才會激發到人支持左翼的主張。在這段期間,這些群眾有沒有在經濟訴求上,被組織起來的可能?
李峻嶸:香港的難題是,隨街找十個人問「社會是不是很公平呢」,應該有八個人都會說不是,尤其是到了今天很多七、八〇年代積下來的所謂常識,已經全部都動搖了。如果你說左翼21有過什麼貢獻,其中一個就是進一步推翻所謂獅子山下精神、自己努力就會成功的常識。
但問題是這些的不滿、這些怒火,最後在一些什麼場合表達出來,再轉化成為什麼訴求呢?為什麼不是在爭取全民養老金時、要求回購領展、借錢讀書要負債上面行出來?大家覺得它不對但又不夠憤怒。憤怒會去了哪兒?就去了一些中間偏右的議題,反移民更加就去到極右議題了。
懷火:我也有同感。在經濟規畫的問題上如不用中港矛盾的視角,會走出來反對的人就再少一點了。
李峻嶸:是啊。理性分析和主觀感受是有分別的,這與身分認同有關,這一場運動你可以去講到很多「香港人加油」這種很肉麻的口號,但是你爭取全民養老金,你不會叫「香港人加油」,你感受不到那個身分認同的激情。我明白為什麼大家在林鄭讓步還是憤怒,但上了國際報章就很開心,這就反映了這件事是一個追尋身分認同的東西。
你會知道,其實《逃犯條例》過了以後,捉拿你的機會微乎其微,但你每一天在領展的商場消費或路過,哪一個對你的實質影響大一點?其實一定是後者。這很令人氣餒,人們不是完全不認同你,但是你動員不到人。所以我那種不以即時動員人為本的思路,人們才不認同。例如林鄭讓步,無論怎麼看都是階段性勝利,但是人們會覺得這不是一種動員的說法,我覺得否定運動的成就是瘋狂的。
我很多學生都會說,到了這一刻參與了這場運動這麼久,還是感到十分無力的呀,很多人參與今次這場運動,都不會期望成功。香港社會運動參與的一個很奇怪的特性是,在外國的話,你愈覺得你參與有影響的話,你愈願意去參與,相關系數是正數。但是在香港是倒轉的,相關係數是負數——p-value少於0.05。你覺得愈沒有希望的事,你才愈會走出來。但是這個現象只會在「政治」議題上面出現,到了階級議題,大家覺得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問題是,那個憤怒與絕望是一定有經濟基礎的,可是人們articulate(表述)出來就不是一個經濟的議題,全部變成了族群問題。當然也一定有對訴自由民主價值的堅持,所以在這一點,我就會覺得中間偏右的主流泛民仍比本土派可取,起碼他們以前不會打那麼多「族群牌」,現在他們也正在鬆動中。
懷火: 按你所說,我也能明白為什麼左翼在這個面向備受攻擊。工人這個角色本身,已經自動包括了基層的新移民婦女、移民家務工等。如果「香港人」身分認同政治無法動搖,左翼就總是會成為它的反面。
李峻嶸:這些在他們的語境之下,全都是負面的東西。族群有時成為了團結的障礙,不過紮鐵工潮時有爭取尼泊爾裔工人加薪,當時我是感到很開心的。
但是這個時代,人們是靠攻擊大台、攻擊左翼來去建立自己,一定要很鮮明地樹立一個敵人。左翼都有很鮮明的敵人,就是資本,但是好多人幻想同資本家合作嘛,那沒有辦法對吧。你認識自治八樓都知道,他們都對大台有不滿,但他們不會去拆別人的大台啊。你就自己搞另一個組織呀。
過去幾年自決派做的,就是要以「自決」在香港人這個身分裡面,加入一些左翼的元素,例如是對小店的關懷、香港人民生問題的關懷。我尊重這條路線,不過不看好。因為我覺得,符號以及符號的內容,不是你喜歡塞什麼入去都可以。「香港人」這個符號,塞不到一些左的東西下去,因為始終香港這個地方,在世界經濟體系的角色太古怪。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始終來自與大陸人的區分,你覺得我們比他們厲害,因為經濟比他們進步,這個身分認同始終講求維持香港的優越性,即自由經濟、低稅制,永遠很難變成質疑資本主義的東西。所以這是我常常說「香港人」身分認同在經濟議題上進步不了的原因,你是依賴著一個來自八、九〇年代的一個很美好的香港的想像作基礎,而你將過去二十多年發生的事,都歸咎於中國因素。
我讀到的英美新聞,無論是Jeremy Corbyn(英國工黨黨魁)或Bernie Sanders(美國民主黨2020年總統候選人),都可以滾起一些左翼青年熱潮。在英國,兩個不認識的年輕人走在一起,應該都覺得對方不會投保守黨,等於我們香港的年輕人覺得建制派愚蠢一樣。英國年輕一代向左轉,但是香港是右轉,那才令人覺得害怕。怎麼辦?
3. 左翼運動的客觀經濟條件限制:當下一場經濟危機來臨?
懷火:在「向左走向右走」的問題上,我覺得基本馬克思主義分析都會說,一定跟經濟基礎有關。例如英國,你真的會看見緊縮政策落實後如何禍民,而你在香港,樓價一直都是那麼貴的啦,沒有東西變過,一直又沒有什麼人失業的啦。沒有什麼會令一班人轉左。
李峻嶸:我明白啊。所以我會覺得,到了下一個資本主義危機打中香港,它一定要做緊縮政策的時候,你反應得來嗎?那是一個問題。上次1998-2003年那一期基本上反應不來。因為左翼21出現,所以我們才用了「左翼」這個字眼,這也是另一個貢獻來的,令到大家以為自己要面對左翼,雖然它毫無威脅,只是多了一個捱打的稻草人。
這個世界不是你有意志就會成功,你一定有一些客觀條件限制。資本主義一定會有危機,1998-2003年就是因為你本身的基礎太弱,所以變成你阻止不到政府去做那些私有化、私營化。但是其實領匯(2003年起,反對房委會向領匯出售商場物業的運動)雖然輸了,但政府都不敢再搞那些私有化機場等的計畫,所以也有它的成功之處。
在低潮的時候,我們要累積自己的基礎。危機的時候,誰可以掌握到那些話語權來領導那個「救經濟、反緊縮」的運動?這個其實很重要。有賴祖國經濟增長,2008年的危機在香港一點都不嚴重,但是如果大陸出現危機,這一定會牽連香港,那可能那時候左翼可以再重整旗鼓呢。不知道呀。
懷火:說到這裡,就算當下一個左翼的高潮可以在下一場經濟危機之下出現,但是中國因素會是更加濃重吧?我的觀察是,中國不斷發展大灣區、深港融合等區域間的去邊界化,就是為了做到危機消解的作用,但大家的關注會在中國加強政治箝制之上。
李峻嶸:那要看到時我們可以提出些什麼、可以把焦點放到哪裡了。所以我覺得要裝備自己,例如我現在都很想去看那些Green New Deal的東西,英美的左翼都要去想經濟出路是什麼,以及要如何去講。當然香港不一定有條件去跟,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又沒有天然資源。但是我希望可以從那些地區得到啟示吧。
你問我的話,最真心的一句是,出路都不在香港。香港的問題靠香港解決不了,對嗎?香港的問題是世界資本主義問題中的一小部分,香港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香港可以動搖到多少東西呢?問心一句,真的是很難。這樣寫好像我很沒有志氣,雖然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很合理的判斷。(其實志氣更高,即是要連結中國工運。)
香港沒有Corbyn與Sanders吧。長毛(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可能就生不逢時吧。把某人打造成香港的Corbyn吧,出來選,搞一個組織去捧那人。你去選啦。不好嗎?我去拉票不行的,我跟群眾的距離太遠了。
4. 面對鞏固現有常識的輿論生態:反思作爲左翼輿論平台的「夜貓」
懷火:那現在你以「夜貓」網上媒體這種方式介入運動,來自一個什麼判斷?目前做到了什麼?
李峻嶸:香港的政治生態是,你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北京做一件事,就將所有的注意力搶掉,釋放出群眾的力量,而你又接不住。這些力量會因此接受什麼呢?看《蘋果日報》、連登囉。右翼那些父權、排外的視野,是在所有議題上滲出來的。我們如何可以建立自己的輿論機器,在每一個議題上提供左翼的分析呢?所以為什麼說要有一個恆常的左翼網上輿論平台,本來就是想爭這一些東西,起碼人們不要看「輔仁媒體」(本土派網媒)啦。
你是在對抗常識嘛,就沒有那麼易明,你一定要長篇大論些,才可以解釋清楚。但是右翼是在鞏固原有的常識,動員一些本身我們已經有的想像與情感。但是社會運動就是要去顛覆我們的想像、既有的常識,甚至顛覆我們既有的情感。所以這樣一定是逆水而行,這是預料之內。這是原先搞「夜貓」想做到的事,但是做不到啦,所以才變成現在純粹以圍內人作目標而已。你只有輿論機器還是不夠,你要有組織基礎、行動網絡,三方結合才可以。
懷火:這個三方結合是什麼意思?
李峻嶸:三年前,立法會選完後,我們一些比較可以接受的議員差不多全部選輸了,只有張超雄和長毛(梁國雄)選得上,還要DQ了。在這麼惡劣的環境,我覺得要做到三件事,我過去兩三年都努力地嘗試:第一是要樹立一條清晰的左翼路線;第二是要一個左翼聯盟,因為本身的「山頭」太多;第三是一個左翼的網上輿論,你叫它平台又好、機器又好。
「夜貓」就是第三件事,但當然還是做不到。因為這些是結合在一起的嘛,你要有組織者、行動者、輿論製造者有機地連結,缺一不可,你才能做到一個清晰的路線。聯盟我有嘗試串聯過,但基本上做不到。
輿論機器就是「夜貓」,但現在做不到我原先期望的角色,所以變得愈來愈脫離行動者與組織者,因為你們只是一班寫手或者所謂的知識分子在寫嘛。「夜貓」自從上年年中開始,主要目標的讀者不過是同情左翼的人為主,也不是寫給所謂大眾看的。有人會認為我們很教條,那在某程度上是刻意的,我會覺得現在香港的泛左陣營裡面需要一個這樣的角色存在。我們全部都是修正主義者來的啦,都不是真的教條式的人。
我會接受某些人對我或「夜貓」的批評:只說不做,就是只說不做的呀,沒有人是全能的,美斯和王霜(女子足球員)也不守龍門。我覺得不是所有人也一窩蜂做同一樣事情,我做組織做錯的事情,要三幾個人收拾爛攤子,做來幹嘛?我們要去建立自己的組織,有組織才有自己的行動。
懷火:回到今次運動,基本上都沒有左翼行動的旗號,今次的情況有沒有某些個別的事件,本來可以做到多一些結合?
李峻嶸:很可惜,無。自從左翼21散了以後,我沒有任何一個我自己可以投入或者相信的組織,有很多事情想不到、做不到。如果左翼21曾經順利地運作過的話,優勝之處就是不同特長的人可以在裡面發揮自己的功能。寫文字的人寫、行動的人去行動,寫手與行動都可以互相配合。我理解當下的問題都是一樣,著重行動的人可能覺得寫手沒有「落水」參與,我不會說他們的批評全錯,但對我個人而言除了自己懶之外,沒有一班可信的同志也是一個原因。
以前有分工的運動,如碼頭工人罷工,本身就是一些左翼議題,那行動者、組織者、文宣製造者有一個很共同的意志,矛盾相對容易一點處理。可能左翼21當時還存在,亦有某些重要的人存在,大家的磨合沒那麼失效。現在是磨合的可能性都沒有,泛左陣營的不同網絡都有參加,但本身泛左的人就不多,又沒有合作,那就不大可能令左翼旗號出現。
左翼本身就是超級弱勢嘛,自己內部又有N個問題,簡單而言就是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事情來得太快,你準備不來,當然可能你有準備都準備不到,因為你本身的問題太過嚴重。出路永遠在左邊吧。但我們如何行去左邊,我不知道呀。
以往左翼21與其他平台期望做到的不果,我過去三年嘗試也是做不到。我計算過我花在這些事情上的時間,可以看上二百場足球賽了,其實花時間看掉這二百場足球賽可能還比較好,想到都開心。問心的一句是,我自己抑或在這幾個星期開始什麼都不理,抑或就搞組織。前者的機會較大,因為我懶,還有我不懂搞組織嘛。我期望可以有一個聯盟,嘗試砌過但是砌不到。等你來吧,等年輕的左翼分子出來吧。
註1:李峻嶸(2019)〈從今次運動中尋覓自由〉,見「夜貓」,見2019年6月25日,http://theowl.hk/2019/06/25/從今次運動中尋覓自由-李峻嶸/
註2:覃俊基(2019)〈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見「夜貓」,2019年6月18日,http://theowl.hk/2019/06/18/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
註3:李峻嶸(2019)〈我昨晚沒去愛丁堡廣場,我去了遮打花園〉,見「夜貓」,2019年6月27日,http://theowl.hk/2019/06/27/我昨晚沒去愛丁堡廣場,我去了遮打花園-李峻嶸/
文|懷火
圖|Anna & Trim
日期|2019年8月2日
懷火網站連結:www.ReignitePr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