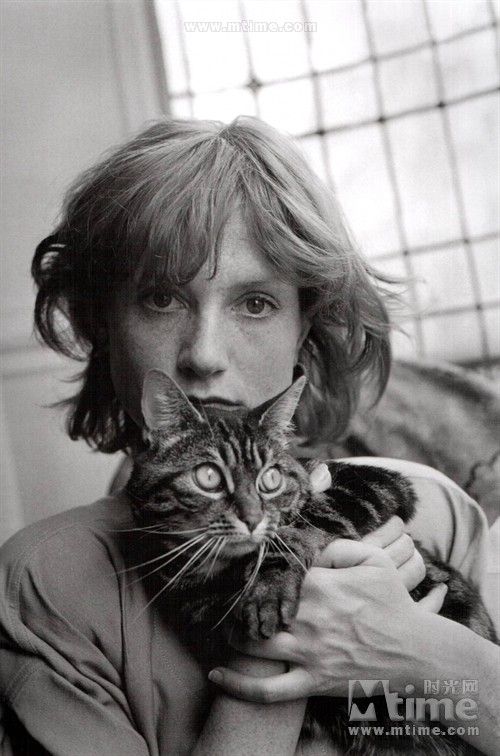我这个乡下女孩,在陆家嘴轻奢店打零工
(原文首发于「人间thelivings」/2020.6.24)
1
早上8:30,我等来了第二班较为空旷的地铁。这个时候,排队的位置最好位于队列的第一二位,方能在地铁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以最快的步伐,一屁股霸占住一个座位。不然的话,就要开始上班前的“排练”——站立。
早高峰的7号线车厢内,除了有人偶尔发出咳嗽声和地铁轮对与钢轨摩擦出的刺耳噪声以外,没有谈话声,几乎所有的乘客都盯着手机屏幕——有的神色沉重,像是要去出席葬礼;有的干脆就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会错过中英文提示到站的广播声。
静安寺站一到,大部分乘客汹涌而出,在通往2号线的过道里,一群低着头的人如行尸走肉般向前移动。响彻在耳边的是节奏一致的脚步声,以及前方传来的一遍遍“请抓紧扶手,不要低头看手机”的机械提醒声。面包店明亮灯光,提醒我要买一袋吐司——我已经吃过早餐了,但为了熬过“上班的艰难时刻”,需要预备粮草。
我得在9:50之前到达陆家嘴站,不然就会迟到。不用出地铁站,6号口直走即是我上班的地方——上海国金中心商场,ifc(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它的官方微博如此介绍:“外形由国际殿堂级建筑师以璀璨钻石为灵感及顶尖建筑美学瑰丽打造,彰显当代都会的浪漫神采与魅力。全球高端顶级品牌旗舰店汇集在上海ifc商场,成为亚洲时尚新地标。”
推开通往商场的玻璃门,世界一下子明亮了起来,这里是商场“LG2”,负二层。温暖如春,飘进耳朵里的古典音乐令人心情舒适。接下来,是混杂的香味——我无法分辨出是香水的味道还是化妆品散发出来的脂粉味,唯一能确定的是,那是昂贵的味道,是我无法抵达的阶层的味道。
快10点钟了!我背着书包奔跑起来,这个时候,响在我耳边的不再是悠扬的小提琴声,而是店长的“迟到1分钟,白干1小时”的箴言。
站在前台的David抬起眼镜框后面的眼睛,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快去换衣服。”
我推开全身镜门,挤过挂满衣服的通道,到最里面的储物柜,取出工衣换上。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专门翻看了同款的卫衣和短裙的吊牌,卫衣的标价为“?2899”,短裙的标价为“?2999”。这是我打工史上最贵的一套工衣,也是我有生以来穿过的最贵的衣服,我算过,我要站131个小时才够买这件卫衣。
这套工衣是离职店员穿过的,还好尺寸合适,而前任留下的那双搭配工衣的、2000多块的运动鞋,硬邦邦的鞋底,狭窄的鞋头,并不适合我的脚型,还不如我80块钱的球鞋舒服。因为鞋的尺码不合适,我被允许穿自己的鞋子上班。
我边走路边扎起我那头乱糟糟的头发,从库房出来,David像是跟我宣旨一样说:“今天是你最后一天班,我们招到全职了。”
我在兼职签到页上写下我上班的时间“10:00”,应了一声“好的”。
“你可以问一下招你进来的人,其他店铺是否需要PT(part time)。”David说完,把手里的iPad递给我,示意给他拍照。
“不用担心,我刚找了另一份兼职。”我按下按钮,叫他看看照片是否可行。
他说没问题,然后把iPad的摄像头转向我:“你把衣服拉拉好——”
“等一下——”我跑进库房,从包里翻出一支口红,给自己暗沉的嘴唇涂上鲜艳的红色,再用手指涂匀,接着把沾了口红的手指在两腮上涂几圈。镜子里看上去精神百倍的自己,像是一个候场的演员。
“好了,可以拍了。”蹩脚的演员,对着摄像头挤了一个营业的笑容。David看了一眼“打卡照片”,确认没什么问题后,发送到微信工作群。
兼职店员没有太多的工作,特别是没有顾客的时候。整理完已经很整齐的衣架,我像橱窗里的塑料模特一样,站在门口,看着清洁工来来回回地拖地,不由得想起第一天来这里上班的情形。
2
那天与我搭班的也是David,我向他请教店员的工作内容。他说:“你只用站在卖场看好衣服就行。”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工作如此简单,问他是不是应该教我收银。他叫我不用担心:“我在就行了。”
“如果你去卫生间了怎么办?”
David说,即使他去卫生间了,顾客要看几圈衣服,还要试穿,再怎么着,他也回店铺了。我又不识趣地问他去吃饭了怎么办,David说:“我在库房里吃饭、休息,有事你叫我就好了。”
“这样吧——”他似乎是为了摆脱我无止境的问题,从衣架上拿了一件衣服,把我叫到电脑前,教我扫描吊牌条形码、查库存量,“如果顾客要别的尺寸,系统会显示店里是否有货,有些没货的,就要从其他店铺调货。”
交待完毕,David看了一眼手表,问我是11点到12点吃饭,还是1点到2点吃饭?
“我想12点到1点吃饭。”我给了一个超出范围的答案。
当然是不行。我问他为什么不行,他白了我一眼,说这是公司规定,员工照着做就行。我想,好吧,我的早餐还没消化,那选择1到2点钟吃午饭吧。David说他进库房去点外卖了,进去前,又像是想起什么没有告诉我,停在门口:“还有,卖场里不能看手机。”门刚“哐”一声关上,他又从门缝里露出半个身子,嘱咐我“好好看店”。
我站在店铺门口,猜测工作日的上午会有什么人来逛商场——老头老太过去了,中年人拉着舔冰淇淋的孩子过去了,年轻情侣乘着扶梯下来了,他们个个衣着时髦,男俊女美,仿佛T台上行走的模特。
“外卖点好了?”
David“嗯”了一声,捧着iPad走到门口的另一侧,站在那儿。我问他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吃饭,他给我推荐了商场对面的正大广场。
“有没有‘全家’之类的便利店?”我这么问,是因为点一份外卖,加上包装费和送餐费,至少也得30块钱,而我的时薪只有22元。估计陆家嘴肯定没有沙县、拉面或是桂林米粉的小店,更别提开在弄堂里的无名小馆子了。
David说具体位置他不清楚,叫我去那一块找找。看样子,他一直吃外卖。
为了打发时间,我们闲聊了起来。David是黑龙江人,可我完全听不出他有东北口音。他解释说,只有辽宁那边的口音会把人带跑,况且他在外面很多年了。今年过年,他不打算回家,倒不是因为节假日有3倍工资可拿,而是春运期间的飞机票价格够平时飞好几趟的,火车票也很难抢到。每年夏天,他都会回老家一次。他老家的夏天凉快,不像上海这么热。
David平时喜欢看电影,一般院线有电影上映,他都会去看。他也喜欢看书,只要去书店,至少会买一本书。包里也常放一本书,哪怕不看,也会带着。David说,休息的时候,他一般不去逛街,因为只要一进商场,就有种“来上班”的感觉。他原本是太古汇店的店员,因为这边店铺走了两个店员,公司把他调过来“支援”。他说零售行业的流动性很高。业绩好的时候,他一个月能拿一万多块,差的时候,只有几千块。
“今天就我们俩上班吗?”我问。
“还有一个人1点钟过来上‘晚班’,交接班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吃饭了。”
“那你今天上‘全班’?”我想起店长也给我排了两个全班——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去掉吃饭的2个小时,一直都要站立。David说他宁愿选择“上一休一(上1天全班,休息1天)”,毕竟出门一趟,来回地铁要花2个小时,干脆早上出门,晚上回去,错过晚高峰,还能省下两趟地铁费。
他问我,上班路上需要花多长时间。
“1个半小时。”
“你的钱都给上海轨道交通公司了。”
正聊着,他的外卖到了。我只能一个人熬时间了。我期盼有顾客光临,好让我有事可做,然而,靠近店铺门口的人,不是询问卫生间在哪儿就是问地铁怎么走。
就在我一个人发呆的时候,店铺里响起了另一种音乐——我以为自己因为站立太久出现了幻听,环顾四周,寻找声源,最后确认歌声是从天花板上的音响发出来的,笑自己像个神经质。
而我在店铺里的一举一动,全被墙角的3个摄像头拍摄下来了。我下意识地调整起自己歪歪扭扭的站姿,不一会儿,我的胃就发出“咕噜咕噜”的抗议声。
待上晚班的Angela换好工衣后,David对我说:“去吃饭吧。”
这简单的四个字,犹如吹响了解放的号角,我的身体和意志同时放松下来——哪怕这解放只是暂时的。
我套好外套,穿过来往的人群,推开商场的玻璃门,一股冷风灌进脖子。我来不及感受上海的寒冬,因为前方巨大的苹果标志占据了我所有的视野。我在屹立于空中的东方明珠塔面前停下了脚步,仰望着它——这里就是上海,在这座城市生活2年的时间感,远远大于我在另一座城市的10年。
从升降梯下来,或停下来等待游客拍好照片,或绕过他们的镜头。游客们笑容满面,以上海地标为背景,对着镜头比着胜利的手势。一架环形天桥跨越世纪大道、陆家嘴环路、陆家嘴西路,处于陆家嘴中心区交通繁忙的交叉路口,站在这道“观光回廊”上,上海中心大厦、金茂大厦以及环球金融中心尽收眼底。
天桥自2010年建成后,成了大量游客的打卡之地——它在斯派克·琼斯的电影《她》里多次出现,是杰昆·菲尼克斯饰演的男主人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据说,陆家嘴之所以成为电影主要取景点之一,是因为导演认为这里符合“未来城市”的想象。
一个家在浦东的本地朋友曾跟我说,她极少来陆家嘴,这里是外地游客和无数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们统治的地方,她“一个乡下人消费不起”,来这里的话,“讲究身上多装几张信用卡,最好是金卡、白金卡,那就不用掏钱,哪儿都去得的”。
我这个外地来的乡下人,穿过人群熙攘的天桥,来到对面的正大广场,在地下美食城绕了两圈,也没有找到便利店。我问了几个人,他们告诉我,停车场里有个“全家”。虽然不是饭点,但全家的顾客比美食城显然多一些,我等了几分钟捞到一个空位,坐下来,打开热好的便当。
坐在我旁边的有送外卖的小哥,有与老公视频通话的商场店员,她一边吃着关东煮,一边与老公比较着,是她去看他、还是他过来上海划算。算来算去,都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老公叫她请假去他那里,给她误工费。
“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啊?”她说。
最后,关于这场见面的计划不了了之,商场店员说,等忙完圣诞节再谈。
吃完便当,我好像更饿了,临走前,我又买了袋吐司,以防熬不到7点钟下班。
3
iPad从David手里转到了Angela手上。她说,自从公司不让玩手机后,她只得站在摄像头的死角处,拿着店铺的iPad看看会员的朋友圈。她提醒我:要对进店的顾客打招呼,顾客离开时,要跟人家说“拜拜”。
这些新增的规定,源于最近业绩不好。Angela说这家店铺走的是“轻奢小众路线”,而不是年轻人喜欢的潮牌,导致来店里的顾客大多都是中年人。她的很多朋友宁愿多存两个月的零花钱,选择PRADA、GUCCI。没有大牌潮牌,那些偶尔进店的年轻人连冲动消费都冲动不起来。
“你看,这个商场里有哪一家的店员,会像我们这样站在这么靠前的位置?”她反问道:“而且,我们店铺的灯光没有别家那样明亮,这也是原因之一,但设计师说我们品牌走的是小暗黑风格。”她加重了“小暗黑”的发音,使得这句话听上去嘲讽味十足。
“我们店里的女装,只适合瘦子穿。”我说出自己的发现。
“你说对了!”她说店里的男装尺码最大的是XXL,女装最大的只有38号或者L,而一般的女装尺码会有40、42两个号。她由此推测,公司的买手是个“死直男”,所以才不买大号的女装。
是的,很多女顾客,常因为没有合适的尺寸而放弃购买。这个时候,好像那件衣服在对她说——“你不配”。
Angela和我聊天的时候,David就拿着iPad打发时间,或摆弄已经很整齐的衣架。
这时,来了一位女顾客,我自觉地迎了上去。一旁的Angela快步走到我前面:“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顾客逛了一圈,没有看中任何衣服,离开了。Angela拉着我的胳膊,说:“我们是这样的——这个顾客是我的,下一个顾客是你的,轮流来。”她说这话的样子,十分神似上午David怎么也不教我收银的样子。
我如当头棒喝,立即跟她解释:“我没有提成拿的,只有每个小时22块的死工资。”怕她不信,我又走到前台那边,找到夹着我签到页的文件夹,翻到兼职协议的那一页,指着“工资为人民币22元/小时”那一行字给她看。
全职店员有业绩压力,每个月必须完成销售指标的50%之后才能拿提成。Angela说这个月店铺的销售指标是45万,每人要完成9.5万。如果当日店铺营业金额小于11000元,全职店员要写报告,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开单,写好的报告要发到微信工作群。Angela最反感写报告,光是苦思冥想各种“没有开单的原因”,就能让她想到头秃。
“幸好公司没有禁止同事们上班的时候聊天。”我说。
“如果不让我们讲话,人肯定走光了。”Angela说。
刚入职一个月的Angela是上海本地人,与父母住在一起,应届毕业生,专业是国际商务,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早就放弃了做个OL,一个是觉得坐办公室没有意思,二是觉得如果进不了大公司,也没什么发展前途。她也说不上多么喜欢奢侈品零售行业,只是做这一行的回报都是肉眼可见的,她希望自己以后能去时装周看秀做买手,虽然达成这一愿望很难。
她看了下手表,说她要进去点外卖了:“我前两天胃疼得不行,大概是因为公司不规律的吃饭时间造成的。”
“这个吃饭时间,很不合理,为什么不跟公司反映?”我问。
“你去反映啊?”David冷不丁道,叫我不要执着于这些细节,公司的规定,员工要遵守。
Angela什么也没说,进库房了。
“这件毛衣,你身上的那个颜色有吗?”一位女士拎着一件黑色毛衣,指着Angela身上的白色毛衣问。
“没有了。”Angela答道。
“我喜欢她身上那个颜色。”女士对站在她旁边的男人说。
“那你总不能从人家身上扒下来吧?”男人说。
Angela在一旁尴尬地笑着。女士似乎觉得这样的要求太过分,更何况再好看,也不是新的,于是,他们离开了。
又进来一拨客人,他们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把那些打6折的衣服翻过来、又扔到一边,再去翻另一叠衣服。待他们走后,我把弄乱的衣服重新叠好。Angela称呼那些试穿了衣服没有购买的顾客为“渣男渣女”——“试了,为什么不要?”
“请问李小姐是——”送外卖的人站在门口。Angela接过外卖,说她进去吃饭了。我好像也有点饿了。
推开库房的门,里间传来电视剧的声音。Angela坐在小矮凳上啃着汉堡,眼睛盯着放在货架上的手机屏幕,我问她在看什么电视剧。
“《庆余年》,挺好看的。”她问我要不要来根薯条,我晃了晃手里的吐司,谢绝了她的好意。
“明天你和店长搭班,就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Angela说,她说这话听上去有些“挑拨离间”,但她和店长有点八字不合,或许是因为她们之间有利益竞争的关系,或许是因为她不喜欢店长过于直接的讲话风格。然后,她没头没尾地说了声“恭喜”。
我正纳闷,她加了一句:“恭喜你快下班了。”
我笑了,叫她继续加油。
在店里站了8个小时,腰疼得快断了,下班回去的地铁上,如果运气不好,没有座位的话,我要在挤满人的车厢继续站1个小时。然后换乘公交,回到家差不多9点钟。
这个时候的我,澡也不想洗,只想刷手机,看一些不费脑子的综艺节目,来舒缓我一天的劳累。别提什么看书这样费神的事了,至于写作这样需要创造力的脑力劳动,我也提不起任何欲望。
此刻,我只想躺平。
4
第二天,7点15的闹铃响起之后,我又赖了15分钟的床才起来洗澡。8点10分出门,步行去公交站的路上啃面包当作早餐。坐上公交,转乘地铁,重复昨天的工作。
上了班,我算是理解了Angela的话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你昨天拍的照片看上去像40岁!”——这是店长与我见面后的,对我外貌的评价,她还说有人问她:“你们的PT怎么不化妆?”
“David也没化妆啊。”我笑着说。
“他是男的。”店长还没等我反驳,又嫌弃起我的头发:“你都快没脸了,要把头发扎起来。”
我答应了她扎头发、化妆的条件,但是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像David那样戴框架眼镜。明亮而刺眼的灯光,让我戴隐形眼镜的眼睛酸涩不已,我怕她不答应,加了一句:“我右眼弱视。”
“没问题。”她说。
“哇,你现在的样子好像阿拉蕾!”——这是店长见我换上框架眼镜、扎了头发、涂了口红后的样子的评价,真是“给一个耳光,再给个甜枣”。
“昨天业绩怎么样?”我换了个话题,“白天都没有开单。”
“昨天晚上生意还不错,做了1万3。”店长说她要去库房点货了,叫我看店。
我巡视着衣架上的服装打发时间——店里的经典款是整件衣服印满了标志的那种;设计款是不规则剪裁、或不同布料元素拼接的那种,以女装为主。一些女顾客评价,店里简单设计的男装比女装好看多了。
“你读大几啊?”不知什么时候店长出现在前台的位置。
我告诉她我毕业很多年了,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辞去了固定的工作,现在打一些零工,交房租、养活自己。
“我太佩服你了!”店长感慨道,说在上海每个月至少得有1万块的工资才能活下去,她又问我是不是本地人。
我摇摇头:“安庆的。”
“我是合肥的!”店长说,她跟父母住在一起,省去了房租和许多生活用品的开销,“我要是一个人在上海,肯定活不下去的。”
我跟店长说“去下卫生间”,其实是去外面透风抽烟。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学会了“偷懒”——站累了,去库房里,坐在垃圾桶上,喝口水或啃块面包,又或者说“去下卫生间”。
即便如此,时间还是过得很慢,一根烟的功夫,我回到店铺,继续当门童。
左耳听着商场的古典音乐,右耳听着店铺的流行摇滚。我以为“店员”这份不费脑子的工作,可以让我充分拥有我的脑子,然而,我的脑子里现在只有腰部的酸痛、腿肚子的肿胀。我将身体的重量从脚后跟移到脚尖,再让左右脚轮班支撑我的身体,然而双脚似乎无法承受94斤的肉体重量。我脑子里有一万个小人在呐喊:什么时候才能下班?
我得找点什么事情做做,好让时间快一点过去。
“你是不是不会叠衣服?”店长见我在叠被顾客弄乱的衣服,问道。显然,我眼中的“会叠衣服”与店长所说的“会叠衣服”,不是同一个标准。
“你不教我,我怎么会呢?”我向她讨教正确叠衣服的方式。她打开我叠好的卫衣,告诉我要按照衣服的肩线来叠,吊牌要塞在衣服里面。末了,她说我没有上一个PT会叠衣服,她没教人家,人家还是个男的。
我尴尬地挤出了个笑容。
虽然店长嘴上刻薄,但对我还是挺好的,叫我站累了就去歇一会儿,15分钟以内回店铺即可。
晚上9:30,店里大清洁。做清洁的是一对父子,父亲头发花白,挥着鸡毛掸子,与他儿子说了句什么。熟悉的乡音,让我感到亲切,问他是不是安庆人,他回过头来说是的。就这样,我们用家乡话聊了一会儿。
他说,他在这家公司做了5年的保洁工作,满60岁后,公司人事说他可以退休了。他在上海只交了5年的五险一金,又没有居住证,哪有什么退休金可以拿?他年纪大了,再去别的公司应聘也没人要他了。好在后来他儿子承包了保洁公司的业务,他才能继续跟着儿子做保洁——他今年64岁了,身体硬朗,每个月能挣到五六千块的工资。对此,他很知足,哪怕不再有公司给他交五险一金。
他的儿子站在门口望风,看大厅的“楼管”是否走过来,因为商场不允许在营业时间打扫卫生,必须在10点以后才行。商场里的店铺大部分是自营店,但要跟商场的店铺一样遵守规定。
5
“COACH又搞了个网红在门口摆拍。”店长把她出门巡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评论那个网红的气质不怎么样。
第三天来上班前,我在家里先给自己的腰上贴了一排膏药。站了2个小时后,才发现膏药根本无法缓解腰痛。店长说她站久了会静脉曲张,David则是脖子痛。
David一来,店长就把我撇到一边跟David聊天去了,说今年业绩不好,也不是这一家店——像LV的店员去年还有一个月拿两万块的时候,今年就不行了,“大环境不好”。店长说去年她还有钱出去旅游一趟,今年就没钱了。然后,他们又提到一个叫Selina的人,似乎是公司的高管,店长说这人总在她休息的时候打电话找她,David则回应道:“她还老爱在群里发一些打鸡血的话,还总@我,我都懒得理她。”
“我们上班的时候也不是一直抱着手机不放,有事的时候才看下。现在好了,硬性规定我们不准玩手机。像XX店里,他们玩手机比我们厉害多了,也没影响做业绩……”店长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她凑近David的耳朵低语着。
“加拿大鹅又在排队了。”David探出身子,说道。
“他们家一天业绩就做了十几万。”店长说。
店长嫌我晃来晃去让她眼晕,递给我一个粘毛滚筒,叫我把衣服上的浮毛滚一滚。对于她的安排,我感激不尽,我终于可以暂时忘却我腰痛的存在了。
下午来了几拨客人,一拨人扫荡了打折的卫衣,一拨人买了最新款,我们忙活了一阵子,都很开心。店长和David高兴的是有提成拿,我高兴的是时间过得快。
晚上7点钟一到,店长就下班了,她今天是“早班”,剩下我和David两个上全班的。
一个保姆推着轮椅停在了店门口,坐在轮椅上的阿姨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用上海话问我是否来了新款卫衣——她上次买的卫衣她孙子不喜欢。大概10分钟的功夫,阿姨在David的推荐下,选了两件觉得她孙子会喜欢的卫衣,一件印着英文单词,一件印着某个朋克乐队的头像。她把信用卡递给站在旁边陪她的那个保姆,叫她去付账,说她累了得歇会儿——她说的“歇”,就是坐回轮椅上,像宝宝走路走累了坐回宝宝椅上。
结完账,她们客气地说“谢谢侬”,推轮椅的保姆问坐在轮椅上的阿姨,如果这次买的卫衣她孙子又不喜欢怎么办?阿姨说,“给他表哥穿好了,反正他们差不多体型”。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对夫妻,两具五短身材全身都印着潮牌的logo。女人试穿了几件卫衣,在红色和黑色之间徘徊不定。男人说黑色的已经有好几件了,这次该买个红色,看上去比较衬肤色。女人听从了男人的建议,男人付完钱,夫妻俩挽着胳膊走了。
晚上的生意不错,David忙着结账,我忙着整理衣服,对着一个个进来的顾客说“欢迎”和“拜拜”。时间在忙碌中过得很快,离10点钟还差2分钟的时候,我问David可不可以先去换衣服,然后下班。他说不行,“要拍照”。
不用说,这又是公司的规定。David说,之前有个店铺的员工早下班关了店门,把巡店的老板关在了门外。
我端端正正地站好,等David拍好监视器的照片,迅速换上衣服,一路飞奔——如果我不快一些的话,会错过回家的末班公交。
10点后的2号线比起7号线要热闹得多,有外国人聊天,有人戴着蓝牙耳机打电话,还配上各种手势,像是在对车厢的乘客做演讲一样。而这个时候的7号线,为生活奔波了一天的上班族们,面如死灰地刷着手机。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几个没有座位的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席地而坐。
6
店长和Angela连上了两天班后,这一天只有我和David两个人上全班。
拍打卡照片的时候,David叫我去换上店铺的鞋,说今天有人来巡店。我问他巡店的人什么时候来。他说他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告知时间,目的就是突击检查。
两个人上班的时候,吃饭的时间就更奇怪了。午饭时间为10:30到11:30或下午2到3点,晚饭时间为下午4点到5点或晚上8点到9点。David说他随便哪个时间段吃都可以,叫我先选。自然地,我选了较晚的时间段。
一个扎着马尾、穿着敞开式灰色毛衣的女人走进来,看上去并不像一个顾客。果然,“不要靠在那里”——她盯着我说。我摆正身体,忍着硌脚的鞋,以及腰疼。
“她是PT。”David从库房里出来,解释道。女人跟David询问了下业绩情况,离开店铺前,很温柔地嘱咐我:“不要靠在上面。”
“她就是巡店的吗?”我问David。
“不是,培训部的。”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男一女,看上去二十几岁的样子。进店铺后,他们俩开始挪腾衣架上的衣服,重新摆放了陈列台上的衣服和鞋子。我猜他们是“陈列部”的,男生对着David抱怨了一通公司领导,说他们脑子里有坑。拍完衣服陈列的细节图、店铺的全景图之后,他们才离开。David进库房继续吃他没吃完的午餐,“有事叫我”。
来了个顾客,看中了橱窗模特身上的羽绒服,叫我拿一件给他试穿。我叫他稍等,先看看别的衣服。推开库房的门,站在门口,跟David转述顾客的需求。
“模特身上就是最后一件了。”
我和David十分艰难地从模特身上扒下那件羽绒服,给那位顾客套上。他在身上穿了几秒钟,脱了下来,说:“不好看。”我和David不得不把那件羽绒服再给模特穿上。
“那人一看就不会买的。”David说。
我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察衣观人。”
活了将近30年的我,“察言观色”的功课都学得不够好,更何况奢侈品零售业的“察衣观人”。David听到在他预料之中的答案,带着一点骄傲,分享起他的经验来:要以顾客的穿着打扮来判断其是否“有钱”,这一点决定了TA是否有能力买得起我们店铺的衣服。如果顾客身上穿的衣服与我们店铺的价位差不多,他消费的概率很大;还有的顾客并不是全身上下都是大牌服装,看上去穿着一般,但是戴着名贵的手表或挎着大牌限量版的包包,或是穿着很贵的鞋子,这样的顾客也肯定会买。
“身上穿的是不是地摊货,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David说完,进库房继续吃午饭。
我一个人在外面看店,站在那儿大概走神了几分钟。一转头,只见一个穿着羽绒背心的顾客在那看衣服,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的。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试穿。”我招呼道。
“有优惠吗?”她用上海话问道。
“大部分6折优惠。”
她沿着衣架翻了几件,似乎没有什么满意的,出去了,没走几步,又折回店里,把手里的包放在凳子上,说她是巡店的。
“店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我是兼职,另外一个人在里面吃饭。”
“你去叫他出来下。”
“让我打个卡。”她对出来的David说。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叠纸,叫David签字,说她忙得午饭都没来得及吃。接着,她又拍了几张店铺的照片。
David问要不要给她倒杯水。她忙说不用,她还要去上面的店铺看看。
“幸好我点的是沙拉,没点味道大的东西,要是点了麻辣烫,味道传到店铺里,肯定要被说。”David说今天运气真是好,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还专门挑他吃饭的时间来。
我问他,等巡店的人走了我可不可以换上自己的鞋。
“你坚持到7点钟吧,那个时候公司的人都下班了。”他说。
晚上出来吃饭,推开商场的玻璃门,夜里的陆家嘴是另一番景象——东方明珠变换着各式各样的颜色,其他的现代建筑也加入了灯光秀。巨大的LED广告在震旦大厦以每次15秒的速度播放着。我身后的双子塔,“上海欢迎你”的字幕以中英文轮番滚动着。
站在冷风中的我,想起下午出来抽烟的时候,见到的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趴在商场外休息处的桌子上写作文,其中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是这么开头的:我妈妈说,上海人以前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现今,浦东有些地段的房价比浦西还要高。而浦西的南京路、吴江路、永康路等轮流被改造,襄阳路的市场消失了,许多有特色的小店也不见了踪影,能看到的是与其他城市差不多的商业街,以及完全一致的连锁店。
“妈妈,你看——萤火虫!”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她指着商场门口绿化带里闪烁的点点灯光,兴奋地大叫。
“宝宝,那不是萤火虫。”妈妈指正道。
“那是萤火虫……”
“宝宝,你好像没有见过萤火虫。”
不一会儿,传来小女孩大哭不止的声音。
尾声
店铺的电话响了,David拿起听筒:“喂,你好……她穿不下那双鞋……上次是硬塞的呀……全职明天过来……”
讲完电话,David告诉我,工资会在月底打到我银行卡里。
“站着没事儿多舒服呀,你干嘛要找事做?”他有点不解,然后又劝我,有这闲功夫,应该用脑子构思剧本,或者写一首诗,“对吧?”
“谢谢你呀。”我答道,“跟你一起当门童很有乐趣。”
我没有告诉他,最有灵感的时候,不是站在店里忍着腰痛的时候,而是上下班的地铁上。
最后一天下班回去的7号线上,我运气很好,有座位可坐。望着对面一排低头族的脑袋,想到自己2019年最漫长的一周终于结束了,顿时轻松不少。
是的,现在的生活虽然不稳定,承受着经济的压力,但我还拥有无价的“自由”,尽管这“自由”是靠着一点点的偷窃累积而成的——因为与同事没有竞争关系,而偷得一丝人情味;因为不是全职员工,而偷得不被公司条规束缚的一点喘息的自由,以及随时可以逃跑的自由。把自己租给他人,把自己留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