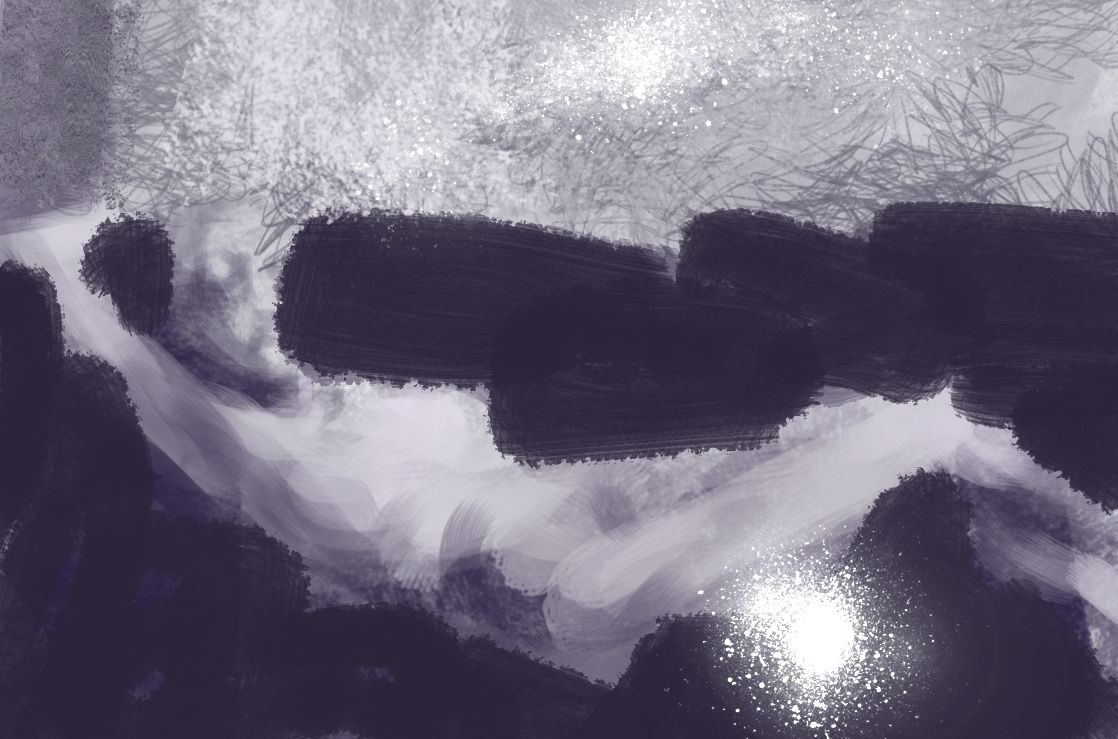想你们了,我的女朋友们
最近思绪纷杂,想的也多,但都没有成文。最近想写的有介绍以摩梭为主的现存的(男女平等的)母系社会;把之前文章中没说明白的部分再说明白,包括把中文中的性别不平等说得更彻底些,和之前的画的模型的一些解读。还有一些身心空间的练习啥的,都还没画下来、写下来。还有平时跟泽一起聊的,比如王者荣耀里的性别问题。这些想法拖着,没有重新整理和写下,反而随着回国越来越难而情绪起伏。

正文
图/文:iago
朋友问起我什么时候能回国,我也只能说不知道。我十分想念她们。要说我和泽在一起之后有什么重大的改变,这就是其一:和泽的关系,让我发现我与其她友人的链接是无可替代的,我时常感受到女性间友谊的共振、深广、坚韧。也因为她们,我学会了在外国与人的相处,而不是以无意识的封闭来将自己孤立于人。
最开始来到这儿时,我还很紧张,带着无意识的封闭,不太接触人,只会用惯性在买东西时跟人说谢谢。这一直持续到我们去另一个国家。我依然十分紧张,租房的时候怕被骗押金,总担心哪个人要坑我们一把。也不太敢跟其他室友交流,显得十分内向。但总归慢慢放松下来,不会带着惊吓。
有一天,我们找到了一家木屋,在谷歌地图上人们给它许多星,说好吃。我们点完菜后,老板,一位跟我妈妈一样年龄的女性,她看着我的眼睛笑着对我说:谢谢。
我确实被震撼到了,我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神,或者说,陌生人之间这样真诚的交流——只是一个道谢。我们只是陌生人呀……!可她却令我感觉我是存在的,我作为一个人在她面前,而不是一个付钱吃饭的AI。
我是因着这位可敬的女士,一位主管自己的家庭餐厅的女士,学会了和人说谢谢时候要看着人的眼睛,学会了看人要超越国族、信仰,只需看到人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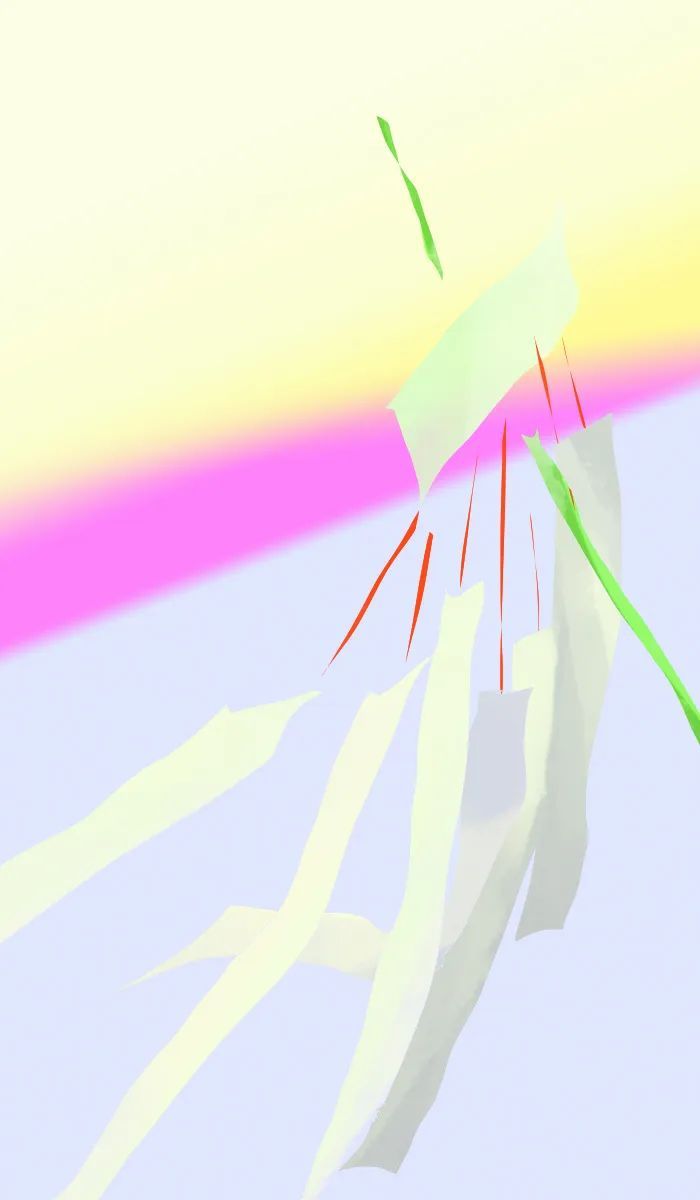
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友人们。想起了家里的客房,星星串灯垂下,我们在言谈之中共鸣共振。想起了那令人晕眩的圣诞之前,香气满屋的泽制披萨,和她煮的红酒。还有我这儿蹭那儿睡的床,一夜一夜又一夜一夜的夜话,那些闺蜜间的语言将我们缠绕。要说我和泽的爱,有什么令我自豪的,那就是正因为与他的爱,让我发现了我有多么的依赖我的朋友,依赖女性之间的友谊,依赖女性之间情感的支持,甚至依赖于这个世界,所有女性发出的声音。
我在这儿已经呆了好多个月了,这个地方是真好。十分放松,人与人之间也真诚可爱。我常看见哪个邻人,在仔细地油漆家具、房屋,或者修缮。他们的房子总要漆上各个颜色,秀丽好看,还要与植物共生,还要饰以物件,或机灵或可爱,都有不同的生机。他们住的房子,大多有个院子,怎么也要占上一半的地,会有草坪沙地、树木藤曼,阿猫阿狗随意错落。围墙与大门也各有风格,一定要有些色彩或材质的组合,都是看着并不贵又好看的。初到,我常被漂亮的高脚佛龛吸引眼球,里面供奉着各路不同的神仙,常有各色五彩饮料,还给插好了吸管。现在,我更爱看路上、巷子里的人家,看他们用心装饰自己的家,看他们与植物共处,互相照顾,互相喜欢。有些家里养鸡的,喔喔喔叫,有些家里有鸟常来往的,锐声曲调飞腾腾的。还有那些在热带气候里张牙舞爪的大叶小叶突突叉叉挂满花的枝桠们,随着风起潇潇,日照影如藻。
我还和好些人熟悉起来,但语言障碍,使我们不能说太多,他们都对我非常好,好些人都拿过食物送我们,玉米、炸丸子和面包。就好像我小时候,我在农村的老家,那些村里人家里有多的零食,就拿上给我。那当然是因为我是个孩子,才能得到糖。而长大了之后,面对的“关心”就是:结婚了没,除此之外,竟却无话可说。至于那些乘凉的大树,也因着什么原因被砍伐一空了。每个富裕了的人家,就重新翻修房子,也不像从前多少留个院子了,而是把地占满铺满水泥,就算房子歪了个角也不要紧,把地方占满要紧。

昨天,我去一个奶奶家吃炸肉串,她的孙女给我们炸,她就在旁边让我们多吃点。她用英语告诉我们,她去过好多次马来西亚、新加坡,说那里吃饭贵。我说我也去过,可我最爱这儿。她就用她瘦瘦的手抚摸我的后背——这是从姥姥传给妈妈再传给女儿的动作,她笑着说:那就留下来吧。
我依稀地也想起,我是曾被这样抚摸过的,好久好久以前了。女朋友们,男性女性们,如果心里难过,就也这样安慰自己,学习母亲的技能,做自己的母亲。
或者因为这样的安慰,今天我可终于忍不住哭了,不断地哭,不断地恨为何不让回家。我太想念我的朋友们了,这阴惆的云低垂地压了我好久。我想与她们快乐地畅谈,面对面的,一起跳舞,大笑,大哭,我们一起骂着这世道,还有那些伤人的人和事,一起诉说着从童年伊始就与我们缠绕在一起的故事,互相拥抱,然后像奶奶的动作一样抚摸彼此的后背,姐妹之间如母女之间。这样的想念,对自己根源的想念就如堤坝背后的洪水一样。
女性的世界并不像男人建立的社会那样,女性的世界里,在无意识中要讲根源,要寻找根源。无论这女性如何被这话语扭曲变形了,她依然需要这个、追逐这个,只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可这根源不是什么父系的姓氏或奉献一生的家族,而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以及、尤其是互相慰藉的、互爱的,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女性要的“根源”就在人与人之间,就要在这样的弥合之中共振共鸣。

那是一年以前了,一个多年以前在印尼排华中逃至新西兰的朋友与我们在江边的小屋醉酒,哭得崩溃,我抱着她慢慢地晃着,给她哼曲,一首她的名字的曲。我今天哭了才恍然明白,她有一道狠狠被与homeland切开割离的伤口,那根源之处原本汇聚着、交织出她的生命的源——可能是一起上学的女伴,可能是奶奶的抚摸,可能是烂漫无尽的夏日,一杯茶或一个招呼,或是石头子和藤椅。
我那晚给她哼的歌,我今天也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唱,不断地唱,不断地回响 ……一边唱就一边想起,我们那晚跳舞多疯狂啊,我们那晚的拥抱,醉酒,那胡言乱语的英语,哭泣着说害怕被抛弃的女友,内敛却情感深沉的哥哥,一种台风般的旋在那里开始成形,我们都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台风眼这最平静的地方。
如今一想起那幸福的时刻,我就要落泪,我不需要付出什么来抓住它,因为它的存在,比什么都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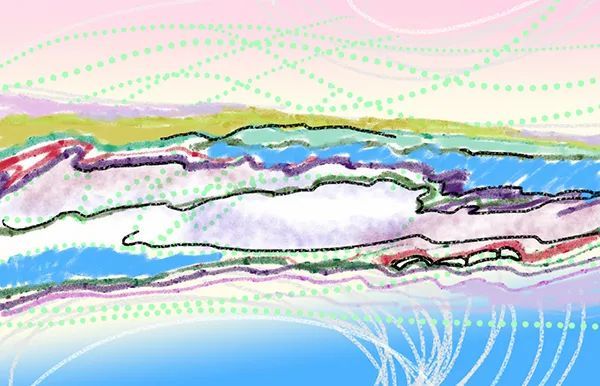
我这几天思绪千回万转,还因着我在看见一网友说相亲于她的咨询师生病的事情,我就忍不住去告诉她说:你要的,在婚姻里不会有。我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多。我最终发现是我的恐惧使我越界。我恐惧她迈入了没有语言支持的、无法消解无由来的冲突的、永远与另一半失臂之交的、被失声被透明化的,而法律上又可笑不公的婚姻关系。因此我便说教了,我没有问她需要什么?或在寻找什么,我就说教了。
我并不知道自己恐惧了,是我突然意识到了这害怕正使我着急,恨不得立刻把武器交到女性们手中。恨不得以怀揣真理的姿态,训斥她们说:快看看你自己,你那勇敢的时刻,你已经做得如此之好了为何还不自知,还要压迫自己?我太急了。我的恐惧转化成了另一种面貌,不是听闻友人被死亡威胁时的面貌,也不是梦里回想起未完成的性侵时的尖叫。而是在我窥得女性为何陷入巧言令色的迷宫的秘密与离开的路之后,这恐惧,使我要逼迫着女性们,都走我看到的那条,所谓的真理之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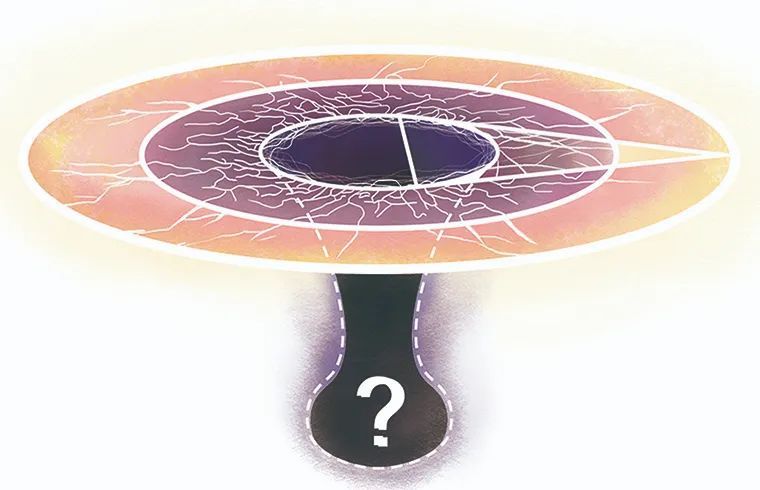
有些女人不甘心看见自己不被爱(可实际上爱她的力量只能来源于她自己),有些我这样的,不甘心其她女人又步入残酷无声的命运之中。大骂婚驴的,大概也是这样的。
其实Me//too已经告诉我要怎么做了,精神分析也不断地说着这样的“技术”。真相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要让人用自己的话说出自己的遭遇、理解自己的需要。我必须放手,必须克服这恐惧、这心里要去拦着尖刀下划的冲动——毕竟,这铡刀早已落下,早在我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早在母亲还在姥姥肚子里的时候,早在所有母亲的母亲出生之前,就在搅动着我们的命运了。这是已然的了。经历了这些的失言的她自己,才是怀揣真理、孕育属于自己的真理的人。我并不能霸占她人的子宫,产下自己的婴孩。

我想把这些都当面告诉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女朋友们。我很是想念你们。我在想念你们,你们比性的高潮还重要,比那口入口即化在鼻窦腔爆开的好榴莲都重要。
我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分离,也知道它不需要付出代价。这种傲慢的权力就如推土机一样,宣告自己比天还高比钢还强。
这种傲慢,身为女性从小到大见得太多太多了,就在每一次我们粗野地走路、放肆地大笑、反击那些欺辱我们的其他小孩时,它都会出现。甚至在我们玩得弄脏了自己、想要去未知之地探险时,它都会出现。它以无数的面貌在无数人无数语言中出现,告诉我们要乖,要恭顺,要压抑收敛,要为了别人“着想”。它对待我们就像电锯伐木,像钢丝捆箍盆栽树,对所有冒头的、不合规矩的、妄图捍卫自己的一切,无论是言行还是房屋都敲敲打打。
但它还妄想要隐形。
它操纵人们以为傀儡,浸侵言语以为话术,无时无刻不侵占诱骗,以致力于布下天罗地网;它内在于人既如没入肉身一起成长的细钢丝,外在于人又如大象之无形,如大音之声稀。它无所不在却又想逃避被指认。
可是,只需要来过一过这人过的日子,看毫不齐整又各自谦让的街巷,看家家户户都有人与树的共生;看人与人间放松真诚的眼神;看吃着的、始终不会怀疑它放了什么地沟油的食物;看这人过着的、一种有盼头(而不是要xxx才完整)的生活。不是以游客的猎奇疏离或鄙夷他人的心,不是以为随时要被坑害的紧张,也不是尖锐的无措或自卑的暴怒,而是忘记这些,以舒畅自然居住于此,学着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就能知道我们平常究竟在经受着什么样的暴力。

我从前还不能真正认识日常的力量,只知道不对劲的、被扭曲的、让人不爱过的生活为何。但我不知道不冲突扭曲愤恨的正常是什么,放松平和是什么,日常的、无目的乃至无意义的行动是什么。从前我知道历史是偶然之堆叠与因果循环之相扣,却被——无论是个人的历史还是超过了个人的历史,冲击得七零八落,又瞎又聋,只知道无措。我如今也还无措,也还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有一些好的,这是泽告诉我的,他说:
“我很高兴,在这段时间里,看到你变得比从前更勇敢、更放松,看到你开始看到以前不知道的生活的另一面,还前所未有地梳理了自己、深入地认识了自己,而我们互相探讨的话题,也比从前更深入。这是这次被迫旅居带来的惊喜。”
我忽然想起Yan说的,不能放弃内心的幸福平和,成为枯燥的革命家。我想,是我不断的自我觉察带来了平和。而我与人的爱使我不放弃这幸福,并愿意为此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