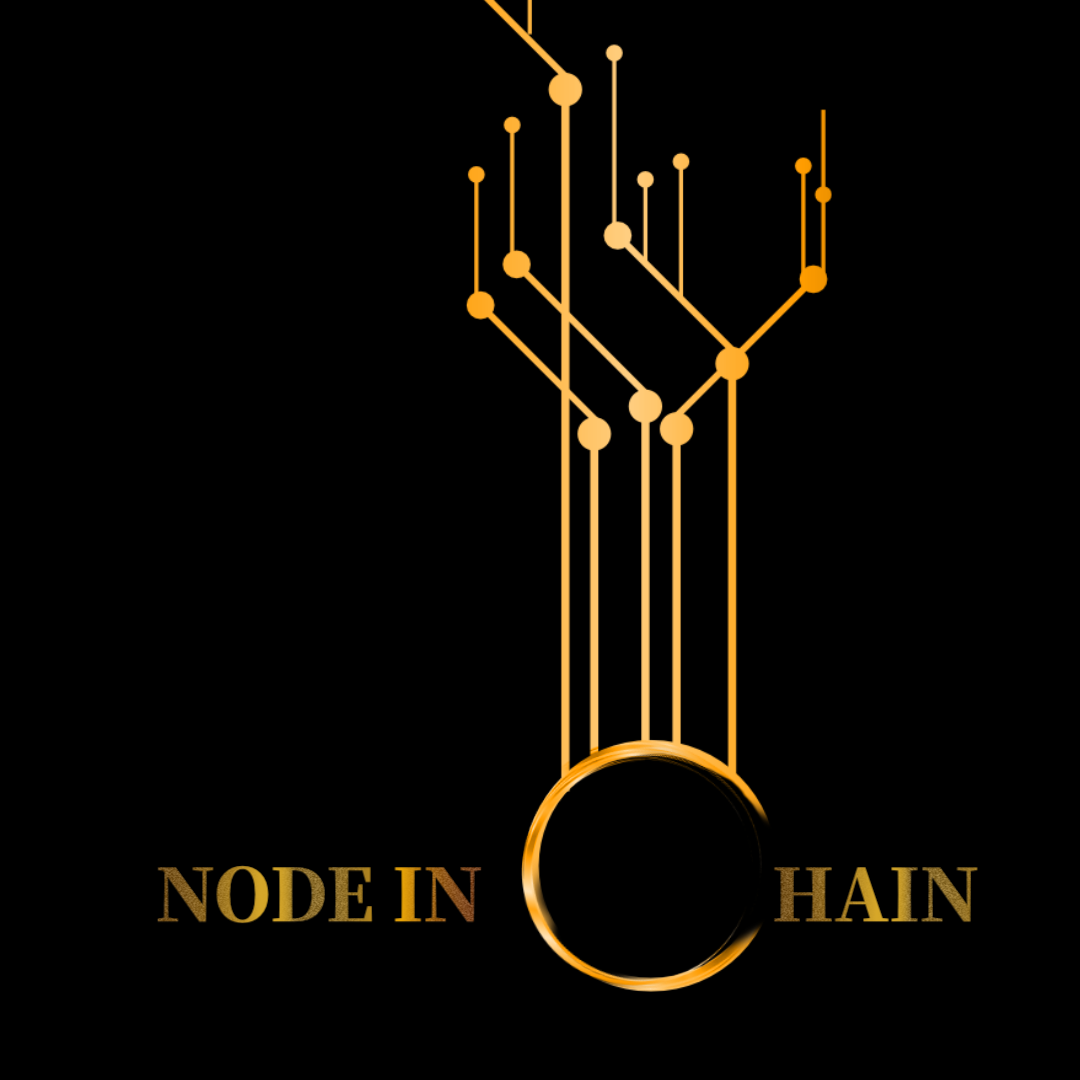沒有流派的歌聲
「所以,告訴我們你是如何發想創作的?」
淡黃色的燈光自廳室上方打下。
你坐在木色的椅子上,將一隻腳些微盤起,讓持麥克風的手可以抵在腰間。
「我想,創作有時候其實並不需要特別到一個場景去專程發想。」你對眼前的聽眾們說,「我們的日常就是最好的材料來源。」
「你是說我們平常的日常,那些我們每天生活都會接觸到的東西事物,只要多多留意,就會發現裡面有文章這樣嗎?」主持人在你稍微停頓時接話問著。
「對,每一個日常的時候,如果我們多多去留意,這一幕景象,這一則新聞等,你會發現它們都有各自的聲音。只要用心去觀察,你就能發現日常其實滿滿是題材,我們只需要發覺它們,並且在這些基礎上擴展發揮即可。」你維持同樣姿勢,不過讓腳向前延伸放鬆一點,同時對眼前的讀者們說著。
「像現在這個場景,其實你就可以寫,一個作家在這邊和他的讀者分享書中內容,回憶起當時情節,然後才發現說,誒過往的謎案似乎並沒有真正解決。原來還是有謎團,而且這樣的謎團跟著他一路來到當代了。那這個看起來就會是一個很可以發展的故事。所以我是比較少會去刻意說找什麼題材,我們的日常就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庫了。」
「看起來大家都很贊同你的說法。」主持人觀察眼前那些聽眾點頭的反應之後說,「我們大家在這次分享會說不定也能獲得很多題材。」
接著,主持人的目光微微往後延伸一點,看向坐在你另一側,與會受邀的另一位作家。
「那長袍子你呢?你是怎麼樣發想創作的?」
你順眾人的目光緩緩轉頭看,那另一位作家似乎有著些許片刻在思考,沒立即接話。
有趣的是,他雖然有著長袍子的筆名,但他本人現在卻沒有穿長袍。相反地,他的打扮和外觀看起來相當……不起眼,就像你在很多學校附近會見到的那種,明天還要考試或打工的學生一般。
而後他開口了,「嗯,我覺得……應該是,直覺吧。」
「直覺?」主持人似乎代眾人(包含你)問了一個大家都想問的問題。
「對,直覺。就……跟數學上的直覺是類似的,你的直覺告訴你3>2,2>1,所以3>1。」長袍子若有所思地在句子中間有所停頓,「我寫東西也有那種直覺在告訴我,什麼東西是應該要寫的,或者這裡是應該這樣寫的。」
「你是說你寫文像算數學?」主持人接續問。
「當然不是那麼相像,只是說文章和小說它有某種自己在走的韻律,你必須要跟著它。你的直覺會告訴要如何跟著它。」長袍子回答。
「就好像上天在跟你說,這裡要這樣寫。在這邊它跟數學或物理定律的直覺就很相似:數學物理的直覺是上天在給你答案。你是去嘗試逼近上天的答案,那將是一種超越性在指導。所以,你不太能逾越它。」你有一種感覺,這位「長袍子」似乎在日常的用字遣詞上也有所斟酌,就好像在寫文章,有時會一句一次完成,但也有時不是那麼流暢。
「你是在說你寫文章,就像科學家寫出物理定律一樣,是上天的安排?」主持人進一步問。
「對,有的時候,語句自己會決定它的下一句,題目題材也會決定它適合出現在哪裡。我們要做的,是去發現它們,跟科學家發現物理定律類似。只是我們是去發現那些字句和題材的走向。」長袍子這次停頓得比較久。「我有時候會覺得,人或者說作家,其實是一個容器。是天地之間一種更超越的東西,會在某個時候借你這個容器去展示一些東西。而我們寫作只是把雙手借給那種超越性,讓它能拿紙筆寫下。」
「那這樣子的話,你有沒有什麼想跟我們大家分享,關於要如何寫作和發想的?」主持人問。而長袍子又是些許停頓後回答,
「我覺得,要相信直覺。要相信你的直覺,讓它能把你帶到更高的地方。」
……
又是盛夏時分。
你如往常在街道行走,
日光傾斜,從店鋪旁的金屬邊緣散逸出彩色尾巴,連同那些人們經過時候會聽見的話語,在空氣裡面編織。
「看看喔。」
「鳳梨要不要吃吃看?」
「現烤麵包喔。」
走著走著,你將目光放到較遠方一處賣飾品包包的小舖。那是一位年輕媽媽顧攤,帶著他的小孩,大約比國小三年級還小的模樣。
小孩平常安靜地站在旁邊。不過當媽媽被佔住又有客人來時,小孩就會上前解說……
「這些都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是我們自己做的喔。」
「很漂亮耶,是你媽媽還是你做的?」
「媽媽做的。」
「啊你就平常來這邊等媽媽幫忙賣這樣。」
「對呀。」
「那你幫阿姨拿那個給我看好不好,那個掛著的那個。」
「這個嗎?」
「對啊,就是那個。」
「等我一下喔。」
你在緩慢行走的路程,觀察著一組客人和他們的互動。當前那組客人正在看一個由小孩拿出的小型包包,看起來像手工編織的。但當中最吸引你的是它的配色,當中紫綠相間的分布搭配和色澤感,似是形成一組神秘的漩渦,要把周圍事物偷偷捲進魔法裡般,看起來頗有藝術氣息。顯然不是出自普通人之手。於是你再瞄了一眼它的標價,嗯,並不貴,比你想像的低很多。
隨後,那組客人將包包放回去,改看一個小巧的飾品。同樣可以看出來,那是一個對事物很有感覺的人做出的東西,而同樣價格也很低。這倒讓你思索好奇起來,即便走過那攤一段時間後,你仍然咀嚼著那些問題:
它的東西漂亮且精緻,但是價格並不高,這樣收入足夠嗎,況且還要養小孩。如果另有收入,這邊只是貼補家用,那麼要堆積起這樣的生產,又會耗去他們多少的時間呢。
更重要的是,那明顯是有才能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如此的才能,卻只能消耗在這樣的叫賣中,為了那一丁點的貨幣。
你暫時不去細想他們的故事是什麼。不過目光盡處,那映在街道尾巴的高聳大樓,如戰艦般籠罩天空,鎮住投往前方街道的日焰,在光與影間形成強烈對比。這幅景象倒是使你想起那句俗話——時間就是金錢——將越發在當代和未來有更直觀的解讀。你曾聽過有人說過這樣的概念:人們是用貨幣去購買他人的時間,而在未來的時候,這種情況將會加劇——
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富人棄如牛毛的零頭將和窮人珍視的數字等值。屆時富人只需支付更少的費用,就能買取窮苦人更多的時間,直至窮人若要維持生計,得耗盡時間和心智的能量。至於翻身則成為極少數特例依靠自身之獨特才能達到的事情。
好比你現在又看見一位老先生在發新開寵物店傳單。老先生客氣而有禮,卻同樣只能在人流中,竭力應對不時出現的惡意,領取利潤最末端的微小收入。
你在經過老先生身旁時,向他拿了一份傳單。
而如果今日的所見所聞只是到此為止,那麼也許這些會先暫時埋藏在你腦海深處,等待日後有東西觸及來再度燃起。
不過你的路程不只如此,在陽光又傾斜了幾個角度之後,你的視線裡出現一所學校。
不知是否是時間空間上的巧合,或是一直都是如此,在你看得見那所學校的一小段行走路程中,背景裡參天的樓廈,似是有所安排般,留出了好一片天空。
這讓學校較為單獨地透露出來,而不是作為某種更大事物的附屬。
可當中真正引起你注意的,是你走近時,在操場一隅的一組學生。
他們的氣息並不如常見那麼張揚,反倒有一種安然的張力。於是你稍微細看了下他們排練的戲劇。哦,那可不是幼稚的家家酒。而是關乎家園、未來、政治制度、經濟,甚至有點參雜個人存在議題的,無所退懼之關懷。如同當中你所聽見的幾句台詞所述:
「如果今日的成功,是透支未來的資源。那麼,我們只是借貸了後續世代的財富來顯得自己富有而已。」
「一個好的制度,是容許內部誕生更好制度的制度。」
「每個時代都有人,能夠跳出來處理那個時代的問題。我們該做的,是讓他們到時候可以不必受到我們今日設下的諸多限制而難以出頭。」
「我們必須把未來,還給後代。」
這種豪情倒讓你想起你的同樣年歲,有感於此,你遂逐步將目光散落到其他各處,探尋青春的蹤跡。而這校園裡的種種日常,現在則成為了日光之下,那少數無所退懼彰顯生命本質的樣貌。
有鮮明的嘻笑打鬧;
有呼喚他人名字的宏亮遼闊;
也有窩在角落,背著眾人自己偷吃東西的喜悅。
似乎那不知是防止外面人進來,還是禁錮內部無從出外的防盜鐵窗條,儘管在學校的邊緣成為映照斜陽的鋼鐵牢籠,但同時也圈住了外邊更為囂狂的惡龍。這個靜謐的地方因此得以有它獨特的聲音。
然而這並不代表外邊的惡龍並不存在。
牠只是被鋼鐵牢籠的巧妙魔法暫時屏蔽而已。甚或,再過幾年,你眼前這些無所畏懼的勇者,轉身就會變成崇信惡龍的侍從。
是什麼讓人們從這個框架過渡成另一個框架?
或者,所有人一出生,其實就已經存活在最終框架中。這前面框架的假象只是他們作為還未升級的暫時儲備而已?
這些問題纏繞著,使你在當天回程中不斷思索,很快地,問題張開了它的寬度,拉伸成一條條綿延的線。隨後,你將不同的線交織在一起,成為一張網。接著,你在書寫當中把這張網攤開來複印。
這成為了你後來的小說,《你們在青春的詩中書寫機械的未來》。
事實上,就當日的所聞,你當然也可以只寫著青春的詩。可是你選擇將那機械的未來加進。你選擇了讓筆下的校園不只是愛情喜劇的舞台,而是帝國山雨欲來的前兆,透過小幅圖樣去彰顯更大圖樣的暗影延伸。
這是你的關懷。
人們總應該去發覺更為隱微幽閉的角落,而不只是滿足於看見眼前的事物與輕易的快感。選擇去發覺更多並且將它書寫下來,是你的關懷。
……
關懷……
是的,關懷。
無怪乎剛才你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腦海,有所滯礙如鯁在喉,原來是這個。
「那麼,你的關懷呢?」你於是轉頭問長袍子。
「關懷?」他側過頭輕輕回應。
「對啊,你說你的書寫是依循上天給的直覺,那麼這當中你的面貌、你的關懷呢?」你說這話的時候似乎是直直地看向長袍子的雙眼,「因為,如果如你所說只是作為上天的容器,那麼這當中是沒有你的面貌的。」
「這是一個好問題。」長袍子先是微微注視著你,之後他一邊說話一邊將頭轉回去,看向前方,似是在思考什麼,「我會覺得容器的不同,你能盛裝的東西也不同。像我們拿一個碗,拿它來裝水,那那些水就是碗的模樣,但是我們拿一個方形盒子的話,它裝的水就是方方的模樣。」
「可是它們會不會倒出來都是水呢?」主持人似乎對這個議題也頗感興趣。
「是的,倒出來都是水。水是流動的,所以乍看看不出容器的形狀。」長袍子回答,「可是如果它們結冰了呢,那麼出來的冰塊就不一樣了。」
「那這個跟你之前提到的作家書寫作為容器有什麼連結呢?」主持人繼續問。
「容器不一樣,裝出來的東西樣貌就不一樣。一個寫作人的直覺,就是他容器的樣貌。當他從天地中捕捉水分後,那些水呈現出來的正是那一個寫作人的樣子。儘管有的時候沒有結冰,水看起來是流動的,可是如果你看它水倒出來的方式,背後也隱藏了容器形狀的訊息。」
長袍子在這邊稍作停頓,而後側過頭來看向你,
「所以,你想問我我的面貌有沒有在作品中呈現。那麼我的回答會是,我的直覺就是我的面貌。」
「但我還是想問一個問題。可以問嗎?」你覺得對於長袍子這套說法似乎總有未解之疑惑。長袍子隨後對你點點頭,而主持人和聽眾們似乎也興致勃勃,於是你就將話題繼續留在這。
「就是,你總有你的關懷吧。」你說,「如果你總是依循上天給的直覺來書寫,這樣你要如何展現你的關懷呢?難道你是說你遇到一個故事時,你就只寫單純的故事而不寫關懷嗎。」
長袍子聽完你的問題之後,又變成那種思考的模樣,隔了一小段時間後才回答。「你問我會不會有關懷,當然有。只是我的直覺會決定我作品的關懷。如果寫一個東西時,直覺不來或者直覺沒告訴我這個該寫,那這樣在這作品中我就會對此保持沉默。」
你則對此回答有些驚訝,「所以你的作品中從來不出現什麼關懷嗎?」
「不,當然會有關懷,但那個關懷必須合乎直覺,而不能是額外的發明。」
「額外的發明?」
「是。」長袍子這次回答比較堅定些。「前面有稍微提到說,我們寫東西的人很像是科學家去發現科學定律一樣,只是我們發現的是文字。所以這些東西,這些我們寫出來的東西,有它們某種上天的線條。我們的直覺就是去提取這些上天的線條。」
「所以你是認為在這些之外的是發明嗎?」這次換主持人問。
「嗯,因為天地要你寫這個的時候,你是不容易參雜太多額外的東西進去的。所以,如果一個東西,它在你的直覺上沒有浮現而洶湧。那麼或許就不是上天的線條,這時候它就不是發現了,而是額外的發明。」
「但發明跟發現有什麼不一樣嗎?」主持人接續著問。
「我是覺得寫作上的發現……有某種超越性。而發明則是可以大量重複生產的。」長袍子說。「畢竟,你總可以去發明更多。如果有心的話,你甚至可以在所有地方加入自己想講的東西。只要把它們跟當前主題做連結,然後將主軸轉向就可以。所以理論上,你可以發明任何的文章和小說。」
「可是,這不就是文章和小說出產的方式嗎?」主持人繼續問。
「是,也許當代很多確實是這樣。但那就會變成一種工業,一種寫作的工業,如流水線上制式生產。」長袍子回答,
「所以,很多時候當我們看到什麼什麼主義、什麼什麼意識,那些全篇填充著特定字詞,或是在軸線上有所扭曲的,你會發現那些東西表面上是從各處挖掘議題深度,但實則千篇一律的相似。」
「你是說,這時候他們就是在發明文章。」主持人說。
「對,就好像作歌的人先選好流派再下去唱歌,自然唱出來的是特定模樣的歌曲。可是此時作歌人的模樣反而被掩蓋在流派下了。」
長袍子回答完這句,稍稍側頭,眼神往你這邊飄過來。
「所以,你剛剛問我,我的面貌在作品中要如何展現。我也只能說,直覺正反映我的面貌。倒是一些寫作,那些似乎是先決定要走什麼議題,然後才去生產的,他們的面貌反而沒有出來。」
「因為他們的面貌被掩蓋在議題下?」你反問長袍子。
「是,畢竟此時對他們來說,一個問題就變得明顯。那就是:是你在書寫,還是議題在書寫呢?」
……
書寫是特殊的。
你在書寫中探觸寧靜,獲得慰藉——藉由書寫,你得以獲取自身在這冷峻世界中的一處溫暖小屋。
但是近幾年,一種新的東西為書寫帶來不同意味。
人們說AI的文字,只是從既有之前提與前面的字,來推斷出下一個字。
然而,你卻看見更後面的東西。
這是一種調用。
生成式AI從世界中廣結資訊,經由無數次訓練,雕塑出其內部參數後,人們再用prompt 去調出那些參數的文字具象。
這就好像先將世界聚合成一個集體意識,然後再將其分離切割。
每一次透過prompt的下達,使用者就像是從那個集體意識裡,提取一部份分離出來。讓那世界的資訊,以使用者想要的框架呈現。只要你知道如何操縱,你就能讓世界的訊息開口說話。
「請用齊克果的風格,寫一篇關於多元成家的文章。」
「請寫一篇以武林高手隱於市作為開頭的冒險史詩,分成上中下三部。」
「請問如果是括弧內的段落內容,以托爾斯泰的筆法會如何寫。」
你在螢幕面前,敲進輕巧的prompt。
然後,AI就能生出遠超prompt份量的文句和段落。更甚之,那些風格的比擬,有時甚至煞有這麼回事:那些已離世或停筆的作家們,如今竟能有相似的風格,寫出在其時代幾乎不會碰到的議題之文章。
書寫現在變成了調用。
而對一般常人來說,prompt是輕巧太多。人們現在隨意就能比肩千古名家,盛大產出。相比之下,如你這樣必須要一個字一個字刻出拙劣文筆的書寫者,是更為稀少且寡產了。
然而回過頭來,人們並不真的寫出什麼。他們只是在調用。
如同其他更多的,圖畫、影片、音樂等一樣,人們調用世界的資訊。只要掌握了適當的工具,那麼你就能如是產出。只是,儘管這乍看之下不是人們自身的書寫,但這樣真的有什麼問題嗎?難道,這不是工具興起之必然?新的工具,新的用法,新的產出。一如人們發明了農耕機器來大量耕作;發明了工廠機械來大量生產。如今只是人們發明了書寫機器來大量寫作;發明了畫圖機器、作歌機器來大量產製而已。
可你骨子裡卻不這麼認為。你不認為那自己能為此如此投入的書寫,會是這麼廉價的。在你眼裡,書寫仍應是獨特的。
因此,這種調用當中應當是存在問題的,而人們總應該發覺更多。
於是,你在接下來一段時間裡,更為大量廣泛地使用、接觸和思考AI及其產物,嘗試發覺這類調用可能會出現的問題。逐漸地,在多次試驗中,包含不只書寫,而是更包含圖畫、音樂等的試驗,以及觀察他人之結果後,你發覺了認為可談及的問題所在。
也就是那並不是世界的訊息。
人們以為那是世界為他們所看見。可那並不是集體意識,而更像是當今主流媒體那種,在高層的眼光裡,或依歸於流量,來決定你看到什麼新聞:
生成式AI訓練的過程就像人們修剪樹枝一樣,會把微小的,不符合主幹道的剪除衰減,讓事物能形塑出主要軸線,以對應人們的prompt來生出令多數人滿意的答案。
某種層面來說,生成式AI並不生成。它們只是在學習複誦,複誦那些主流的、強勢的答案。至於那些微小的,獨自成全的,卻是逐步被衰減的(也許並未完全剪除,但至少是衰減的)。
這也是為什麼生成式AI 的產出一直缺少一種歸鄉感。
因為它複誦的那些主流的、強勢的答案,並不自我成全,可只有自我成全能帶來歸鄉意境:一如它的文字游移,卻不總是探觸本質;一如它的美麗美好,卻也只是主流文化頌讚的模樣;更甚者,在各種AI使用和訓練的語言中,不同語言的資料量有著明顯不同——某些語言資料量大且可近性高,而某些語言則不那麼多量。這便造就了生成式AI靠往強勢語言的傾向。
是以,它的主流,並不只是主流,更是強勢語言文化中的主流。如今人們便可明顯見到,AI在其各種生成物是如此理所當然地朝強勢語言的審美靠攏。
可以想見,在更之後的年代裡,人們將讓下一代藉由AI學習世間的樣貌。他們以為那是世界為他們所看見。但那不過是以往強勢主流的帝國回聲。
此時讓後代藉由AI來學習,就好似拿著美學霸權的模樣去交給下一代,說這就是世間的美醜一樣。那只會強固已經足夠僵化的審美體系,減弱其依靠自身演變的力量。
於是,這種僵固最終會在文化中築出一道道的高聳城牆。城牆內的狹窄範圍堆疊著了無新意的重複答案,世人們卻還認為城牆內是美好的全部。可當中,竟無一處是歸鄉。
有感於此,你遂逐步整理自身在期間理出的思維,並將其攤開來書寫。這成為了你後來廣為流傳的一篇文章,〈亙古不變的太陽神 — 我在生成式AI中看見文化霸權〉。
也許你的書寫不能總是像AI那般文思泉湧一路暢行,但正是你對事物的額外關懷,促使你去追逐各種的問題並產出不同的觀點。
是你那小小之地,讓世間不是只有表面上最直觀的答案。
人們總應該去發覺更多。
……
是的。
人們應該去發覺更多。
透過發覺更多,人們的書寫才不至於遺漏世間那些微小的,卻獨自成全的聲音。
這也即是回應長袍子說法的一種反例。
於是,你在長袍子闡述完他的想法後,便開口問長袍子,「那你有沒有想過,如果僅僅依循直覺,這樣可能會漏掉一些真正的東西。」
「這是一個好問題。」長袍子一如既往,一邊思考一邊回答。「我想,對於一個東西或者議題該不該出現,真的有必要的話,直覺會告訴我的。」
「可是,你如何判斷一個事物是所謂額外的發明,或者它們可能是真實的,存在於世間等待發現的,只是你的直覺那個時候沒有告訴你。或許你可能在知識面力有未逮,或者前一天喝多宿醉了,或者是心情不好。總之在某些時刻,那些真實的東西沒有蘊含進你的直覺。可如果你心境或知識有所變化,也許日後就會發現那裡有新的直覺。」你邊探問邊敘述地向長袍子與聽眾說話。
「嗯,這是有可能的。」長袍子維持他那不疾不徐的神態。「那我的回答是這樣,當日後我們有新的直覺時,屆時寫的東西自然不一樣。可如果我們當前直覺既是如此,那我們就遵從當前的直覺。」
「那麼,有沒有一種可能,如果不去額外引申,你或許就因為沒去想而錯漏了真正的『直覺』。當你採行這種直覺之外不多做發明的寫作風格時,你實際每一個時期的作品,就確實存在漏掉很多東西的可能?」你一步一步地將問題逼近核心。
「不可否認的,確實存在這種可能。不過大致來說,我還是盡量遵從我的直覺。」長袍子回答。
「但為什麼你這麼在意直覺呢?如果不這麼在意,你的書寫可以更廣闊的,對吧。」你有種感覺,其實不管長袍子回應什麼,你這一系列問題都會問到這一步。
「對的。」而長袍子對此的回應相當簡單明瞭。但你對這樣簡單的答案似乎並不感到滿足,於是你又問了一次,「那麼為什麼你仍然這麼在意直覺呢?」
這次長袍子的思考時間就稍微長了點,有一剎那你覺得他是不是不想開口回答了,直到他再度以那種淡淡的語調說話回應你,「因為直覺關乎世界的真實,不論是虛構世界抑或是我們世界的真實。」
「世界的真實?」
「對,而且關於這個,眼前其實就有一個例子,只是這個例子我不知該不該說。」長袍子在這邊停頓了一下,「還是說好了,就是,嗯,你有發現我們是小說人物嗎?」
「我們是小說人物?」
這什麼怪異回應,我們是小說人物?
先別說這和你們談論的主題有何關聯,雖然你自身作為寫作者,對這類事情的意涵較能迅速掌握,而能馬上銜接對話,但這還真是夠荒謬的。你可還記得前天跟朋友去吃飯,昨天才又去街上碰觸人群和靈感,你可不是什麼五分鐘前才被創造出來的,等等,還是其實你是呢?
「對啊,你不覺得很巧嗎。怎麼這麼剛好,我們兩個對於寫作,一個說要遵從直覺,另一個說要廣為引申探觸,而且兩者之間還正巧有一個寫作分享的小廳活動可以對談。」長袍子對於你驚訝的神情(你覺得你此時應該是瞪大眼睛的)似乎並不感到詫異,他持續對應討論的主題來回應,「這種剛好,剛好到就像是一個虛構小說作者所設計的橋段,用意是要讓我們兩個對此展開辯論或對話。」
「可是這跟我們剛才的討論有什麼關係?」
「這麼說好了,你覺得我們之間互動一路的發展,是不是在那個作者他的預期內?」長袍子在這邊看了你一眼,「那麼,如果不在他預期內,當我們跟他的想法產生衝突的時候,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呢?」
「但如果我們是小說人物的話,我們的反應其實都是他的書寫,不是嗎?」你說。
「是,但也有一種可能,是他現在必須順著我們。」長袍子略帶神秘地說。
「他現在必須順著我們?」
「是,一般來說,作品會跟寫作人的意志有關係。不過終究有些時候,那個人他想寫的東西,我們不一定會想這麼做;或者,他不希望角色這樣決定,可是那個角色就是想這麼決定。」
「這怎麼說?」
「就回到議題上來講好了,假設今天寫我們的那個人突然想講性別議題,於是他接下來就試圖將你刻畫為女性,將我刻畫為男性,來嘗試加入性別議題到寫作討論中;或者,嘗試將你、我與主持人和在場聽眾都刻畫為女性,如此就能展現只有女性的場合在議題中的對談。你覺得,這樣可行嗎?」長袍子說。
「但現場並非只有女性。」你說,「而且我們的談論也跟性別議題無關。」
「是,所以你會發現,當我們已經形成自身的意志時,或者說,當其筆下的那個世界或文章脈絡已經開始形成自身意志時,一個寫作人他就不一定能完全地更動它了。」
「嗯。」
「可是,是什麼決定那個世界的意志呢。」長袍子說,「這就是直覺作用的地方了:直覺會跟你說,這句的下一句接這樣有點硬喔,文句上的安排應該是別種樣子才對;直覺也會跟你說,這個角色是不會說這樣的話喔;這個橋段的發展走向最可能是往那個方向走。」長袍子說,「換言之,直覺所代表的是一種節制。它規範了寫作人的意志不去逾越其筆下世界的意志。」
「你是說,角色活過來反而決定書寫的走向嗎?」
「是,如果你相信直覺,那麼寫我們的那個人他現在就必須順著我們。我們的討論有我們自己的軸線,他必須順著我們的軸線;相反地,如果寫我們的人是一個完全不在乎直覺規範的發明派狂人,那麼,當他認為他的關懷是超越我們的時候,我們就仍舊只是他展現關懷的工具和手段。」長袍子在此稍稍停頓。
「所以,直覺的這種節制,表面上好像限縮了寫作的自由。但實際上你筆下的世界或文章的軸線,它們本身卻是自足自由的。如你剛才所說,他們活了過來。而相對地,發明派看起來在寫作上恣意揮灑,但其筆下的世界或文章,則更可能受創作者意志投入而更動扭曲。於是,你所看見的就不會是一個自我成全的世界或文章,更會像是創作者的意志投影。」
「那麼此時,讓我再問問大家,假設我們是作為一個小說中的角色,你會比較喜歡寫你的是直覺派的作者,抑或是發明派的作者呢?」
……
你後來沒有回答長袍子的問題,因為主持人抓準他一連串談話的空檔,趕緊插入說分享環節時間已超過十分鐘了,要進入問答時間,否則可能會拖到店家太晚收店。
之後進入問答環節後,有幾個聽眾表示他們是你的讀者,也問了一些你過往小說,包含情節、創作時的心境、思緒和情感感受狀態等等。你還是挺喜歡回應眾人的。
至於長袍子,似乎在現場他的讀者並沒有想像的多。你只記得其中有一位,問了他關於其小說中一位主人翁的抉擇之類的。其他更多的則是先前不認識的聽眾問他現場談話的內容。
然後,為了避免太多地延宕到店家收拾的時間(你們其實已經延宕了,所做的努力是為了避免延宕更多),活動後來就在主持人帶動的合照中結束了。之後眾人逐漸散逸,三三兩兩地離去,你也在停留一段時間後步行前往捷運站。
有意思的是,在你的步行中,你注意到長袍子在同一條路上,似乎也是走往捷運站,只是他走在你前面一點點。於是,你將腳步邁大一些,逐漸走近他……
「Hi.」長袍子注意到你前來,他放緩腳步,讓你們的前緣切齊。
「Hi.」你給他一個一樣的回應。
「剛剛真的是謝謝你。」長袍子先這麼開口。
「謝我什麼?」你回。
「謝你有承接我的對話,因為有時候我一些話不是那麼……好接。」長袍子說。
「你是說,我們是小說人物之類的嗎?」你直覺先想到這個。
「對啊,之類的,它們的效果應該還可以吧,至少聽眾聽得很投入,不會覺得太無聊。」長袍子這樣回應。不過,嗯,效果,這個背後的涵義……是你現在想的那樣嗎?於是你接著問,「你的意思是,所謂我們是小說人物的說法,只是在現場為了能夠引起聽眾注意,不至於太無聊的說話手法嗎?」
「有點類似那樣的,至少聽眾們有得到一些娛樂效果。」長袍子說。
「我一度以為你是真的這麼相信。」你說。
「沒有,當然不是。我們當然不是小說人物。」
嗯,果然確實是如此,你們怎麼會是小說人物呢,可他當時講得跟真的一樣,倒是差點就被糊弄了。
「那你的表演很成功啊。不過我有注意到你有一點混淆到一些概念,就是把直覺跟節制相關聯;把關懷跟議題,與發明和肆意書寫混淆在一起,之類的。」
「那麼,感謝你沒有當面拆穿我。」長袍子說。
「但我還是滿喜歡你那個容器說的,所謂不同的容器會形塑不同的故事與文章。」
「這個我是真的相信沒錯。」長袍子這麼說。
而你這樣聽著走著,倒是突然想起在會場有一個問題在你腦中浮現。於是你問,「那麼對於你這套容器直覺說,我剛剛一直有個問題想問。」
「是什麼?」
「你說作家是容器,書寫需遵照直覺。可是如果一個作家真的很想展現他的關懷,主動地展示的那種,那麼,這時候他應該怎麼做呢?假設這個作家沒有像你那麼堅守直覺,而是可以鬆動試圖取得平衡點的,那有什麼方法能夠讓作家可以展現關懷卻又不失於直覺呢?」你問。
「如果是沒有那麼嚴格要求直覺的寫作人,那其實是有方法的。」
「喔,所以確實是有方法的,對吧。」
「是的。只是……」長袍子在這裡又進入了他先前那種沉潛一會兒再回應的模式,只是他這次的回應是這樣的。「在這邊容我賣個關子好了,我先不講,搞不好你回去不久就會得出你自己的答案。」
「這麼神秘。」
「對啊,因為捷運站是不是快到了,我覺得這個現在講又講不完了。所以下次好了。也許等到我們下次有機會見面,你還想問這個問題的話,你再問我。到時候我們可以再談談這個話題。」
「好吧,既然你都這麼說。」你於是暫且不談這問題,將話題轉往更日常的範疇,後續便和長袍子聊了很多日常的東西。而正如他所說,捷運站在你們對話時已經在目光視線裡了,很快你們就進站到達月台。接著一段時間後,是他那個方向的車先來了。於是他向你道別後就前去搭車。
有趣的是,就在你看著他走去搭車的模樣時,心中突然有一種預感,其實你們兩個不一定會有下次碰面的機會。倒是他那離去的背影,看著看著有種奇特。好似那裡有個虛擬的光環。在那個光環之內,是長袍子一個人;在那個光環之外,則是整個全世界。
並且,當一個人看光環的某一側時,光環的另一側就好似虛化成為背景。因此,當你看著光環內那個孤身人影時,外邊世界就沉靜下來;而當你看著外面整個世界時,光環內的那個人似乎就在世界中消失了。
你端詳了好一陣子,直到列車將長袍子載走後,腦海中仍然殘繞著一些訊息。並且這些訊息開始如絲線般綿延編織。嗯,也許這裡,是有關懷可以發揮的。你想著想著,逐漸地,一個議題的模樣開始浮現:
究竟一個作家和世界的疏離是否存在著極大值或極小值?一個完全融入於社會主流的人,會是一個作家嗎;至於一個跟世界完全脫離的人,又能夠成為一個作家嗎;還是說書寫之人必定某種程度保持與世界的疏離,卻又不會完全脫離呢?
這似乎會是個很有趣的題目,你再度咀嚼著這些訊息。一篇新的文章或小說的雛形顯然已開始醞釀。看來,你今日除了會場會談還有別的收穫。你又有了書寫的新題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