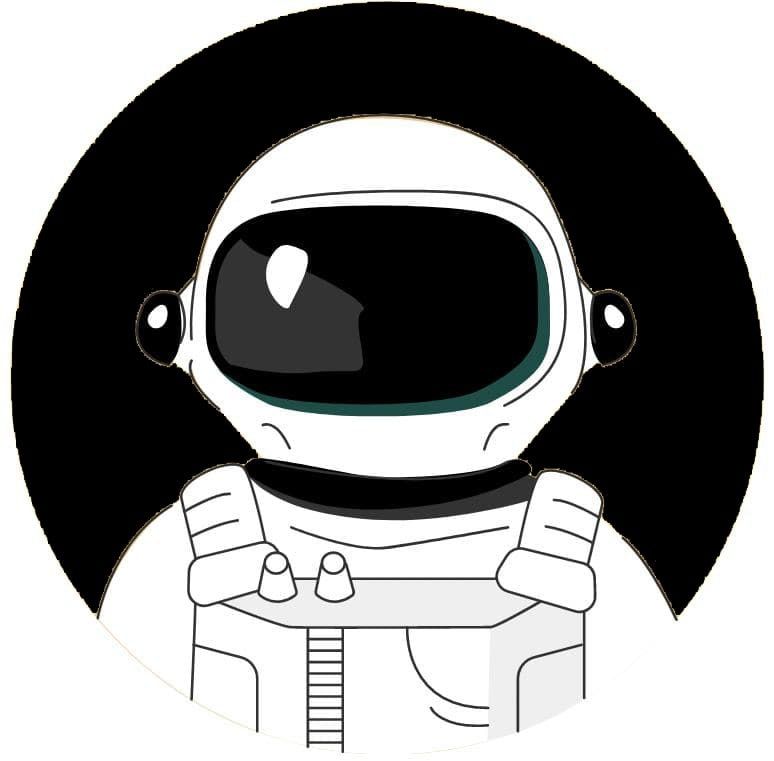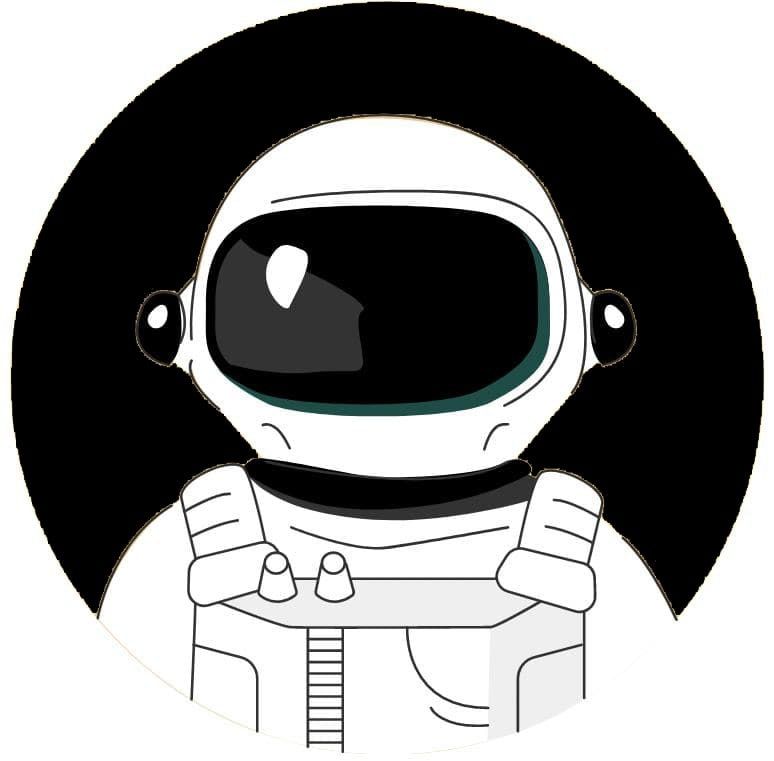疫情告訴了我們什麼?
台灣五月爆發疫情後,至今又漸漸平息了。五月的病毒仿佛一個警告,導致的結果之一(正面來看)是大幅提升了國內的疫苗施打率。然而,放到全球的角度,情況又未必樂觀,除了Delta病毒,南非也剛發現了目前為止變異最大的變異株,有可能讓市面上的疫苗全都無效。病毒也是演化不息。
或許因為我們在台灣,生活在相對安全的情況下,我們總感到疫情會過去,生活會恢復成原狀。但是,在遭遇更大危機挑戰的地區,情況可能是「回不去了」,甚至是「不應該回去」。比如皮凱提就認為應該趁疫情危機,經濟被迫停擺的時機,思考如何以公平永續的社會發展模式重新出發。
這不只是發生在當代。歷史上許多災難造成的破壞,都和發生時社會經濟的結構密不可分。災難就是對人類社會體質的檢驗。能否渡過災難也和社會經濟秩序的重組有關。尼爾.弗格森的《末日》,就是在談這樣的問題。
弗格森的本行是金融史,他自言,對災難史的興趣來自研究所時閱讀1892年漢堡霍亂大流行的研究。在讀了理查.埃文斯對那段時期的詳細研究後,他了解到:
//致命病原體會導致多大的傷亡,有部分其實是受到該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影響。埃文斯認為,漢堡的階級結構所害死的人,絕不比霍亂弧菌更少,因為城裡地主盤根錯節的權力關係已經成為牢不可破的障礙,導致陳舊的供水和地下水道系統難以改善,窮人的死亡率因此比富人高出十三倍。幾年過後,我為《戰爭的悲憐》這本書做研究時,竟發現統計數據指出,德軍會在1918年潰敗,有部分是因為一場可能由西班牙流感所引爆的疫情。後來我又在《世界大戰》一書中,深入剖析這一年發生的西班牙流感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如何成為了終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大「瘟疫」。//
類似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到處都是。因此弗格森來到這本書的起點,即是認為,要研究災難的歷史,就要和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歷史放在一起談。//流行病疫情的嚴重程度除了與新的病原體有關,也和受到攻擊的社會網絡有關。只研究病毒本身,是無法了解傳染病規模的,因為病毒能感染多少人是由社會網絡所決定。再遭縫災害之際,社會和國家的體質也會一覽無遺。由於災難對經濟、文化和政治都會造成重大影響,有些甚至會顛覆常理,因此我們能從災難中看出哪些社會脆弱,哪些社會堅韌,哪些有事承受災難之餘還能更生勇健的「反脆弱」社會。//
我們或許會認為,因為台灣疫情不嚴重,因此沒有、也不需要進行這樣的反省。其實不是的。舉例,在五月疫情與萬華爆發之初,出現了對萬華居民生活方式的批評。這些批評也引來了反彈和辯護。萬華居民自發性的社會互助組織,也得到了大量關注和捐款。這就是疫情和社會網絡不可分割的本地例子。
是否還有更多呢?讓我們在疫情期間,重新認識社會網絡,重新檢視秩序,好不只是「回去」疫情前的世界,而是去到「之後」一個更公平永續的社會?或許台灣因為整體受疫情衝擊不是太大,反而需要更細緻地認識疫情,與疫情帶來的變得更好的機會。
可以從讀尼爾.弗格森的《末日》開始。認識不只是COVID-19。人類歷史本就充滿了與災難辯證生存的經歷。人類這個物種,文明這種東西,都是從災難裡滾出來的。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