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莓山(一): life's necessities
202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的室友ellie冲进房间跟我大声说:“我爸买了座山!”
那时我大二,在首尔上学。我们学校是网校,所以每个学期去一个不同的城市,在当地实习和生活。
我上这个大学的初衷是想要离开我的小泡泡,和与我非常不同生活的人交流和互相理解。不过那时首尔疫情挺严重的,我大部分时间不在宿舍就在当地的大学实验室。幸好当时我和比较要好的美国朋友ellie和我们一个越南朋友做室友。
Ellie的身上有很多冲突。
她很小只,比我矮一头。但是她力气非常大,可以在跳舞的时候把高大的男性舞伴抬起来飞。
她定期给自己后脑勺剃光,软软的金发竖起来就像北欧战士,披下来时就隐藏起来。她平时就是很少几条衬衫和牛仔裤换着穿。小时候的一天,她爸告诉她姐姐不能和男生打架了,因为她胸部发育了不应该近距离接触异性。她是那时候开始穿男性服装的。但她最近从朋友那里交换来了一条短裙。
她坐不住,平常聊着天突然会下腰、下蹲或者做个前滚翻。但是她又是寝室里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当时除了学业也有两份打工,自己付学费。
她表情夸张,声音有戏剧性,可以清晰表达很复杂的概念,陌生人会觉得她是一个活泼的人。但是私底下和她聊天时,她又很能提问和在你身旁去理解你。有次我跟她说最近一个事故,她用蓝眼睛看着我的时,我感觉被某种神原谅了,一下子哭出来。我跟另一个朋友说她给我的这种感觉时,他说他也从ellie那里感到自己以前信天主教时的那种被接受。
确实,ellie的家庭以前在一个密歇根的基督徒邪教。
她爸,ethan,家里前几代都是那里人。ethan从小就被教育要为了上帝造福世界。ethan从很小就为父亲的农场干活,鲜少的休息时间中也必须“闲书”和“有用书”(圣经,教科书)一半一半地看。ethan一直对学习充满激情,就算是家教不上学,也不断学习。但是由于某个血统关系,教会里的人一直不让他做更领导级别的工作,暗示他必须做非智力、没有决策能力的苦工。
ellie的妈妈是个沉默的年轻女人,除了做教会里的模范妻子母亲,还生了五个孩子后开始跑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直到ethan当上牧师之后,被竞争者陷害说他们家犯了圣罪。于是全家被踢出教会,迁徙到麻省。在那之后,ellie和她的4个兄弟姐妹伴随爸爸经历了四五次创业、失败、搬家。因为收入很不稳定又低,几个孩子都给公司打工,比如给几百只山羊挤奶,或者给太阳能客户做CAD模型。ethan总是每天睡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工作。其中包括:一个黑人白人都能参加的创业教会,一个太阳能电板安装公司,一个山羊农场,和每次空档回到施工翻新房子。
而眼下这座山似乎是ethan的下一个项目。
冷静下来后,ellie跟我讲了讲她爸的项目。”爸最近认识了一个建筑师。他们俩一拍即合:都想有在一个有自然的地方,做一个环保生活的样本,让不同人可以上来住住,也可以各类知识的专家和孩子来一起学习环保。昨天,他们看了一片山顶的地,大概xx亩,现在可能要买下了。之后就要开始周末自己时间带队上去施工。他想着夏天让我住在那里,这样准备周末更有效,而且合伙人想要有人去体验和记录在那里生活的感觉和问题。他们还想再找一两个人和我一起。上面没有水电没有厕所,我们都需要参与施工和待客,但是管住宿而且有津贴。你想来吗?“

其实我去的理由很基础。当时我刚确定在夏天会在一个人机互动实验室做实习学徒。因为疫情,项目远程。回不了国,所以我在找住宿。我和他们聊了之后确定可以用数据上网,发电机充电,也可以不参与全部施工确保我有40小时远程工作时间。我对生活条件也没要求,就决定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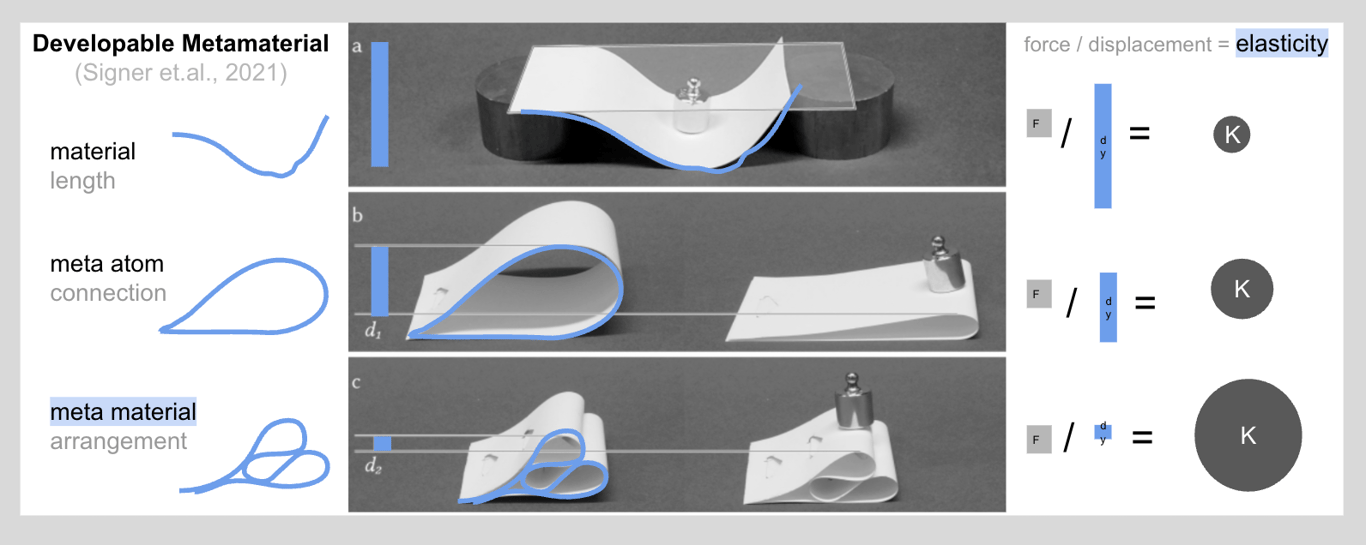
一些生存以上的模糊愿望让这件事变得更诱人。
第一,其实工资预算内租房很容易,但我不想只是住在一个合租房里。那我就想要和好朋友住一起或者在一个组织、机构里,比如工作室或者农场。这是因为我在大二那年其实和室友们的相处都像只是存在在同一个空间里,在自己桌前干自己的活,在自己床上哭自己的事。要是能在伤心的时候互相安慰,或者能一起造一些玩意就好了。
第二,我特渴望锻炼好体力劳动和生活能力,因为我身体不太好。要是在城市外的大自然我想象是很治愈的,还可以学到人之外的生物怎么生活,可以写生画菌类和树皮!
第三,我有点贪。我想这个夏天要是能有些优质的独处就好了。比如一些小的东西在积累,比如读书或者parkour。因为学期中我感觉自己被学业控制。半夜2-4点上很需要理性脑子的统计物理课,早上10点又上另外两个数学课,中午要轮班给室友们做饭,隔天朝九晚五又要坐地铁去当地的实验室搅拌晶体。我一开始尝试分两个睡眠,但是很不稳定,结果就是睡的很少。有些疲惫和崩溃的时候,我只想自己跑出去散步,在首尔的巷子里不停走着听音乐,一个一个便利店里寻找新鲜的东西安抚自己。当时我有催吐,导致本来作为治愈的独处居然变得更累更躁。
我以为森林和前辈可以治愈我的所有毛病,后来我发现我没准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