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企圖與管治意圖——讀《Governmentality: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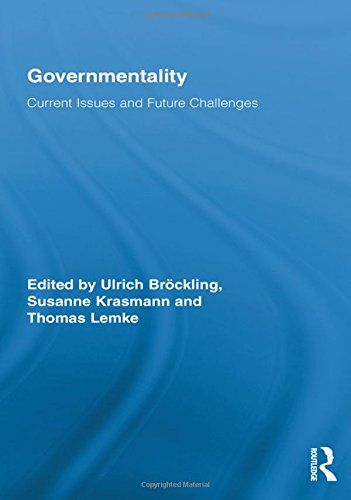
書名︰Governmentality: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編者︰Ulrich Bröckling, Susanne Krasmann, Thomas Lemke
出版︰Routledge (New York)
版次︰2011年
ISBN︰9780415999205
這是一本環繞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晚期研究Governmentality的專書,匯集了15篇對此進一步研究和當代演繹的學術文章。在此之先還得處理翻譯問題,Governmentality純粹按照詞性對譯應是「管治性」,但這顯然不能夠完全反映傅柯提出Governmentality包括引導或約束公民行為(Conduct of conduct)的設置(Dispositif);加上傅柯的知識權力觀以及對意識形態的批判,Governmentality更有指涉「管治意志/意圖」的治術概念。免生歧義,以下就用「管治意圖」對譯Governmentality。
要認清的隱含前提是,這裡假設管治者至少是有能力管治的,而管治者不一定是政府,也可以是在某些空間例如教育機構享有壟斷權力的人。問題的核心於是環繞︰管治者的意圖是怎樣透過權力手段體現出來,最終影響被管治者的行為。
經歷一罩難求、夙夜焦愁的煎熬,「全面封關」的訴求不得要領,「政府無能」或者「失敗國家」幾乎就是唯一結論。從傅柯對管治意圖的理解延伸,這裡至少牽涉了「風險/安全」以至「主權(Sovereignty)/彊界(Territorial)」的概念。要確定我們是「安全」的,就必須先將任何形式(不論顯現或潛藏)的風險先納入計算才得以排除,而整個過程(即Securitization)無可避免會為社會可承受或可接受的風險劃出界線。界線該在哪裡劃定,是緊密接觸者還是泛指所有來自深圳河以北的人,簡單如訪港內地旅客跌幅應該以哪個數字作為基數,首先已經涉及知識與權力的操作。
幾位學者在其論文中不約而同以國家監控和美軍嚴刑迫供作例,說明管治者往往以反恐、國家安全等保護民主社會之名,先將「安全」和「人權」等概念從知識論的定義脫離再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使種種不民主行為(例如侵犯人權的酷刑或監控)變得順理成章。這些都不是專制獨裁政體的獨有現象,就算是民選出來的政府和國會,都對這些國家操作的老大哥監察甘之如飴。
無獨有偶,為了確保緊密接觸者在指定地方隔離,政府建議隔離者須戴上配備全球定位功能的電子手環、醫院應該連接出入境系統、有輿論讚賞台灣及澳門當局統一口罩供應及價格……我們也似乎接受,只要安全受到一定威脅(儘管界線語焉不詳),許多本來不該被視為問題的行為(譬如零售商按市場需求決定口罩供應及價格)都可以成為眾矢之的,自由市場、個人權利甚至憲法都應該讓路給政府行使非常手段。可以推想的是,要是有天被搶購的不是口罩而是廿四味導致藥材短缺,輿論也可能要求政府統一採購然後代煲中藥派街坊。
此種質疑其實是給一眾自由主義者的提醒,尤其是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價值,在民粹操弄下其實極為脆弱。怎樣回應政府干預對自由主義威脅的質疑,在另一篇文章中則有學者提醒德國學界主張一定程度政府干預(例如法律制約和社會規範)達致社會平等和正義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從法律理論來說,例外狀態也不是全然脫離一切法律框架,更像是《儲備商品條例》或《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般可以合理化政府在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和極端情況下介入干預的管治工具。而再退一步還原基本步,政府干預本身就是實踐管治意圖的重要一步,當中必然包含質疑經濟化(Economization)和否定放任自流的絕對自由。
如此這般,管治意圖與民主價值之間的張力便顯而易見。政府的管治方式也由掌控人民生死的政治(Politics over life),改為對人民生活微觀監控(Politics of life)。簡而言之就是在社會各層面採用防微杜漸和量化風險以「自我提升」的思考邏輯︰例如將警政策略由偵緝罪犯轉為預防犯罪的漁翁撒網式監視,或由治療病症轉為預防疾病的「新公共健康」(New Public Health)論述 — 與英美兩國在戴卓爾和列根治下推動的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Management)可謂一脈相承。
新公共健康的論述就是試圖將所有人的健康標準和營養需要視為統一及無差異,飲食金字塔劃出的營養指標就是典型例子。儘管如此,生活方式終究是個人選擇,即使這樣可能為公共健康系統以至國家財政帶來潛在負擔,但國家權力還是沒辦法插手干預我們把甚麼東西放進口裡,國家似乎可以做的就是透過行政手段(開徵煙草稅和糖稅、劃出禁煙區等)誘使人們更方便投入健康生活。然而吊詭的是,每當我們成為病人需要接受治療,醫學權威壟斷的知識體系卻一反標準化的腔調,強調治療方法還須視乎病情度身設計。
西方先進國家由1970年代開始,將生活方式和習慣中有害身體的行為納入公共論述,並且將與生活方式有關例如癡肥、糖尿病等疾病,視為個人不自律、不自制的後果。就算是旗幟鮮明將個人權利和福祉視為公共責任的福利國家,面對強調個體化的新社會(Neosocial)時期,當代福利資本主義都有將個體事業化(Enterprisation of self)的傾向,背後驅動的除了經濟理性,還有要求個體行為要自我約束(Self-monitoring conduct of life)以符合公共利益,將人們置於社會理性(Social rationality)的邏輯之中。於是市民鎖好門窗收好財物的責任更甚於警察巡邏,參與家族聚會然後染上武漢肺炎,需要譴責的是聚會,而何故親友能夠輕鬆過關抵港早屬焦點之外。
說穿了,今時今日我們談的管治意圖,已經超出了地域或法律邊界的傳統政治領域,而是微觀管理對抗(Antagonism)和異議(Disagreement)的能力。表現差劣的從政者悻悻然希望市民包容,無異緣木求魚,不會得逞。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