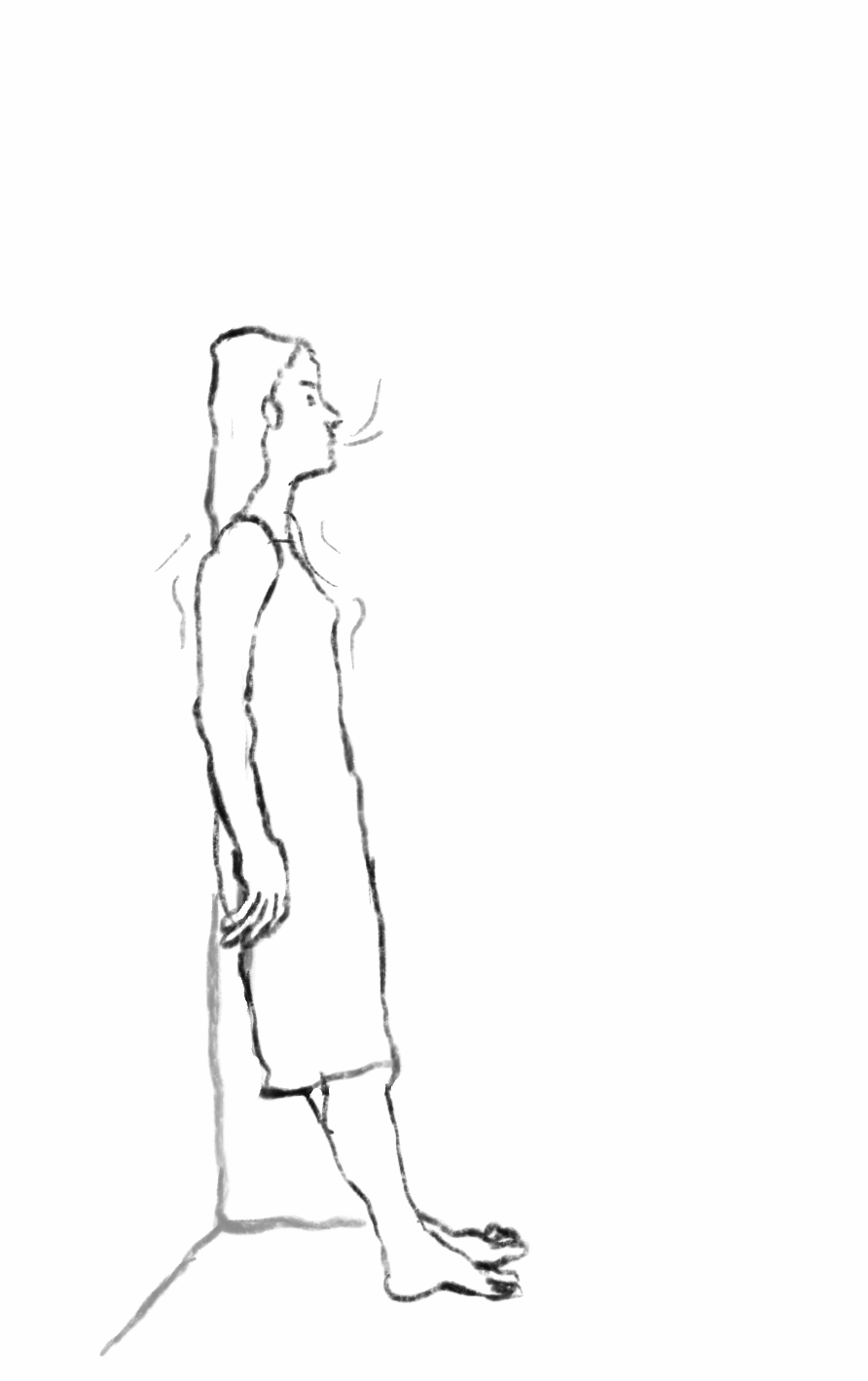庙岭
我住的镇子叫教堂山,华人女篮叫它庙岭,因为这里有很多山丘。
去年八月我来这里做细胞群体行为的实验。说实话我不喜欢这里,但是昨天和前辈聊天发现我需要在这里再呆一年把现在的烂摊子项目完结,所以我不能逃离。我想通过描述它来喜欢上它,忍受它。
公寓和实验室之间要经过两个大坡,每个都有100米爬升。经常早上七点半起来想着“不要骑车了,坐公交吧”。刚醒时心跳弱,畏惧骑上那个大坡时腹部脱力和呼吸变辣。结果等到骑出去在公交站转弯漂移时,呼吸和风刮过皮肤的感觉太好了。我总是不断发现骑车让我多开心。有时想去来去年在台湾也是骑了更大更长的坡,还有一天骑车八小时。说明这部身体做得到。不过当时是被一人从旧金山骑到纽约的同学和每天骑两小时山路去上学的同学带着,现在是让我这个混乱体自己去做。

学校旁边的面包店Panera可以每月11元无限续咖啡和汽水。我被养成了习惯,早上经过这里往暖杯里盛咖啡。一般还能坐在这里写半小时日记或者业余项目再去上班。我一般坐在靠近厕所,对面总是有一对老爷爷老奶奶,坐在很小的桌子那里。老爷爷是黑人,戴毛帽子,穿红色毛衣。老奶奶是白人,两人都戴口罩。每人脚边有target超市袋子,一人一个学校笔记本,上面很密密麻麻的小字。我想有天问问他们在写什么。还有个坐姿很笔直的老爷爷每天点蓝莓燕麦坐在卡座电脑前。他们都是早上八点以前到,每天都是。我也几乎每天去,见到他们会有种安心感。大家都在小本子上写自己的故事,像个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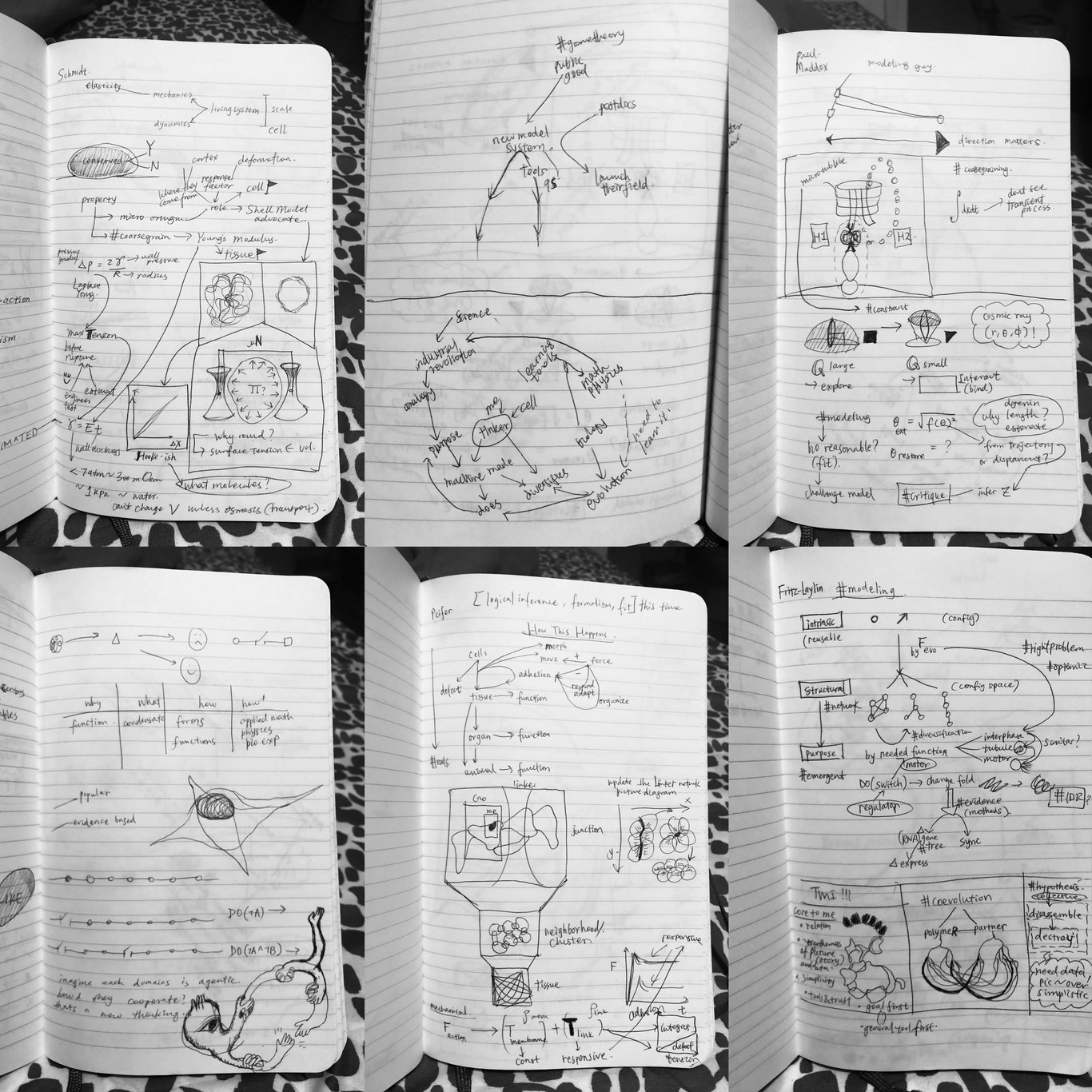
这个镇子真的有很多树、花、动物。从自行车架走到实验室会经过教学楼之间的花树。有天看见一只鸟正好跟着耳机里的节奏突然停住,挺身做S型,然后又突然小碎步跑到灌木丛里,搞得我笑出来了。三月天气变暖后这样对着花和鸟笑了好几次。实验室导师每周末和妻子去教堂山周围看野花,看黏菌。我问他采吗,他说不采就看。来自德国的博士后也经常和女朋友带着儿子去附近森林,在群里发黑色蛇的照片。我想起来我没上过很多生物课,也没真正爱上过任何动物,从而产生对这些爱好者和保护者的尊敬和好奇。同时我也喜欢无知地跟鸟对视但不知道他的名字。
刚来这里一个月时,在公交上看公路两侧都是巨型大树,要很多人才能抱住。20米高,橘色质感。我在那一瞬间以为看到了一个巨型恐龙,不禁哆嗦几下。有次飓风,也就10分钟的忽然出现和消失。飓风把几颗大树吹倒,树杀死了一个在车里的女人,导致10次车祸,还砸坏电线导致三个镇子断电。教堂山的人和人盖的东西对于这些树和风来说很脆弱。
在冬天丢了自行车钥匙的日子里我经常在公交车上产生强烈情绪。来这里第三周,有个华人博士生在离我实验室一条路的另一个实验室拿枪打死了他的华人导师。我们在实验室里用纸把门玻璃糊上,听着警察新闻,观察着楼下的车,继续工作。一小时后警察错抓一个人,三小时后说确认抓到打枪的人之后,我去坐公交回家。我一边看着公交站打电话和看警车的人,一边感觉脑子里的气压胀胀的。第二天封锁学校,我就坐公交去买菜。在车上把耳机塞得很紧听朴树的NEWBOY,胸腔被鼓打的收缩,不知为何就靠在窗子上掉眼泪。心里运算着谜题:“你不知在世界发生什么的时候怎么继续生活?你学会所有事情之前怎么做事?你知道所有信息之前怎么做决定?”

现在住的这间四人合租公寓是我在实验室工作开始倒数两天前才从一位三十多岁的高大美丽单亲妈妈-医学生那里转租到的。晚上爬三层楼梯打开没锁的大门,厨房的水池里有室友昨晚十点从超市下班后做完晚饭还没洗的粉色塑料盘子。水池旁有一只腿朝上的死蟑螂,直线花纹很像更讨人喜的甲虫。我拿手把垃圾桶盖子往下按,压缩堆到顶的冷冻食品纸盒子,再把纸包住的尸体放上面。阳台的门敞开着,有一盆谁买的新盆栽和我四个月前放在外面的发芽红薯,长得张牙舞爪。
进房间门第一件事是把开口很低的窗户向上推开。昨天暴风雨前的空气很好喝。几小时后突然暴雨开始,以厉害的角度向内下,把我放在床边地毯上的衣服淋透。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跑去关窗,观察到窗沿像浴缸一样湿。
进门第二件事是把所有被汗弄潮的衣服都脱下来。我有时回家之前会拐进公交站和房间之间的小区健身房动弹一小会儿。每次去到健身房都有种安心。最近里面没有那么浓的柠檬空气清洁剂味道了,也没有那么大的音乐声。一般会有两三个戴着耳机表情痛苦的人在用器械,或者一边看手机一边爬坡。我有时候也没想好要做什么训练,不过一般就是10-20分钟的自重或哑铃HIIT,或者熟悉的几个器械各做4x10组,或者跑步。但是最近外面暖和凉爽,还有好多花香,我就期待去外面跑步。回家太晚又不想黑暗里跑,周末去实验室的话中午等待时在校园附近的森林里跑一会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