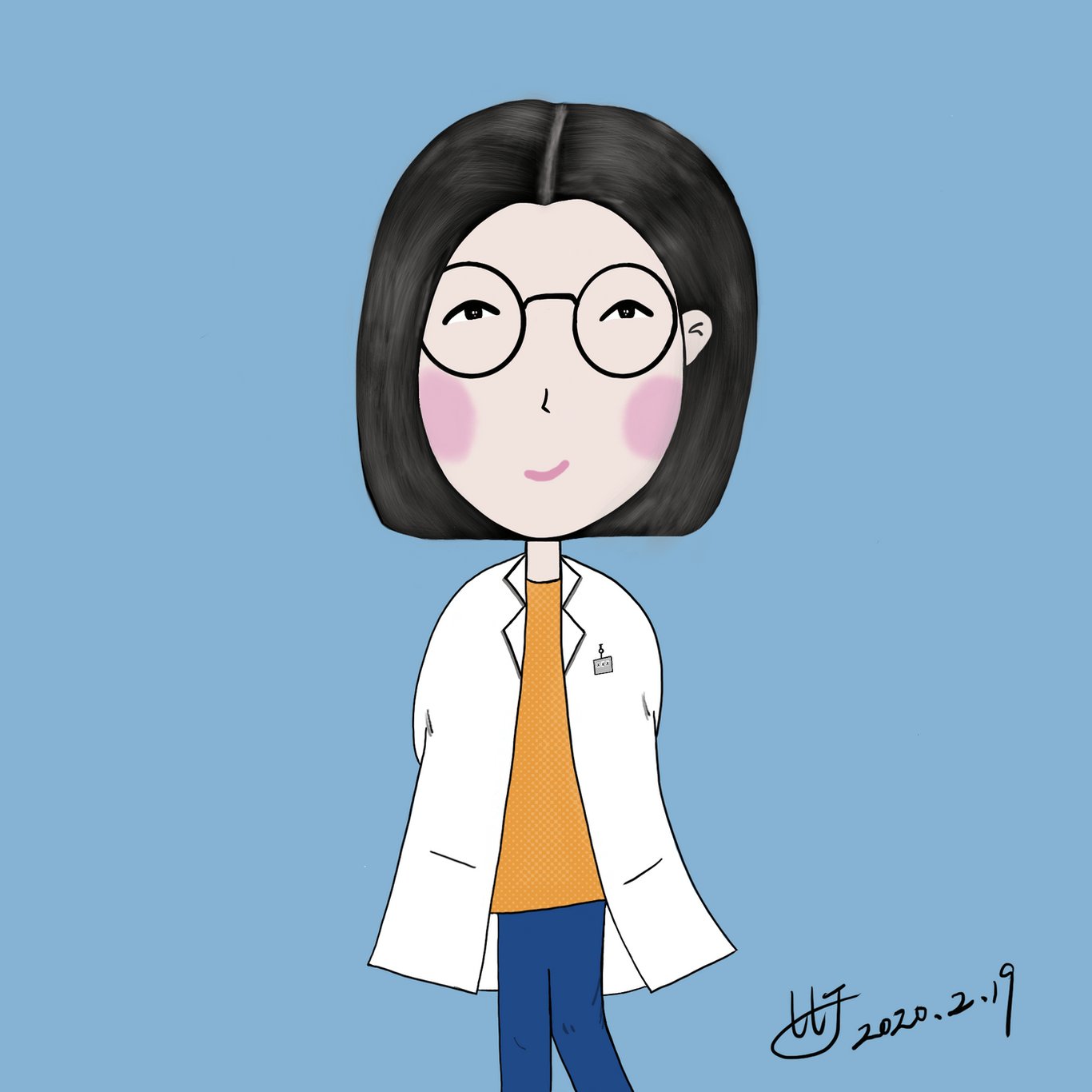读者故事:德国精神病院住院记
01 异乡的孤独
2020年1月。周三,德国。
傍晚,我挂断了国内男友的电话,他沉沉地睡去了,我一个人孤单地留在异乡的傍晚里。时钟刚过四点半,太阳已经缓缓地落下了山头。德国的冬天是最难熬的,进入冬令时后,太阳升起地越来越晚,落山地越来越早,十二月底的时候三点半天就快黑了。我已经近2个月几乎没有去上过课了,此时的平静带给我无限的悲哀和痛苦。
巨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眼泪不自觉地往外冒,终于允许自己嚎啕大哭。我用掉了一包抽纸,用过的抽纸被我随手扔在地上。我任凭自己从沙发上滑落到地上,坐在随手丢弃的废纸里,像是坐在白色莲花上的童子。
不,我可能还不能死?我走出房间,走到露天的阳台,拿起手机,拨打了位于哥廷根的自杀帮助热线。
打了一个没打通,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再打一个。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很令人有安全感的中年女性。她的声音使我想到德语中的一个词,形容女性的,叫做Dame,意思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女性,比中文中的“女性”一词还要优雅一点,因此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怎么翻译,所以我暂且将她称为一个很优雅,又有气质的中年女性吧。
她接起电话,我说我好难过,没有人陪着我。由于七个小时的漫长时差,国内的朋友和家人都睡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德国这边我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我感觉很无助,很想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她总是在询问我为什么如此难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长期的情绪积累使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最终爆发。
她建议我给我的男友写一封信。我觉得和她再聊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她总是在问我为什么,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成了这个颓废的样子,便草草寒暄挂了电话。我准备拿起笔给他写一封信,转而又觉得索然无味。我拿起手机,给男友发了一段消息,大致意思是很难过,想把我的眼镜留给他当作纪念,还给他唱了一首歌曲中的一段。
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霎那凋落,我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眸是最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的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郑智化《别哭,我最爱的人》
我忽然感受到此生从未感觉过的平静,但是眼泪还是不自觉地往外流。我打出了第二个电话,给小鱼同学。她是我在德国的中国同学,来自同一个学校也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我跟她说了我要做出决定了。之后我再一次给男友打了电话,他接了,我也只是在电话里跟他一直哭啊哭。我感受到电话那端他的无力感。他远在一万公里之外,根本做不了什么。
我觉得应该用中文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觉,便在网上搜索了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自杀帮助热线。但是听到我前面还有两个人在排队等待,我就挂断了电话。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他们都很悲伤。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02 自杀的尝试
我拿出了三十盒氨磺必利。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药吗?因为我出国交换,怕德国这边精神科不好挂号,所以带了一年的药出来。德国的精神科就诊不像中国这样方便。医生少,病人多,我十一月预约了就诊,直到二月份才能见到医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家精神科诊所勉强同意我在他那里咨询。
我把氨磺必利一盒一盒拆开,一板一板拿出来,一片一片拆出来放在一个饭盒里。我觉得是时候做出决定了。但是这时候小鱼和胡同学赶到了,把我拦了下来。
我有点冷静下来了,但是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不能不活下去。我决定去精神科医生那里询问一下,询问一下是否需要加药。
精神科医生莫坦博士是一个儒雅的中年大叔,做事磊落又不失气度。他听了我的想法,脸色一沉,建议我去精神病专科医院住院。经他打电话询问,当地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没有病床了,他决定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医院去。
我不太愿意住院,我自认为自己不适合住院治疗。但是莫坦博士说你现在很危险,你只有自己自愿去住院这一个选择,否则他就打电话叫警察把我拉去医院。我说好吧,拜托和我同去诊所的胡同学帮我回家拿了充电器,莫坦医生叫的救护车也来了,我被带到救护车上。
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性,工作起来还是一丝不苟,有着年轻人所缺少的从容。我得知她从事救护车上的工作已有二十多年。
救护车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另一个小城市。德国的精神医院不叫字面意义上的“精神病院”,而叫做Bezirksklilikum,字面翻译是“区域医院”,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区域医院”,但是在这个名字的医院里只有精神专科,所以也就可以当作是“安定医院”了。
03 初入医院
我被救护车带到了这个城市的专科医院。到了医院,工作人员采集了我的个人信息,半个小时之后,我被带到了责任医生面前。我把自己的情况跟她讲了,她给我做了身体检查,之后把我送进了die beschränkte Station,所谓“限制病区”。
限制病区,顾名思义,指的是对患者人身自由的限制。我了解到,在病区里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不能出病区的大门。大门自动锁闭,如果超过十秒没有关闭,护士站就会响起警报。厨房和储藏室也是锁闭的。有趣的是,大门、厨房和储藏室,以及每一个房间的钥匙都是同一把钥匙。护工和医生可以用一把钥匙横行天下,患者则寸步难行。
我在走廊里等了一个小时,看到有一些老年女性患者颤颤巍巍地在楼道里活动,还有流着口水的小姑娘“疯疯癫癫”地缠着护工说话,护工大约是觉得有些烦躁,便给了小姑娘一片药让她服下,她便回到自己房间里昏昏地睡去了。我知道护工没有处方权,但是似乎他们可以决定是否让患者服用镇静剂。
我继续等了一个小时。我十一点到的医院,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我还没吃东西。终于有护士来管我,给我抽了血,量了血压,做了心电图和血糖测试,然后又没人理我了。这就是德国,这就是德国的官僚主义,德语叫Bürokratie,效率就是这么低下,行动就是这么迟缓,我已经习惯了。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终于有人想起我,问我是不是还没有房间,我回答是,之后我被安排进一个病房。我住院的那天是礼拜五下午,这比较糟糕,因为周六、周日几乎没有医生上班,整个医院只有一个急诊医生。周末的医院就像停摆了一样,死气沉沉。
04 难以适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开始感觉心情糟糕。一直如此,太阳一落山心情就糟糕透顶。我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我,冷漠又低沉。我想回到温暖的家里,和室友聊聊天然后在暖和的被子里睡去。我跟去护士站敲门,希望能和医生商谈。住院期间,如果不去询问的话,是见不到医生的。医生“很忙”,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可能一个星期才能见医生一面。
敲了半个小时的门, 没有人理我,我回到房间。又等了一会儿再过去敲门,还是没人理我,但是护士站里传出哈哈大笑和看视频的声音。我很生气,大声质问他们为什么忽视我,才有一个小姑娘护士出来告诉我,这一个小时是他们的交班时间,在这期间他们是不会工作的,希望我不要再来打扰他们交班。我说交班需要大声聊天,哈哈大笑,看视频以至于忽视患者吗?她也无话可说,只好让我等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有护工来跟我说话了。我说我想回家,她说根据法律规定,医生认为你有危险行为,所以你必须在这里呆着。我问我要呆几天,我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她说医生不在,她也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很生气,和她吵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精神不正常,开始不理我了。我说根据哪条法律我需要被关在这里?你给我在手机上查出来。她居然很不屑地跟我说,你作为一个学生有能力在网上查到你想要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给你查。我气得爆炸,说,你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这样说话,我真想用手机砸爆你的头!我回到屋里嚎啕大哭。
一夜未眠。
05 住院生活
病房和活动空间的设置:病房是两人一间,有独立卫生间和小桌板、小夜灯和窗帘,窗户可以打开但是只能开一条缝。我没有带换洗衣物就来了,只带了手机和充电器。自由活动区域有餐厅、客厅和吸烟室,客厅里有沙发和电视机。此外就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了。比较好的是,病区覆盖有信号不好的WIFI,可以用手机。
一日三餐:早晨是面包,巧克力酱,果酱,香肠。中午是牛排或者猪肉配蔬菜沙拉和土豆泥,晚餐是面包配香肠奶酪或者蔬菜沙拉。德语里面晚餐也被称为“晚面包”。每个人的餐食都是配好之后由护工送过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餐盘和自己的食谱,病人可以自由选择食谱。每天有两种主菜,还有配菜,水果,甜点和浓汤可以选择。饮料咖啡和茶可以随意自取,下午三点钟甚至有饼干和面包作为下午茶。周末的选择则比较少。护工每顿饭都会来发药,会看着你把药咽下去,他才会离开。
我有些惊讶,国内精神科患者是不建议喝咖啡和茶的,但是这里的咖啡和茶居然是不限量供应。这令我感到了文化的差异,可能欧洲人离了咖啡就活不下去。
我感到自己快饿死了,问护工有没有吃的。护工进厨房给我几片香肠,一个面包,一个苹果和一杯水,让我先垫一垫,一会儿吃晚饭。护工属于医院的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照护病人,以及给医生打下手,对于患者来说,有一定的权力。患者只能听从护工的安排,虽然护工会尽可能给患者提供其想要的东西比如饮料或者香烟。
06 素食的爷爷
我住院的第二天,病房来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老爷爷。他头发稀疏,行动迟缓,有点阿尔茨海默症的样子。护工给他端来了午餐,他揭开盖子,看到是香肠,“砰”地盖上了,小声而又缓慢地说,不要肉。旁边的患者跟护工说他吃素,护工不闻不问。我们几个患者把自己餐盘里的奶酪分给了老爷爷,他才吃上东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天。星期日晚上终于有一个护工说已经将他吃素的消息报送给了厨房,明天会有餐食送来。
星期一中午,老爷爷颤颤巍巍来到桌子前面,兴奋地打开他面前的食物的盖子,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块大大的猪排!他把盖子摔到了地上,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我义愤填膺,和护工争吵“你们不是说今天给他送素食来吗,怎么又送了肉?你们根本不关心患者!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同情心和同理心吗?你们就这么冷漠吗?”
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工送来一碗番茄汤,说,是厨房给他们送来的食物,跟他们护工没关系。我简直是气急败坏,说,你难道就不该代表医院给这位老先生道个歉吗,他因为你们的工作疏忽几乎三天没吃东西了!我本来想继续说,但是旁边的患者都暗示我不要再说了,我只好作罢。希望之后这位老爷爷能获得他喜欢吃的食物。
07 热情的匈牙利小哥
有个来自匈牙利的小哥,特别喜欢照顾别人。第一天就主动给我拿刀叉餐巾纸,还给我倒果汁。刚刚提到的老爷爷不吃饭的时候,他把面包涂上果酱和黄油,再盖上奶酪,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放到老爷爷手里。有的患者称他为“没有胸的妈妈”。
他特别喜欢打扫卫生,倒垃圾,帮忙分发食物,调节室内温度,和老奶奶们打扑克聊天。我有时怀疑他是个护工,假扮患者潜伏在我们中间照顾大家。但是他记不清自己的电话号码和邮箱,以至于我们交换联系方式的时候他居然只记得他女朋友的电话。
他说他也曾经企图自杀过,但是他对自杀过程和想法一无所知,像是断片了一样。他喜欢“顺势疗法”,通过使用牙膏,身体乳,VC片等方法战胜疾病。对于顺势疗法我不了解,但是听起来像是骗人的玄学,我不太相信。
08 陌生的病友们
病房里有一个女性患者,说话疯疯癫癫、令人难以理解,她被安排一个人住单间。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突然拿起杯子往地下一砸,然后坐在桌子上哭喊“Mama,Mama,Mama”,但是护工只给她吃镇静剂,扫地上的玻璃渣子,根本不关心她的情绪。周围的患者都躲开了,没有一个人去关心她。我也没有关心她,我好害怕。我可能也是被疾病吓破了胆吧,太懦弱了,不能为身边人做些什么,发光发热。
再说说和我同住一间病房的病友。他是一个伐木工人,听说是由于受到别人的威胁而自杀,未遂,被送来住院。他看起来还算比较正常,和病区里其他病人相比。他经常和家人喋喋不休地打电话,导致我夜里很难休息好。他不会说德国普通话,只会巴伐利亚方言,我和他交流十分困难,他甚至听不懂我说“抽屉”这个单词。我看到他用的是小米手机,这令我很惊讶。
09 出院
星期一早晨十点半,医生开始查房。医生详细地问了我情况。我把我整个病史、病情和感受都跟医生说了。我已经感觉好了很多。在医院的这几天里我想清楚了很多事情,我不想死了。我打算休学,回国,准备翻译证、歌德学院C2以及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机票和书已经买好了,休学申请也已经提交给学校。我希望尽快出院。
医生回答我说,只有主任医生才能有决定权,他只是病区医生,没有权力决定我是否可以出院。和国内不同的是,这里的主任医生并不是一个职称,而是所有病区的总负责人。他让我等通知。
下午,我听说主任医生不同意我出院,我非常沮丧,同时要求与主任医生直接交谈。当我见到主任医生的时候,她似乎并不了解我的情况,我又把整个故事给她讲了一遍,并且表达了我对整个治疗环境的不满。最终,她勉强同意我出院。
住院4天,时间不长,却让我深深感受到自由的可贵。在德国长期居留的所有人都必须缴纳每个月高达100欧元的保险费,因此住院治疗的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报销。出院时需要带上医生提供的说明,上面记录了从入院到出院所有的谈话内容、用药情况以及体检报告,以供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后续参考。
带着这份记录,我走出了医院大门。
10 重获自由
我独自走了一个小时山路到火车站,坐火车回了小城。
从住院到出院,一路忐忑不安,直到进宿舍房门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安全。我忍不住想,精神病院里真是太多奇奇怪怪的病人了,我甚至觉得自己是那里面唯一一个病情尚轻、理智尚存的人。
— END —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