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见你》:投向边缘群体的一束暖光
《想见你》已经完结了一周有余,不过笔者相信,许多人仍会不时回忆起黄雨萱和李子维跨越时空的爱情,并感叹于编剧强大的逻辑能力。但相比而言,更令笔者动容,甚至对整个剧组生出些许敬意的,是剧中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与刻画。这一点,正集中体现在陈韵如、王诠胜和莫俊杰的角色设定上。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宇宙中最黯淡的那颗星
拼命地发光
想要有人发现我渺小的存在
可是最后等待我的
却只有坠落
陨落的那刻,我知道
世界上没有人记得我”
这是陈韵如在日记中写下的话,大部分人在看到后都会像黄雨萱一样,发出“这也太压抑了吧”的感叹,并让她“再努力一点”,变得阳光一些。但却很少有人愿意尝试敲一敲她“在心里最深处那关着灯的房间”的门,去听一听她唱给自己的情歌,即使“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也能给她一个拥抱、些许温暖。毕竟,“happiness”是“幸福”,是被推崇与追求的;悲伤,在当下的许多语境下则是“矫情的”“麻烦的”。选择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比选择分担悲伤的人多得多,这是人之常情。
但每个人都会有“陈韵如”式的阶段吧,对这个并不美好世界抱有太多期望,希望可以被看到、被理解,却不知道怎么说出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在得不到想象中的回应、关注和在意后更是不敢再表达,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把脆弱的自己包裹得越来越紧。即使努力想要融入集体的氛围,却在一次次的尝试后更加习惯一个人的独处,甚至会在从人群中抽离时感受到自己的又一次被消耗。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时光只是一个阶段;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阶段就是一生。而这一切,会被简单地概括为“那个人很怪、很孤僻、不好接近”。
有时候笔者会想,为什么这个社会号称自己是“包容的”,却只容得下“积极向上”呢?为什么“忧郁”“彷徨”“迷惘”会无处安放呢?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去追逐快乐呢?为什么要对悲伤避之不及,甚至认为这是可耻的呢?为什么不能平等看待不同情绪呢?为了效率?为了发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对个体该有的尊重。


王诠胜,一个很羞涩、很纯真的男孩子。他没有一点点杂念、很单纯地喜欢上了班里另一个男生,勇敢地向他告了白,却遭到一场欺凌。当他听到喜欢的人说“以后离我远一点,恶心”时,当他跌倒在地时,当他冲向自己喜欢的男生并吻了他时,当他被拉开后倔强地说出“喜欢你,很恶心吗”时,眼泪,不由就流了下来。
还记得在第四季吐槽大会萧亚轩的专场上,她的男友黄皓说,“Love fights everything”。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这句话,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说出这句话,而爱,原本也应是自由且广博的,无需与其他任何人事物进行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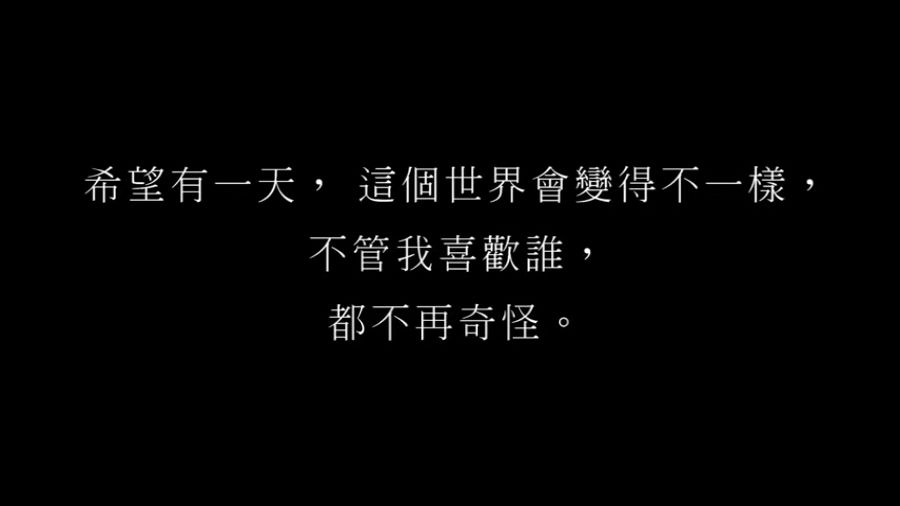

“每个人,只要看到我耳朵上的助听器,不是笑我是聋子,就是用一副我跟他们不一样,好像我是怪物,要不然,就是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真的很可怜。”
这应该是很多身体有残缺的人共同的感受吧:希望被别人正常对待,却始终被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并被一遍又一遍或明示或暗示“你和我们不一样”“你需要照顾”“你很可怜”。这是廉价的同情,不是同理与共情。我们的社会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有同情心、有恻隐之心,家长看到乞丐会对孩子说,“你看他是不是很可怜,我们给他一点钱好不好”。有同情心固然很重要,但对同理心的培养更重要。拥有与他人共情的能力,我们才能真的设身处地去考虑他人需要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只为满足自己内心所谓的道德崇高。

三个人物,三类边缘群体,一个温暖的剧组,一部优秀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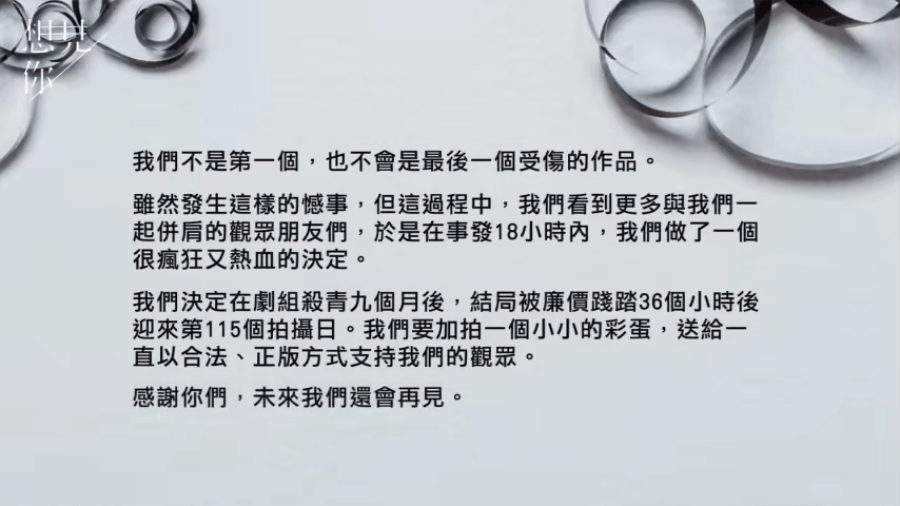
感谢你们,期待未来的相见。I know you’ll be back someday or one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