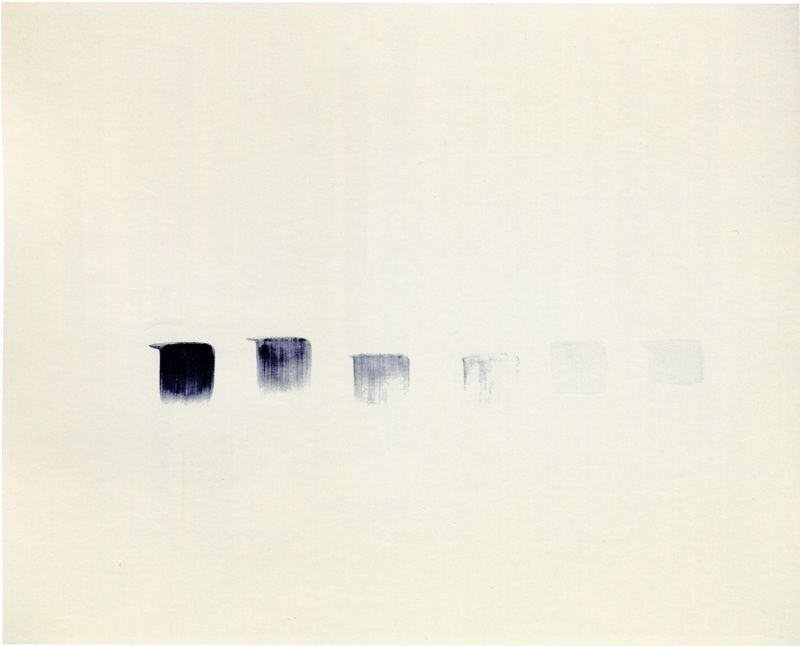講座紀錄:國際生產,臺灣製造──全球脈絡下國際藝術節策展及其市場(下)
其他 2018–08–24

時間:2018年6月6日19:00–22:00
地點:社會創新實驗中心A-2社會創新實驗大型活動講座
主談:王文儀(臺中國家歌劇院首任藝術總監)、鄧富權(臺北藝術節策展人)
回應:吳牧青(藝評人)
主持與提問:紀慧玲(表演藝術評論臺臺長)
紀錄整理:羅倩(專案評論人)、評論臺編輯群

∇藝術節政治現象:藝術節可以不與政治或市場協商?抵拒有必要嗎?
紀慧玲:
第四個提問,我想從臺灣或臺灣主體性看國際共製,臺北藝術節未來如果朝向大量的國際共製,我們可以怎樣在共製裡面談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這個概念?
鄧富權:
我先從島嶼這個概念開始。我來自一個很小的國家(新加坡),所以我對小國家比較感興趣。因為,我覺得就是去問「為什麼」(Why)?你是靠什麼存活(survival)?你的生存技術(survival skills)與工具(tools)是什麼?從小在新加坡就知道,小小國家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國家?卻又存在了超過五十年。從小的教育和思想洗腦我們,只能朝外,無法靠內,完全需要靠國際交流;於是,「關係」對我們來說很重要。我們的護照很厲害,去很多國家都完全不用簽證,而這就是全球競爭力。我很快速地說一下,我是新加坡第一代受過戲劇教育的,從十七歲開始。那時候,戲劇系也尚未有成立的條件。但,新加坡政府想透過文化在國際間找到認同跟代表性,而這是從文化沙漠的恐懼感開始,於是我們這一代才被帶出來。我們是從小就知道全球競爭力、軟實力、文化力與政治力(Global power、Soft power、Culture power and Political power)的整套關係。
我來到臺北的時候,也在想臺灣的立場是什麼?我曉得臺灣歷史很複雜,所以你們一直在談社會是怎樣的社會,生存跟未來。有些已經談到煩了,尤其是跟年輕藝術家談的時候。無可避免地,你們每天都有危機感,是一種內建的危機意識。從這個角度,我想問,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藝術家,從現在到將來的可能性在哪?我想分享,但不是針對個別藝術家,而是對外合作的概念與手法,有衝突(confrontation)、摩擦。我覺得,未來的方向是大家要越來越開放,是我要做的方向。
共製,大家都嘗試過。投資時間、投資更多更長的耐心跟對話,作品會越成熟。若只是快速的用錢,因為有錢,所以共製,短短三個月,可能產生很奇怪的成果。我希望的共製是:「藝術家自己提出來的案子,先做研究(research),把問題列清楚。剛開始可能不清楚,但經過過程(process)跟時間,磨擦一下,會變得完整,而交流與文化就會深。」我很強調過程,之前的製作經歷曾有花上兩三年時間才首演;所以,如果還沒準備好,是不該做商業演出。並不是快速去便利店買東西吃完就算,這是浪費,藝術也要有生態想法。
王文儀:
如果政治本身就是公共、大眾事務的話,我認為做劇場本來就是一個大眾的事情。而在公眾的參與機制上,我甚至相信「劇場是人類學習解決問題的所在」。因為,在劇場裡看見創作者的切入角度,讓一般民眾有了新的視野,是精神層面。製作是一個精密管理,創意又是心智的最極致表達,是人與組織管理的實踐。良善溝通是社會發展基礎,而劇場一直有溝通的本質,行銷是溝通的第一部,作品是溝通的第二部,演出後的交流是溝通的第三部曲。在數位化時代,劇場又是唯一人與人群聚碰面、產生溫度的地方。所以,我對劇場有萬分崇敬,更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多元有趣的地方。所以讓更多公眾參與、加入,是我認為最好的事。用政治話語,我願意我的劇場是一個多元組合、民主自由的地方。至於市場,我想市場是沒有辦法協商的,因為市場永遠在變化,我們只有觀察、理解、嘗試分析、給一些判斷,然後跟市場一起攜手向前。這是藝術產業最有趣的工作。面對未知,我前面說反求諸己變得相對關鍵。藝術產業,觀點與角度永遠走在前端,為了觀眾而調整或停滯,等於扼殺劇場的存在。創作上要誠實,行銷上則要有能力清楚地溝通。臺北這樣一個成熟市場,我們這些參與其中太久的老人,就會告訴你,市場是每兩年持平、第三年是衰退的、第四年再起來、兩年持平、第三年再衰退,第七年再衰退。原因可能真的是新觀眾、新世代沒有堅持的話,看到第三年就開始疲累衰退。到了第四年,理論上可能是全新的觀眾又再出現,高一變成大一,大一進來看演出,大一到大四,進入社會後就沒有空再看戲了。於是我們永遠在等待大一新生,這樣一個循環背後有一些理論與心得可以以後再探究。假如我們開始對應這個循環,需不需要在第三年、四年做最可口甜美的作品?以便留住觀眾?答案是也許會、也許不想、好吧試試看……像這樣沒有標準答案、持續性的提問,讓藝術工作變得有趣。所以,市場沒有辦法協商,只能夠手牽手大家一起走。能不能創造它?極有可能。畢竟任何一位大一新生都需要各位的輔導,推出有趣的節目,告訴他説我們怎麼看待劇場,劇場為什麼是一個重要的藝術形式,如果你也相信這個,我們就非常自信愉快地跟市場如傳教士般不厭其煩地推廣,然後我們也開始市場經驗的累積,知道哪一些步驟是無法省略、哪一些可以創新,在與市場接觸方法上持續創新、持續受傷,我認為是這個產業特別有趣的地方。永遠有不同的挑戰。
∇回應人時間
吳牧青:
講到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我想絕對不是狹義的政治。比如幾天之前,文儀(還是臺中歌劇院總監)如果坐在這邊,你可能會用一種政治的眼光去看待她的角色。包括富權,雖然藝術節不直屬於臺北市政府,是臺北市文化基金會,但它還是一個政府中介單位。因此,某個程度講,策展人就是一個臨時政治中心,重新去構思一個機構下的臨時機構,這個臨時機構如何被策展人策動。也有人會開玩笑說,用位階來看,有人也許當上臺北藝術節總監,過幾年,極有可能變成局長之類的。所以,藝術節時時在回應政治。
表演藝術也是很早以前就有策展人了。就說國際策展人這件事如何持續被運作,也不是這幾年。舉林人中的例子,以國際共製來說,他算是策展人作為製作人做得最好的,從一個很小的個體性做到自己也蛻身為藝術家。十年前他就做了《漢字寓言:未來系青年觀點報告》策展,迴響很不錯。文化局要推藝穗節,差不多也是那個時候,文儀還在的時候。從很多小的機制去看,之所以現在有很多方方面面,包括最近我在典藏藝術網推一個策劃講「稀缺見證者作品」,這幾年累積下來,我覺得某種程度上策展保持了一種有機狀態,有一些鬆弛性可以發展,當然會有一些市場壓力,這也可以回應剛提到的,國際共創的必要性在哪?我覺得這已不只是表演藝術界的現象,在更高層級的,可能是國家文化單位、文化政策,都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共製這種模式,在藝術節裡可以作為一個很好、很有效的橋樑,搭建國與國間合作的任務?有可能嗎?它有無缺陷?比如說,如果它為國內觀眾而做,媒合演給國內觀眾看,國外團隊也可能只是另外的(重要)臨時演員。或者,希望成為國外藝術節的跳板?我們必須質疑它的目的與有效,談共創,要有非常全面思考策略的問題。
講到市場,我覺得表演藝術有走向兩種「面對市場性」的權宜之計,一種是可以再現的,一種是不可拷貝性的。不可拷貝性的也許像明日和合製作所的作品,他們非常明確,做一些沈浸式的,難被複製的。比較正統鏡框式的,絕對會越來越多像英國國家劇院NT Live(National Theatre Live)那樣,開始被電影化,不只被虛擬實境化,還會進入數位拷貝蒐藏的可能。這部分應該很多已在進行。於是,正統的現場演出,愈來愈有觀眾市場支撐的壓力。我覺得,面臨市場的問題,當然不能像富權剛說的,到7–11買東西一樣,可能沒有這麼嚴重;但就像中盤商或經銷商,要賣掉,不能囤貨,壓力並不輕鬆。我相信臺北藝術節絕對有這個壓力。作為一個官方為主導資源的政府單位在後面,它的實驗忍受度到哪,是有待觀察的。今年也許是蜜月期,明年合製出來了,會是另一個檢驗。還有,我想講一下,藝術節真的是一個節或只是一個品牌?更多數的藝術節走向品牌,因為它第一檔節目和最後一檔節目,拉拉拖拖可以間隔到兩、三個月,你大衣脫下來準備要穿背心了,還是同一個藝術節,你會覺得它是節嗎?不會,它只是蓋上品牌的印章,可以成立,但已不是在特定氛圍下凝聚的過程。官方策展方面,希望它能不能跳脫只是節目企劃,更接近「策展」。國內有新點子舞展或者劇展、也有TIFA,還是趨近於品牌而已,以後是可以被重新打散的。比如視覺藝術,或是影展類策展,可以發現,界域的消失。因為我們去承載感受這些創作載體的媒介本身已經一直在交換,區隔越來越小。在兩廳院的調查資料裡,並無法顯示觀眾有多少是相關從業人員。在一個禮拜裡的兩三場重要演出中,會一直重複看到同樣的人,就可以知道重複狀況有多嚴重,而這部分是沒被分析到的。表演藝術之所以可以不用那麼媚俗,可能是靠這三千個鐵粉觀眾支撐了表演藝術約莫三成的核心買票族群。但,如何讓這群人不會垮掉持續保有熱情?大家都說把這群人養大,可能比你到外面大海撈針想辦法找個兩千人進來還容易。也許吧,但我不知道。這是一種抵抗。某種程度會來搞這行的人,都有自尊心,且不是朝向市場的。

∇綜合座談與Q&A時間
紀慧玲:
現在有很多國際共製節目,是跟國外的藝術中心、藝術節同步合作,從高行健《八月雪》時候就已經有了。請問文儀與富權,如何看待國際共製我們的主導性,以及國際共製對臺灣的藝術家、觀眾、臺灣的市場可能產生的意義。
王文儀:
對我來說,一直都是作品好最重要。跟誰共製?主導是誰?平台在哪裡?都是為了追求好作品。作品好,不論有沒有共製,每個單位都會搶著要。
鄧富權:
對我來說,過程比作品(product)更重要。因為你要進入跨文化的挑戰是很大的。如果缺少足夠的時間、空間,藝術家去追求、定義好一套問題,然後去研究,再去找他的夥伴,然後於國際間進行共創;沒有好的模式的話,最終的作品一定不理想。但,這套邏輯很有機的。問題是,在官方跟平臺組合的操作下,很少給到足夠的時間。我們如何保護藝術家的創作過程,就算最後是不好的作品,它的價值則在於對話、談判、交換。透過這個過程,大家才會領悟,無論好壞,是大家投入──深深地去投入、誠懇地去投入。我想問的是,是否我們要把所謂的評價,用一個比較平衡的方式,從計畫帶到過程,給出一個更足夠的空間?我們確實會受觀眾和官方的壓力,但如何保護藝術家與夥伴們去完成與過程,是可以重新衡量的。
紀慧玲:
我想富權一直很強調創造性的過程,但他講的也是很理想的狀況。跟談戀愛一樣,只要過程不要結果。確實我們很少談論過程,但以我寫評論的角度,是因為看不到過程,僅能以成品去談論,這也是藝術最沒有辦法估量的部分,也是最被忽視的部分。於是,如何重估價值,也許是看待藝術的另種方法。有沒有人要提問?
李宗興(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學生):
謝謝三位與談人精彩的分享,也謝謝評論臺辦這個活動。我有一個問題給富權,一個問題給王總監。
富權在剛剛的分享一直提到臺灣的年輕藝術家需要跟國際藝術家合作,就讓我想到你之前最有名的製作Pichet Klunchun and Myself(《泰國製造》),傑宏貝爾(Jérôme Bel))與皮歇(Pichet)合作作品,你是不是有意識地在複製這樣一個國際共製的形式,讓在地與國際有名的藝術家合作。同時,也非常多的舞蹈學者質疑,強調兩者之間,兩位藝術家合作關係的權力不對等,不知道你怎麼樣看待或是如何回應這樣的權力不對等?
另外的問題請問王總監。您一直提到,因為臺中歌劇院本身的空間,以及所在的城市,產生在地脈絡,來回應我們今天的講題「『全球』脈絡下的國際藝術節」。我好奇的是,當您在挑選全球作品的時候,如何看待全球?全球其實常常只是北半球。這些作品,如何在臺中產生意義,怎樣連結地方與全球的脈絡?
鄧富權:
Pichet Klunchun and Myself這個作品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產生的。我邀傑宏貝爾來曼谷,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於是,他提議要先跟一個傳統藝術家進行對話。當然他一到曼谷就遇到總總交通、蚊蟲叮咬的現實狀況,只能有三次機會和皮歇對話。然後他們就決定了,以對話為一次報告(Report)──起初沒有想過是一個演出(Performance)。很妙地是,兩位藝術家在舞臺上很自然地複製了他們的對話,完全沒有排練,就是很深刻的談。在舞臺上呈現那樣的經驗,看來就好像是演出(雖然我們最初根本沒想到是演出)。後來有些國際策展人來到了曼谷,看到這個最後變成演出的報告呈現,就將其帶出了曼谷──這是傑宏貝爾也沒想到的。比利時首演前,關於不平等是有過修整的,重新檢視兩位藝術家是否有平等權力、分享權力。但,任何觀看者都有自己的眼光,它有平等嗎?需要平等嗎?傑宏曾跟皮歇說,我不想來你的城市,因為我不想遇到你的觀眾,在你的場地裡表演。但他們最後決定,他們有權利決定是否繼續這個計畫、這個城市、這個表演。這是可以詢問藝術家的,而不是提出很資深的意見去判斷裡面是否夠民主。我有點慚愧的是,因為我給傑宏貝爾的經費和時間只有一個禮拜,加上我沒有要求他做一個製作;於是,情況是偶然的,最後變成可以被複製的演出。我之前和很多藝術家做過不同的共創模式,像是和另一個印度女性藝術家則花了五年時間。對我而言,最理想的情況下,應該要有足夠資源給藝術家;可是資源是有限的,有些多有些少。不論資源多寡,我不可能控制產出,只能帶著戲劇顧問的身分,如果這個藝術作品還沒有完成它的旅程,提醒藝術家思考是否冒險推出,或者再延遲下去。作為一個製作人,我會設想怎麼把過程再拉深,直到成熟才首演。回到傑宏貝爾和皮歇的製作,那是超越我原本規劃的。
王文儀:
對專業的營運團隊來說,臺中是一個新興市場,而對觀眾來說,我們對他們也是全新的。我們的出現,臺中期待了很久,不是期待我們,而是期待這件藝術場館的事終於要發生了。我們理解的臺中觀眾組成是這樣的,臺北的主力觀眾大概20–35歲,但在臺中則年長十歲以上,35–50歲。這是因為這群觀眾在文青年代的需求是完全沒有被滿足的。藝術電影、展覽、國際演出、劇場演出等,在這個城市的選擇非常少。這些僅有的場域之間,又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直接將文化、文化人湊在一起,久而久之就降低參與興致。而高鐵出現之後,文化人口流動到台北,比例不高,但有了些許滿足。所以現在歌劇院的出現,讓他們年輕時的渴望終於可以被滿足。35–50歲的觀眾事實上是非常棒的組合。在這個人生階段,可支配的時間、可支配的金錢比較寬裕,而思想也成熟到可以快速理解許多作品的意涵。他們其實才是藝術產業最想吸引的一群觀眾。只是現在他們還在「期待又怕受傷害」的階段。所以面對他們,我們要小心翼翼經營,所以之前講的浪漫與理性之間,這時就有了一種數學行為要出現,就是票券張數、安全名單、危險作品之間的算數,看看自己有多少關卡要突破?怎麼突破?可以說,面對臺中,我們有臺中意識、沒有臺北觀點、或南北半球觀點,只有藝術觀點。給這群有興趣知道更多的臺中觀眾一些好東西,讓每個人都可以在劇場裡找到自己夢寐以求的。藝術策劃與政策,最怕父執情節parenthood,就是由策劃者決定什麼該看、什麼不該看。我們面對臺中這群好奇觀眾,則是什麼都會陸續推出,而且保證是這類型中最好的。面對這些人生經驗成熟的觀眾,如果每一年都有一些觀念上的突破,就可以培養一群成熟的文化觀眾、進而真正建立一個文化環境、文化城市。
觀眾(街頭藝人):
我本身是街頭藝人,不是劇場。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街頭表演其實是親近觀眾的,可以免費也可以付費,就這點來說,想請教兩位主講人,這是否破壞藝術的高冷性?第二個問題,我很明顯的感受到,對於策展,兩位有完全不一樣的看法。我想問的是,策展人在邀請藝術家的時候,是否必須對藝術家的生活負責?我的意思是,策展人是否應該要付演出費給你邀請來的藝術家,還是說你只要給他一點點錢,剩下的讓他自己賺。
鄧富權:
我先回覆付費的問題。藝術節當然不會要求藝術家免費表演。我相信之前沒發生過這種情況,我也不希望會發生這種事情。之前做製作時,也會代表藝術家在產業做買賣角色,有些平臺資源多,就是要付多一點點。偶爾也會想到,藝術家去印度表演,印度的經濟情況就是不可能有所謂的國際標準工作費。這時,我就會問藝術家,你想去嗎?你多想去?為什麼要去?思考過這些條件後,才會決定,甚至免費去表演。我們要了解這種狀況,尤其是亞洲有很多小品牌是需要互相支持的。所以,在某種情況下可以免費,只要達到團隊共識。資源多少,預算多少,我都會說明,要不然就是不平等的交換。
我本身很欣賞街頭藝術,今年也邀請陳星合和他的團隊參與藝術節。街頭藝術有不同的經濟模式,很多成功的街頭藝術家是不用靠藝術平臺過活的,且在更自由的空間裡活得更好。你一旦進入舞臺,就必須接受觀眾跟評判。於是,街頭同仁是否能承擔這個壓力,也是主辦人和街頭藝術家經過討論、建立共識才可決定。
王文儀:
街頭藝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每一個演出都在戶外,地面上用360度環景思維創作之外、還可以想像天空的加入,非常令人興奮。戶外街頭演出與室內票房,我不認為有任何扞格之處,反而極有可能互相幫助。目前的街頭藝人之於街頭藝術,雖然規模上有差異,但只要是一個藝術作品就不應該被免費邀請。建議每個環節都落入合約,讓細節理性呈現。專業的合約其實非常細節,像我們在辦理舞蹈節目時,舞者都希望後台有物理治療師,而這項費用,通常是舞者要自行負擔的。而後台難免希望咖啡、點心等,這些也都會在合約中載明,從不會模糊行事。所有演出都是一個合約談判過程,沒有一定的答案。
周伶芝(藝評人):
剛剛兩位都提到,藝術節儘管沒有完整論述,其實都有問題意識在裡面,無論是反映了某種來自城市生活機制的觀察,或說藝術節必須要定義當代這件事,我認為這都表示藝術節必須以問題意識作為出發點,因為藝術節的製作、規格,還有整題節目規劃,包括財政、觀演習性等,是否要和政府、市場協商,都得透過一個完整的策展機制,回應對於現代城市生活的某種觀察,不論是比較激進或是甜美。我想提問的兩個問題,一是大劇院時代的來臨,象徵了一種文化資本的號召,但某種程度也反映出一個城市文化空間的失衡可能。在一座城市裡面,也許可以有藝穗節反映大大小小的文化空間,可是當劇院推出一個策展時,它是否能透過節目的策劃,回應文化空間失重的狀態。比如德國某藝術總監說開放劇院讓難民使用,讓劇院成為一個文化跟政治的活動中心,這雖然是比較激進的例子,但可反映我剛剛說的,場館面對城市生活的社會責任和藝術定位。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劇院,盡量開發後臺或是運用停車場、建築物裡的非演出空間,作為參與或沈浸式劇場的空間使用,擴大範圍、也表現一種空間釋放和經濟效益。但更常見的是,美術館大舉運用表演藝術,因爲它的展場空間較鏡框式劇院更為自由彈性,也讓它的臨場展演性變得更相輔相成。前陣子上海有個當代美術館的總監,發下豪語説,以後電影院和劇場都不用存在,只要有美術館就好了。因為視覺藝術長期建立論述上的話語權,更懂得透過策展的方式去策動,以及運用空間的彈性來創造更多多元新奇的關聯。在這樣的當代藝術情境下,從場館或者一個城市藝術節的面向,你們的想像,會如何用策展的方式,回應當代藝術創作的情境。包括牧青的提問,英國劇院將現場表演影像化,代表他們承認媒體轉移的必要性,表演藝術不再強調當下,而是透過不同媒介的轉移來創造典範,那麼劇院如何去面對這樣的媒介轉移和檔案製造?而藝術節又是怎麼去看待這些多重的生產關係?
鄧富權:
我不屬於大展館,所以很難回覆。我可以分享,這五、六年,大的美術館TATE、MoMA,開始很大量的把劇場藝術家吸進他們的系統裡。很多知名的劇場藝術家,也抵抗不了誘惑,樂意地去美術館表演。這回到場館的憂鬱,第一,劇場不只失去藝術家,培養這麼多好的藝術家,現在跑去別的領域;第二,還失去買票的觀眾,因為通常在大美術館場合是免費看表演的。所以,要保衛劇場空間,劇場應該怎麼再走下去,大家也很焦慮。如果美術館可以跨領域、跨邊界,那我們其實也可同樣在劇場裡面創造跨域。劇場功能並不比美術館差,而我們需要找不同的方式回應,把跨領域的基本功能帶回來。劇場除了展演、表演,還可以做什麼?盧辛達‧柴爾斯(Lucinda Childs)有好幾個作品都是美術館呈現,當時(美國七○年代)的美術館是很崇拜舞臺的,將多委託(commission)完全交給盧辛達。現在也許我們可以説,Hey!美術館,不如你跟我們合作好了,不要再各搶各的,我們可以回到一種比較成熟的討論方式,做不同的共創。
我也想過,在北藝中心還沒蓋好的情況下,我有很大的自由去和不同空間、不同單位合作。因此,明年、後年會引導不同的嘗試方式,並不會只限在劇院。但是,我會保護場館,只會把我真正有把握跟相信的藝術家和實踐擺在舞臺上。其他追求非劇場空間的作品,才跟別的場館合作。大家要多去思考不同的合作方式,而不是變成搶地盤、搶藝術家,這不是很健康的情況。
王文儀:
我的作法也是,請大家一起來做。驫舞劇場在凸凸廳演出,而同一個場地放過影片、做過展覽,我們也改善了這個廳的屋頂懸吊機制,電力系統也在改善中,有許多可能可以持續發生。我深信這本來就是劇場的功能,劇場本來就是多元的,而我相信還有許多素材被遺漏、許多可能未被開發。網路世代、去美術館演出、美術作品進入劇場、英國國家劇院開始電影系列等,都告訴我們直接去擁抱各種可能、然後做得更好。一個劇院,我想像他是雪梨跟克拉科夫的結合。白天一堆觀光客沒關係,像白天的雪梨,這本就是公共建築的任務,但到了晚上,一群藝術觀眾就出現了,把座位坐滿,興致盎然地觀賞,演後邊喝香檳邊討論、就像一群哲學系學生飢渴地想跟發表辯論、藝術家也在,或嚴肅或輕鬆都好。克拉科夫有全球最古老的大學跟舊城的美麗城堡,新市區日間的街道也是安靜,大部份時候是樂透窗口有些人潮,劇場所在地就在街角,不用偉大建築刻意彰顯,等到了演出前,觀眾蜂擁而至,不是來看熱鬧那種,看得出來是真的藝術觀眾。我有點期望臺灣未來是這樣的文化生態與生活。我相信假以時日,會發生。
吳牧青:
講到文化空間、資本集中,大劇院時代來臨,你會看到很多藝術家逃離劇場,就算只是逃離幾步都好。逃離到更衣間,逃離到不要黑盒子,逃離到地下停車場,就算還是在兩廳院,這都是一種逃離。同時,如果用經濟體系概念,在美術館發生的表演,對於劇場的買票觀眾,構成了一種外部性溢出,但另一個觀念,也可能是禮物經濟,相互交換。富權剛講到自由度的問題,等兩年之後、北藝中心蓋好,反而喪失了一部分自由,你必須要和這些文化資本空間集中的力量結合,因為它是你必須應酬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角力的過程,如有界域的模糊,它必然是在各種鬆動的情況下造成,什麼樣的場館,創作的風貌是怎麼?都有可能重新定義以後的場館功能是什麼,包括美術館也一樣。所以,關於哪個圈子收編誰,或或視覺藝術圈也會覺得大部分的經費都給表演的拿走了,永遠講不完。我覺得,在藝文的創作領域裡面,不是絕對被資本操控,禮物性的交換,賞賜了某些可以跨出界域的好作品,不受市場力量左右,不需要靠賣多少票證明它是不是優秀,也不必然就排擠劇場買票人口。如果拉開來看的話,我覺得它真正的意義在這裡。
(END)
2018–08–24首發於表演藝術評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