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人口經濟化的實驗
記得在高中生物課上,老師教給我們兩種種群數量生長的曲線模型,J型和S型。J型表示生物在理想的資源無限的環境中呈指數型增長,而S型則表示生物在非裡想的環境中增長率先上升後減緩的現象,隨著種群數量逐漸接近環境的負荷量K,增長率也逐漸趨緩至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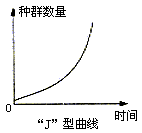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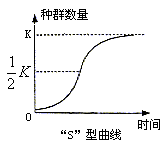
課程當中還提到S型曲線對計劃生育的啟示:我國的人口環境容量是有限的,當前眾多的人口已經為我國造成了沈重的負擔,因此應以環境容量指導人類計畫生育,限制人口無限制地增長。
1982年中國將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寫入憲法,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82)。在官方表述中,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管理,人口會像J曲線一樣不受控制地增長,超越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造成嚴重的社會資源短缺問題。在此邏輯下,生育成為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而必須管理的對象,生育的決定權由個人轉移給了國家。
1995年國家進一步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計劃生育被看作一種優化家庭資源分配,生產符合國家發展需求的高素質人口的手段。縮小的家庭規模將有利於減輕家庭經濟負擔,提高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質;計劃生育還能夠促進農村地區消除貧困,讓農民擺脫“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不良循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995)。
學者Michelle Murphy在The Economization of Life中提出人口經濟化的概念(Murphy 2017),指出這是一種以宏觀經濟為目標,用科學的方法衡量個體價值,從而將人口納入公共政策管理的體制。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將控制人口視為經濟計畫成功的先決條件,用經濟理性和統計工具將鮮活的個體轉化成可衡量的數字,以實施計畫經濟的手段實施計劃生育,實現社會主義人口經濟化的過程。我想探究的問題是:在計劃生育中人口被經濟化的過程是怎樣的?計劃生育發展了一套什麼樣的語言將人口納入經濟的範疇?計劃生育建立了何種制度性的安排?計劃經濟如何衡量人口的價值?經濟化的人口又如何反作用於人對人口的理解?
1. 宣傳倡議——計劃生育的誕生
1798年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出版了《人口論》,人口論的基本思想是人口的增長呈等比數列(如:2,4,8)而食物供應的增長呈等差數列(如:1,2,3),因此食物供應的增長無法滿足人口增長,只有通過戰爭、瘟疫、飢荒、貧困和道德等方式抑止人口的過度增長(林骙 1926)。馬爾薩斯對於人口增長的預測類似於J曲線,而S曲線則由美國生物學家Raymond Pearl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提出。Pearl將人口的增長類比於一個封閉瓶子當中的果蠅,認為人類文明就是限制人口增長的玻璃瓶,而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可以通過公共政策調節。Pearl的研究推動了當時以優生學為主流的人口研究轉向經濟學,將人口問題與經濟發展水平、國家規劃連結。
文化研究學者Lawrence Grossberg批評現代經濟學已從社會當中脱嵌,成為一個獨立於社會,可以自圓其說的體系(Grossberg 2010)。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學與人口學相結合發展出的人口經濟學,將人從實際生活的社會環境中抽離異化,化約為與生產相關的人力資本,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察人口問題。微觀人口經濟學則將孩子視為一種耐用消費品,用消費者選擇理論來分析家庭生育決策(李仲生 2002, 17-20)。
經濟化的人口理論,對中國計劃生育的決策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爾薩斯人口論自19世紀傳入中國,雖然屢遭批判,但是對於人口過快增長造成的資源短缺的擔憂逐漸在中共內部形成共識。五十年代初因為土地改革導致的移民潮使城市人口失業率激增,由此造成糧食短缺問題,為保障糧食供應而推出的統一徵購制度又造成了農村的糧食危機,再加上內戰後激增的生育率和雄心勃勃的五年計劃,令中央的人口政策由延安時期的鼓勵生育轉向反對高生育率(White 盛學文 1994)。劉少奇在1954年的會議上發言體現了黨的高層如何看待人口問題:
“人口增加後有沒有困難?有困難,困難很多,而且一下子解決不了。例如北京的糧食、布匹、藥品就都不夠。國家在這方面有很大負擔,很多個人也有困難。總之,小孩生多了困難很大,父母、家庭、小孩子本身都困難,社會和國家也困難。衣、食、醫藥、學校等等都不夠,而且一下子也解決不了。因此,應當贊成節育,不應反對。”(劉少奇 1954)
劉少奇擔憂激增的人口將導致公共資源和家庭的負擔,但此時官方的人口政策仍然是“節育”而非“計劃生育”。計劃生育的提出與毛澤東倡導的由下至上制定宏觀計畫的“計劃運動”相關聯,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奠定了官方計劃生育的基礎:
“我認為人類在管理自己方面是最不稱職的。它有工業生產,紡織品生產,民用物資生產,鋼鐵生產的計劃;(但)卻沒有人的生產計畫。這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大笑)如果(我們)這樣下去的話,我認為人類將會過早地陷入衝突之中,加速走向滅亡。”(White 盛學文 1994, 408-409)
東亞研究者Tyrene White指出,毛澤東將人口再生產描述為一個無政府的失控的過程,如果無政府、無規律的人口再生產相當於經濟領域的無政府主義一樣是反社會主義的,那麼將生育納入社會主義的宏觀計畫也因此獲得了合法性。1970年周恩來在會議上說:“計劃生育屬於國家計劃範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你連人口增加都計劃不了,還搞什麼國家計劃(史成礼 1988, 158)!” 人口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爲在全面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唯有人口增長不受控制,與人口增長相關的糧食、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等一系列宏觀經濟計畫也就失去了控制。
為了建設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中國於1952年成立了國家統計局和國家計劃委員會,1953年由國家統計局負責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結果成為制定計劃生育目標的決策依據。後來的二十多年內,國家主導的節育活動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計劃生育的管理機構,從中央到基層培養了一支轉職計劃生育的幹部團隊,由國家財政負擔龐大的計生費用。然而此時計畫生育的落實仍然以政府的宣傳和派出醫療衛生人員提供節育服務為主,強制性的“一胎化”政策直到1979年才出現。
2. 強制命令——“一胎化”到“女兒戶”
毛澤東逝世後,以華國鋒為首的新領導班子急於利用經濟發展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因而提出雄心勃勃的“四個現代化”目標,並且提出用一個新的貨幣指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結果。為了快速提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必須提升經濟總量,減少人口增長,因此控制人口成為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任務。時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華發表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的長篇文章,提出為了“爭取本世紀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長率為零”的目標,“必須大力提倡和推廣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 (梁中堂 2009, 64-73)。1980年她進一步提出一胎政策要達到農村90%,城市95%的遵守率,和二十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的指標。經過從上到下的政治動員,不到一年時間全國的29個省就有27個各自制定了本省的計劃生育暫行條例,明確規定用經濟、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控制生育,山西省的計劃生育暫行條例還出現了類似於後來“計畫生意一票否決制”的官員任免措施。從此計劃生育從自覺自願變成強迫命令。
1973年成立的國家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1981年改為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計劃生育部門從此由一個臨時性辦事機構轉變為政府的組成單位,再加上“一胎化”推出前二十年已構建好的延伸到每一個居民點的龐大計劃生育隊伍,為“一胎化”的強制實施提供了組織基礎。
“一胎化”的合理性更得到了科學的驗證,1979年在成都舉行的人口科學討論會上,火箭專家出身的宋健團隊運用控制論、系統工程和計算機科學,快速、精確地預測了人口未來的增長趨勢,根據他們的測算,即使是推行“一胎化”,人口在未來二十五年依然會增加。火箭專家的測算基於一系列不靠譜的假設,而且絲毫不考慮人為因素和科技對預測結果的影響,然而他們的預測很快出現在主流媒體上,為“一胎化”作理論背書(方鳳美 2017)。“一胎化”的必要性經過科學的論證和宣傳系統的推廣,在當時的領導幹部中形成共識。
聯合國於六、七十年代通過的一系列人權宣言規定生育權是一項基本人權,每一個人都有權自由地決定,不應該被國家強制力干涉。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受社會、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自然發生的結果。然而中國將生育率下降作為目標,中央制定的人口指標如同其他計劃經濟時代的指標一樣層層加碼,脫離現實,以目標倒逼強制性“一胎化”政策的執行。前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錢信忠曾在會議上說:“如果一九八五年把人口增長率降低到千分之五左右,當年淨增的人口才能降到五百萬左右。這就要求一對育齡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 (梁中堂 2014, 11-44)。”按他所說,“一胎化”是由人口目標倒推出來的必須實行的政策。錢信忠上任後,將開展結紮絕育手術作為工作的重點,在農村地區強制推行大結紮和人工流產,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野蠻的行徑。1983年底錢信忠被罷免,然而他留下的“一胎上環,二胎結紮”,直到國家開放二胎之前都是計劃生育部門的基本工作方法。
強制執行“一胎化”政策激起的民怨沸騰,令中央不得不修正政策。其實1982年中央頒布的“11號文件”就規定了“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的安排”,為了淡化重男輕女的色彩,文件用“有實際困難”指代第一胎是女兒的“女兒戶”。該文件頒布後卻遭到已走在“一胎化”道路上的計劃生育部門在實際工作中的抵制,根據後來的計算,1982年生育二孩的夫婦占不到當年生育一孩夫婦的5%。然而也是從1982年開始,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開始超出正常區間,從此一路高歌猛進,再也沒有回歸正常(UNICEF)。
1984年中央又頒布“第七號文件”,以“開小口子,堵大口子”為方針,同意將生二胎的比例擴大到10%。然而文件下達後在各地的執行程度不一,直到1988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要求各省以“女兒戶”為核心修訂計劃生育條例,“女兒戶”才成為全國農村的一般政策。
“第七號文件”規定各省可以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為各省靠計劃生育罰款斂財開了方便之門。地方官員在收取超生罰款(後改名為社會撫養費)上有極大的自由度,可以達到一年家庭收入的數倍,而且罰款的範圍不斷擴大。女性未婚生育要罰款;未婚同居要罰款;不採取避孕措施,即使沒有懷孕也要罰款;不參加常規孕檢還要罰款(方鳳美 2017, 45)。與之前國家承擔計劃生育的巨額開銷不同,中央鼓勵地方政府自行籌集計劃生育工作的資金。尤其是中國實行土地稅改革後,各縣鄉和村政府失去了獨立的收入來源,更加依靠收取社會撫養費維持開銷。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和使用長期不透明,成為了滋生腐敗的溫床。
1990年中央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票否決制”的問責機制,所有幹部如果未能完成轄區內的計劃生育指標,無論工作幹得多好都要面臨處罰。“一票否決”刺激官員採取更激進的措施。一個極端的例子是1991年山東冠縣、莘縣的百日無孩運動,當地婦女無論懷第幾胎、孕期幾個月,一律強制人工流產。計劃生育執行過程中大量的殘酷暴力行為都由基層的計生官員執行,他們大多數都清楚,無論自己做什麼都不用承擔刑事責任,因為完成計生指標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方鳳美 2017, 45)。
3. 計劃生育的後果——未富先老
在計劃生育政策持續多年的強制落實下,我國的出生率自1992年起就處於人口自然更替率以下,但因為人均壽命增加,人口總量還保持增長。2000年中央頒布人口的“8號文件”,重申“人口過多仍是我國首要的問題”,計劃生育的主要任務由嚴控人口數量轉向“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李琦 2019)。江澤民在90年代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指出“人口、資源、環境三者的關係,人口是關鍵”,為以往人口與資源衝突的論述中,增加了人口與環境的衝突,而人口資源環境三者都是對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90年代的人口政策,轉向可持續發展和人自身的發展,人口工作中倡導的“以人為本”並不是以家庭的生育意願為本,而是把人打造成符合國家經濟利益的高素質的人口。
儘管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逐漸受到重視,但國家計劃生育部門仍然擔心“一放就鬆”,沒有管控的人口將如馬爾薩斯預測般爆發式地增長,因此提出“放寬”的同時“收緊”,逐步放開生育限制的同時繼續落實“一票否決制”。民間主張放開生育甚至取消計劃生育的呼聲經年,但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才將“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去掉,代之以“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李琦 2019)。2015年全面開放二胎,然而收放並舉,超生、未婚生育等仍然屬於違反計劃生育法而應受到懲罰。
然而由於經濟發展和長期政策的影響,再加上女性經濟地位提高、生育成本和住房價格高企、鼓勵生育的傳統被打破,人們的生育觀念已經徹底改變,每一次生育政策的放寬都沒有出現預期的生育率增長。中國或已步入低生育率陷阱,進入難以扭轉的未富先老狀態。而反對計劃生育的話語,多是從計劃生育的後果反對計劃生育,如養老金虧空、老無所依、老齡化社會不利於經濟和科技發展等,鮮少批判計劃生育背後科學和經濟至上的思維方式。
計劃生育政策管理的是全部的人口,但卻由女性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痛苦和犧牲。“一胎化”政策自誕生之初就伴隨著對嬰兒的性別選擇,女嬰遭到遺棄、殺害和虐待,B超技術的推廣則把性別選擇的時間提前到孕期。後來推出的“女兒戶”政策目的是為了緩解幹部和群眾之間因為“一胎化”而造成的緊張關係,卻更加劇了性別歧視。女性的身體承受絕大部分的絕育和避孕手術,如果生了女嬰還要承受家庭的壓力。女性的生育權受到來自家庭和國家雙方的干涉,一些地方條例甚至規定對精神有毛病或尤其太嚴重遺傳病的人實行強制流產。 女性成了家庭生育意願和國家計劃之間衝突的犧牲品。
計劃生育和流動人口管制都是國家宏觀人口調控計劃下的一部分。計劃生育政策通過與控制人口流動的戶籍制度、工作單位綁定,確保了依賴工作單位提供全方位生活物資和福利的城市職工無法承擔超生的後果。違反計劃生育出生的孩子,包括未婚生育的孩子,則被視為搶佔社會資源的令人嫌棄的人,需要向計生部門繳納社會撫養費方能取得戶口,成為合法的公民。計劃生育與戶籍的結合,將公民權明碼標價,只有符合政策出生的人才擁有完整的生存權,不符合政策的人口則被視為公共資源的掠奪者,不受歡迎的人。
4.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計劃生育並不等同於一胎政策,強制性的“一胎化”直到1979年才出現,且數年之後就被農村地區推行的“女兒戶”政策取代。計劃生育的誕生,與國家領導人對於“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的基本國情和人口增長不受控制的認識有關。而激進的“一胎化”政策的推行,則與國家急於實現現代化建設的目標相關。“人口必須進一步控制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從經濟上算出來的”:如果2000年中國人口超過十二億,那麼“實現四個現代化必然化為泡影”(李琦 2019)。
鄧小平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之上提出了二十世紀末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是在充分測算中國人口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
“我們的現代化標准,就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達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 1000美元。我們經過反復研究,覺得可能 1000美元還是高了一點,因為必須考慮到人口增長的因素。所以我們這個目標放到人均 800美元的水平上。“(《鄧小平年譜 ( 1975—1997)》 (下),第 836頁。)(李琦 2019)
鄧小平對於世紀之交的宏願,已經有了現實的答案,2000年中國人口為12.66億人,大大超出了12億人的目標,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949美元,基本達到了小康社會的目標。一方面,成功實施人口控制政策,被視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人口紅利”被視為國家經濟飛速發展的動力。在我看來這兩者並不矛盾,兩種觀點都將人口視為與經濟密切相關的社會資源,未出生的人口是降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隱患,已出生的人口則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
有部分主張取消計劃生育的人,提出以市場調節的方式控制人口。江澤民回應:“通過發展市場經濟自然而然地降低出生率,那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利於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李琦 2019)。”無論是反對者還是支持者,雙方都用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調節供需關係來理解人口的自然更替,將人的生育行為想像為純粹理性計算的過程。
Grossberg曾批判在當代,經濟邏輯已經延伸到了人類社會的各個角落,在普通人心中具有類似於自然定律般的超然地位(Grossberg 2010)。在我看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中國執政者和平民百姓心中也具有類似於自然定律般的超然地位,任何對人口管制的鬆懈都將導致人口的激增,從而對資源和環境造成壓力,拖垮經濟發展。人口被看作一個獨立於社會運行的體系,可以像機器一樣按幾個按鈕生育率就控制生育率的上升或下降。國家則被政策制定者看作一個以發展經濟為最終目的的機構,人口、文化、環境、資源都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資源。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在以國家為名的經濟體看來,人則是手段,不是目的。
現代社會的經濟化,是將現實世界豐富多彩的人類世界,窄化為只涉及金錢利益的經濟關係。經濟化的過程包括:發展語言體系,建立制度性的安排,衡量被管理的對象,以及上述條件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的連結(許寶強 2020)。在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經濟化的過程中,受到馬爾薩斯人口論影響的國家領導人、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源源不斷地為控制人口的合理性貢獻話語,經過國家宣傳系統和計劃生育工作者的宣傳教育,人口控制論深入人心,就連反對計劃生育的人也忍不住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分析利弊。制度建設方面,計劃生育實施過程中建立了從中央深入到基層的轉職行政隊伍,不斷完善計劃生育法律和條例。為確保政策的推行,計劃生育的指標與領導幹部考核、戶籍制度和工作單位掛鉤,圍繞計劃生育的罰款催生了地方財政腐敗的空間。
計劃生育的底層邏輯是以發展經濟為目的,培養促進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政策制定者眼中的人不是擁有個體感受、思想、經驗和情感的人,而是從事生產和消費的經濟體,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分母。計劃生育將暴力施加在女性和未出生的女嬰身上,當代中國人口中年輕男性比女性多出多少,就代表有多少本該出生的女孩被消失。只有符合生育條件出生的人才擁有完整的生存權,而不符合政策的人口則要“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人在出生前就被政策決定了是否有活的價值。
人口經濟化將人看作是經濟體系中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要超越人口經濟化,唯有把整體概念中的“人口”打散成具體鮮活的“人”,把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看作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承認生育權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給予每一個人自由發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