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們的媚俗時代
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想起一次義教的經歷。大學一年級寒假在貴州山區一間小學待了四天,負責教小二至小五的學生。義教最後一天,離別的時候有個陌生臉孔的小六女生走過來跟我說:「哥哥,我想好好看清你的臉,把它刻在我的腦海裏,那我就不會忘記你了。請你也好好記住我!我會用功讀書,將來考到香港的大學來找你!」我當時內心激動不已,想到農村的孩子如此勤奮上進,但任憑他們如何奮勇與命運對抗,最後真正能走出大山的卻寥寥無幾,難過得潸然淚下。現在回想起來,這幕離別難免有點滑稽可笑,那個小六的女生和我是都沾染了米蘭昆德拉所寫的「媚俗」,才會因為一個毫不認識的陌生人不知所以地放聲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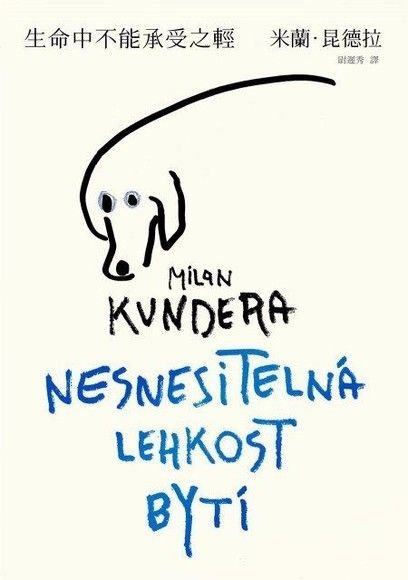
媚俗:自己感動了自己
「媚俗」在日常的語境下多數應用在藝術創作之上,用作形容遵循商業化公式來迎合大眾口味,而無實際價值的作品,平日濫於催情的愛情電影便屬一例。但是,米蘭昆德拉的「媚俗」比日常用法有著更深層的意義。
「媚俗的源頭,是對存在(『存在』可以理解成『事物』)的全盤認同。」
米蘭昆德拉的「媚俗」可以理解為自我感動類的情緒。我們將眼前的事物浪漫化,賦予事物超過其本身價值的意義,最後自己感動了自己。在書中,米蘭昆德拉寫到一個美國參議員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後感動到淚流滿面。
「參議員把車停好;孩子們下車,跳上一大片草地,衝向運動場上的一棟建築,那裏有個人工滑冰場。參議員留在駕駛座,一臉夢幻地望著四個小小的身影在那兒奔跑;他轉頭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他用手畫了一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和孩子們都圈了進去:『這就是我所謂的幸福。』」
為何民主國家的參議員,看見身旁來自共產國家的女人,再望向在草地奔跑的小孩,就聯想起幸福呢?若然小孩走出參議員的視線後不慎跌倒,又或者打架起來,那又怎麼說?
「媚俗讓人一滴接一滴,流出兩滴感動的眼淚。第一滴眼淚說: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多美啊!第二滴眼淚說:可以跟全人類一起,因為看到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動,多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淚,造就了媚俗之所以為媚俗。」
我們的日常生活亦不乏「媚俗」的例子,譬如當提起初戀的回憶,我們就會預設那必然充滿著遺憾美,自動過濾當中不愉快的經歷,亦不會想到初戀對於某些人來言可以意味著不堪回首的過去。又或者在暗戀過程中,花費無數個夜晚為心儀對象編織頸巾,深深被自己為對方的默默付出感動,但沒有想過對方是否需要你織的頸巾。
上帝不拉屎
自我感動有甚麼問題呢?米蘭昆德拉指出,在將眼前事物浪漫化的過程,為了維持美好的想像,我們會否認一切與之不協調的東西。譬如我們會抗拒想像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做愛、上帝有直腸會拉屎,因為這些污穢低俗的情節會毁壞我們腦海中美妙的畫面。所以米蘭昆德拉說:「媚俗將人類存在本質上無法接受的一切事物都排除在它的視野之外。」
套用在香港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示威者受到警方不合符比例的武力對待,過萬枚催淚彈、示威者被警棍打到頭破血流、女示威者當眾被掀起上衣、無數示威者被警察性侵、殺害的傳言、三隻被射瞎的眼睛⋯⋯然而若果我們沉溺於「雞蛋撞向高牆」的想像,選擇性地過濾黑衣人士在馬鞍山天橋焚燒老伯的畫面,無條件合理化「手足」的一切行為,我們就成為了米蘭昆德拉筆下那些「媚俗」之人。

不過,我們不可能完全擺脫「媚俗」。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因為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是超人,也沒有人可以完全擺脫媚俗。不論我們如何輕衊媚俗,媚俗終歸是人類境況的一部分。」
極權的「媚俗」
我們真正要慎防的是極權的「媚俗」。梁文道將極權的「媚俗」解釋為情緒的專制,「這種專制的重點不在於控制人民的行為,也不在於控制每個人的思想,而在於控制他們的情緒。以正義和正確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須在恰當的場合表達出恰當的情緒,哪怕那些表達有點違心或矯揉造作。」

情緒背後其實隱含一種價值判斷,比如聽到國歌奏起感到激動,就反映你對政權的認同。當我們要求對方展現和自己一樣的情緒,就是強迫其他人作出相同的價值判斷。為何所有人看到國旗都要流淚,而不可以覺得噁心;見到閱兵典禮都要振奮激昂,而不可以輕衊呢?
專制政權精心透過學校教育、媒體渲染、法律手段操縱民眾的情緒,從而使民眾不經思考地全盤認同政權,否定所有與美好國家想像不協調的批評。若果我們盲目跟隨被煽動的情緒行事而不加以思考,我們最終將會喪失感受自己真實情緒的能力,淪為「媚俗」的扯線傀儡。
------
參考資料:
白水(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生命中不應承受的媚俗〉: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6939
梁文道〈媚俗〉:http://www.commentshk.com/2010/08/blog-post_21.html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